回到台北朋友住處,簡單打一下現在腦袋裡的東西。
今天一下火車,就直跑慕哲咖啡館。黃致豪律師要講王景玉案。早上我才看過判決,可是有很多看不懂。並不是真的完全不懂,我整個快速看過,挑看得懂的看,多少還是可以拼出一些脈絡。到了會場,黃律師問我,看了判決有什麼心得嗎?有解決我心中的疑惑嗎?我當時才剛到會場,還有點喘,肚子有點餓,腦袋空空,什麼都講不出來。我本來想要趁講座前趕快吃一點麵包,但很快講座就開始了,我打開筆電,開始聽講做記錄。
我開始聽講,我很想專心,但大概是一路戴了很久的口罩,火車上四小時,加上現在,加上現場人多,我覺得呼吸有點不順。我肚子很餓,我很想吃一口麵包,但因為我坐在最前面,兩位講者就在我面前,我不好意思拿麵包出來吃。這時候我想,如果是滌,肚子餓了應該就會把麵包拿出來吃吧,因為這個麵包又沒有很重的味道,不會影響到別人。但我不是滌,而且我坐最前面,而且我很想聽。
過了一個小時,肚子比我想像得餓,而且我開始覺得有點頭暈。這時彭醫師剛好在講精神鑑定,在講有沒有行為能力,在講控制。這時我覺得,現在的我的腦袋根本沒辦法控制我的腦袋,喔不,我正控制著自己不要吃麵包,不要離開座位,但是我無法控制我腦袋的思考,這時候如果有人突然問我,對台上講者內容的反應,我一定什麼都說不出來。
我那時閃神,我想著,我是一個所謂的「正常人」,但我完全無法思考我的思考。這時如果突然有人要我分析什麼,我一定分析得亂七八糟。過了一個小時半,我覺得我的頭有點暈,肚子,好像有點怪怪的,我很想上廁所,我想不行我不能再顧及什麼禮貌了。我還是很想聽QA,但我知道我繼續坐在那裡也沒有意義,因為我的腦袋已經不是我的腦袋了。當黃律師和彭醫師講到一個段落後(我甚至在等一個段落),我拿起隨身包和麵包,走出講座會場,到旁邊的咖啡廳。
我先去上廁所,一脫褲子我嚇一跳。好多血。我以為我的月經已經結束,但她又來了,量很多,而且屬於會滴的那種。我吸一口氣,還好我還墊著護墊,雖然都滿出來了。量很驚人,我坐著等她滴完,想著難怪剛剛覺得頭有點暈。然後我想著還好我有帶隨身布包,有衛生棉,還好廁所有衛生紙,雖不多但剛好夠用。
我花了一點時間清理,清理好後走出廁所。我點了一杯卡布,然後拿出麵包開始吃。吃麵包的時候,我發現店員在看我,我想著是不是不能用外食。但我實在是不行了我一定要馬上吃,我想著怎麼會把自己弄得那麼不舒服。店員繼續看我,我繼續吃。
我想著如果是滌,一定不會解釋自己為什麼在吃麵包。但我不是滌,我知道店員看我的原因。店員送咖啡來的時候,我主動說,請問不能用外食對嗎?店員點頭。我說不好意思因為我現在人很不舒服,我一定要馬上吃點東西。店員點頭表示可以理解,她說沒關係你的麵包沒有什麼味道,而且現在已經很晚了。
我想著在所有可能引發不解的時候,如果其中一方願意主動說明什麼,那麼誤解就可能減少。但那是因為我還有餘裕。如果我當下不舒服的程度比那個願意說話的自己高上五倍呢?我還願意說明自己的狀況嗎?我可能不願意說明因為我顧不到。但店員有可能因此認為這個人奇怪,不知道咖啡館禁用外食嗎?他不會知道我不舒服。
後來我一邊吃麵包,一邊聽著會場內黃律師的聲音。我想到他剛剛講的刑法,他說刑法與刑事訴訟設計的用意,是為了保護被告的權益。保護被告的權益?我覺得這聽在一般大眾的耳朵裡,應該覺得不可思議。「他們是犯罪的那一方耶!為甚麼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我發現法律上所講的罪,跟一般大眾所認為的罪,似乎有著定義上的落差。一般大眾所認為的罪,是「犯行」;而法律上所認為的罪,是一個人是否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能力,這個人是否有「完全責任能力」?
可是什麼叫做「完全責任能力」?一個人究竟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到什麼地步?
我們都直覺的覺得,一個人一旦成人,不是笨蛋不是白痴,他應該就要能為自己負責。可是我想著我自己剛剛的狀態,自己那個很不舒服的狀態,我可以覺察到那個時候我的判斷能力比「平常」要低。這不是說我無法判斷,但我有可能做出比較差的判斷,或是我的判斷就跟著身體或情緒的狀況走。
我想著如果把我的不舒服放大到十倍,或是一百倍,那我還能做出好的判斷嗎?我還能為我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嗎?但我又可以想像有人一定會說,「那你為什麼要讓自己落入很慘的處境?」嗯,這個社會似乎認為一個人若落入很慘的處境,一定與他自己有關,他該為自己負責。
確實我剛剛也想著,我幹嘛要把自己弄成這樣,我為什麼要那麼趕?我為什麼要提著行李走爬四層樓的樓梯導致出血?我為什麼不多走點路坐電梯?我不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嗎?我知道啊為什麼我沒有避免?
但我沒有影響到別人,看起來沒有,因為我努力讓自己的不舒服,不要影響到別人。但如果有些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某些行為呢?「那他就不要出來,不要出來外面亂走。」我想起有次有個鄰居說,「你弟為什麼都走地下室停車場的坡道?他為什麼不走大門?為什麼我問他他不回答?為什麼他很兇地看我?」
我試著解釋給對方聽,我說我弟走地下室是因為他不喜歡碰到人,所以他選人少的地方走,「你覺得你怕他,其實他才怕你。」「那他為什麼要那種眼神?他為什麼要罵人?」我說,他罵的對象不是你這個人,而是你說的話讓他直接反應,他覺得他走地下室又不關你的事,「他對你沒有敵意,他碎唸白癡是因為你說的話。他不想回答你是因為他覺得沒必要回答,他也是住戶,為什麼不能走自己大樓的地下室?」
我試著解釋給鄰居聽。我可以感覺到那一觸即發的可能危險。比如當下如果他繼續逼問我弟,那我弟會怎樣?或對方會怎樣?還好後來事情往好的方向走,大樓管理員是一個想要試著了解我弟的叔叔,他對鄰居說我弟有自閉,「他高功能自閉。」「自閉症會這樣嗎?自閉症會很兇的看人?」「他亞斯啦!」
管理員試著用名詞來解釋我弟的狀況。我不喜歡簡單的被貼標籤,但在那個鄰居身上似乎有用。那個鄰居在知道了「原因」之後彷彿稍稍鬆下來,似乎貼了標籤後他就能理解我弟。「那他有沒有去治療?你們做家人的有沒有帶他去治療?」
這問題的問法令人不舒服,也很難回答。我吸一口氣,試著從另一個方向說給鄰居聽。我簡單說了滌的狀況,沒辦法說得很詳細,只能先概略的說,把重點擺在──
「他挑少人的地方走,就是想要避開人群──這樣的行為其實不會影響到他人──但別人不了解的話可能會害怕,所以我也才想要說弟弟的狀況給你聽。」我說,「如果有像你們這種『理性』的人願意多一點了解,如果社區有人看到我弟那樣覺得奇怪,你就可以幫忙講給他聽,那我弟就不會是問題。」
我故意把他大姊拉成像是一夥,說她是理性的人。大姊看起來也比之前緩和。雖然,她對我弟的理解仍舊是標籤的理解。這談起來很複雜,但至少跨出第一步,至少讓她不要怕,讓她不要以為我弟有敵意。
但我又可以想像,如果有類似我弟這樣的人,如果他沒有有餘裕能夠理解他的家人,如果大樓管理員和社區的人都帶著敵意,那麼情況只會變糟。那麼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了什麼」,那像這樣的人,他屬於有完全責任能力的人嗎?他究竟可以為自己付上多少責任?該為自己付上多少責任?家人的責任呢?社區的責任呢?刺激他的人的責任呢?
黃律師談到刑法中的「謙抑思想」。因為刑法可以剝奪人的自由、財產,甚至剝奪人的生命(如果這個國家還沒廢死),所以它在下判斷的時候,必須「努力」瞭解被告在行為當下的方方面面,以期判決「罪」「責」「相當」。
可是到底什麼是「罪」「責」「相當」?這又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但至少我理清一點,刑法的設計不是用來還被害者「公道」的(這句話說出來可能會令許多人搖頭),它反而是在政府動用權力時,保護被告的權益,所以才會有無罪推定,才會有刑法第19條。
「可是,如果刑法不是用來還被害者公道,那被害者該怎麼辦?」最後黃律師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我已經寫得太多了,我本來要簡單寫,卻從昨天晚上寫到今天早上(請不要擔心我有睡覺),我要先休息了。
邊想邊寫,寫得很亂。對法律若有理解錯誤的部分,請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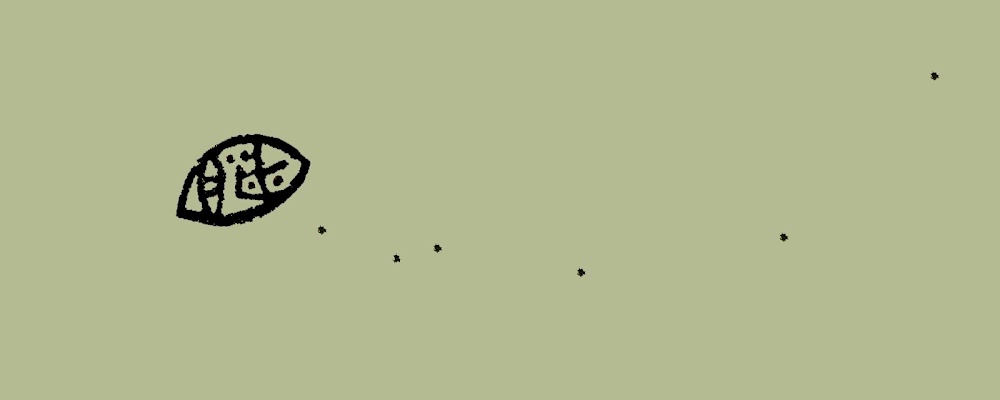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