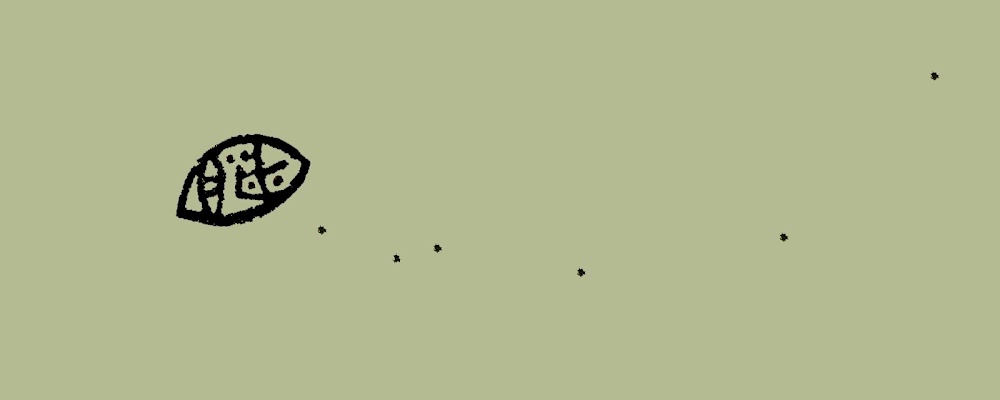我想把那些行政事務一一記下。想了想,又停。又想想,還是記下。
滌的遺物很少,除了衣服褲子球鞋、電腦,從前看的書(很早很早以前的書了,他後來都只看網路上的資訊),幾乎,沒有了。所以花最多時間的,反而是媽幫滌買的基金、保險。這些媽因為擔心滌可能永遠無法在經濟上自立,擔心自己先走而替滌做的各項與錢有關的事,現在都用不到了。滌未來用不到了,但錢還是在那裡,需要處理。
本來就是媽媽的錢,但因為在滌的名下,所以滌走了要辦繼承,爸媽是繼承人。要辦繼承得先被遺產稅申報,要辦完稅,處理完之後銀行才能辦繼承移轉。而這一切不是從國稅局先跑,而是得先跑銀行做資產餘額證明,保險公司的保單也都得一一去做保單價值證明,拿到證明後再填寫遺產申報書,再跑件,完稅核發後再去銀行辦繼承移轉。全部辦完可能是,九月第二週的事了。
媽說,「我真是替自己找事。替你找事。」
我說不要這樣說,誰知道。你真的是為滌的未來做很多打算,「誰知道會用不到……」甚至國民年金他自己也不用到,「反而是我們兩個老的可以領到遺囑年金……」媽說。
爸說,竟然是在滌離開之後,拿到滌給的錢。
2021年8月29日 星期日
滌給的錢
2021年8月26日 星期四
好奇怪的感覺
廚房洗碗槽的菜瓜布、擦桌子的抹布、擦地板的抹布、吹風機放哪裡……這些細微小事,逐一跟媽媽確認。我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沒在高雄老家待超過一週的時間,現在卻是因為滌不在了,所以留了這麼長的時間。
一方面是因為滌在時的生活空間,我若回家待得太久,對四人都是辛苦。這很微妙,回家跟滌說話、跟爸媽說話,是抒壓緩解,但住得太久卻會讓原本就緊迫的生活空間,變得更加壓縮。現在,滌不在了,房間門不用再關起來、客廳餐廳的燈都可以打開,整間房子突然變大了。好奇怪的感覺。
好奇怪的感覺。滌離開是這麼一件無可復返的事,卻帶來在生活空間中放鬆的感覺。放鬆,我問自己可以這樣感覺嗎?但是不可以嗎?
昨天我在滌的房間,現在我還是都叫滌的房間,跟他說話,像從前跟他說話一樣。喔不,當然不可能像從前,從前是一來一回,現在我只能自己說了。但很奇怪,我不覺得孤單,真的很奇怪。
昨天我在想,滌現在在哪裡?這個問題不是真正的問題,我不是真的想知道他在哪裡。只是我想到從前,我想到人死這件事,我都覺得,死了就沒有了,我一直這樣覺得。但是昨天,這整個禮拜,我發現我會去想他會在哪裡?他會有感覺嗎?他會感到平安嗎?他會感到自由嗎?還是他什麼都不會有感覺?他什麼都不再是,不再有?僅有的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腦袋裡的,他的樣子?
我從前不會去想死的那邊的事,因為我無法知道,想了也不會知道。現在我仍舊不覺得想了會知道,只是會忍不住去想。我會去想,但不是想知道答案。我不是在問答案,我只是在想。
2021年8月22日 星期日
寫出來,以後應該可以比較自然的談這件事。
我弟於2021年8月18日晚間10點41分離世。走得很快,應該沒有痛苦太久。
很奇怪的感覺。很奇怪。我聽到我爸說救護車載他入院時,我心想,他因為飲食問題身體已經出了狀況,現在願意入院檢查治療了那麼應該是好事。在我訂了票等待回家前,我爸又從醫院打電話來,「弟弟已經住加護病房,醫生說他的肝已經不行了,最快一兩天,最慢一週。」
所以我根本就來不及,我回到高雄時,弟已經在加護病房裡無法探視。再接到加護病房的電話時,已經是,要準備後事了。前後不到二十個小時。好奇怪的感覺喔,在前往加護病房的路上,我還在想,最後我要跟滌說什麼,他能不能聽得見?會不會我什麼都說不出來?結果門打開,醫生跟我們說,請我們節哀,「心臟已經於10點41分停止跳動。」我看看時間,差了九分鐘。什麼意思,所以等一下走進去看到的就是死掉的弟弟嗎?那會是什麼樣子?我好像走得很快但覺得時間過得很慢。我看到了,我本來以為會很恐怖,但我不覺得,他就像平常一樣,直挺挺的、正正的躺著,跟他平常睡覺一樣。他平常睡覺就是那樣啊,躺得超正的,身體不會歪,頭不會偏,現在就跟睡覺時一模一樣啊,只是皮膚變成黃色的,我真的覺得他會睜開眼睛。
所以真的很奇怪。我腦袋知道他死掉了,但是心裡不覺得。接下來就是一次一次,確認他死亡的事實。確認死亡後,馬上就要送殯儀館,這麼快啊,這麼快就要送殯儀館?要怎麼送?護士說找葬儀社。葬儀社?這麼突然我們都還沒有找啊。「醫院對面就有一家,」護士說。那時候已經要半夜了,媽媽還在哭,我要趕快連絡。我搜尋了網路上的葬儀社,沒有頭緒,我不知道哪一家比較好。我們走出醫院,對面果然有一家,我打了招牌上的電話,店面的鐵捲門往上捲了。我簡單說明,我們希望樹葬,了解相關流程與費用後,想說就這家吧,至少老闆可以馬上找人來載弟弟。我不知道,原來人死了馬上就要離開醫院。還好,之前就跟爸媽討論過樹葬,至少確定了這件事,本來我還在想會不會太早討論了,現在很慶幸我們先討論過了。「你們不用請法師嗎?」「不用穿西裝穿壽衣嗎?」不用,弟弟希望簡單就好,我們也希望簡單就好。
我和爸媽回到加護病房,等葬儀社的人來。媽媽握著弟弟的手繼續哭,我還是覺得很奇怪,弟弟看起來就跟平常一樣。葬儀社的人來了,把弟弟從病床抬到擔架車上,這又確認了一次,弟弟被抬的時候沒有醒來。我跟在擔架車的後面走,到了地下室,弟弟的頭因為路面顛頗而晃動,又確認了一次。上了禮儀車,我們隨車到殯儀館,弟弟下車,要被推進冰庫前,又確認了一次。沒有死掉的話,不能被推進去吧。
接著是隔天,去醫院辦死亡證明書,再次確認。去戶政事務所辦除戶,辦事員問身分證要回收還是剪角保留,又確認了一次。把文件送到葬儀社給老闆,繼續確認。老闆拿著文件說,這樣就可以去辦火化手續了。
很奇怪,爸媽都睡不著,可是我睡在弟弟的房間裡,我竟然睡著了,還睡得很沉,醒來時才想起弟弟不在了。我想起,今天要火化了耶。刷牙洗臉時,我覺得指甲有點長。我突然想滌平常是怎麼剪指甲的呢?他那麼討厭咖咖咖的聲音,他是剪得很慢很小聲,還是乾脆用手剝?我沒有機會問他了。
去殯儀館,弟弟從冰庫被推出來,又確認一次。整理好入棺後,再確認一次。他們要我跟弟弟講話,可是他們人好多我不好意思在他們面前跟弟弟講話,而且我現在要說什麼?我在想弟弟知道自己那麼快就要死了之後,他在想什麼?爸爸說那天弟弟在加護病房時,眼睛大大的看他,好像在說,啊那麼快啊,卻也沒有多說別的,也沒有哭。我問爸弟弟可以接受嗎?應該可以吧,爸爸說。我沒能跟滌說上話,我不知道他最後的想法是什麼。
但我又想,你不是很出世嗎?應該能接受吧?可是我又想,你就是太天真了,才把自己的身體搞成這樣。但會不會其實是我太天真?太相信滌會知道自己的身體,太相信他說的話。一個太自以為是,一個太相信對方。
長輩無法送棺,只有我能送。我跟在弟弟的後面,葬儀社的人要我跟著喊,火要來了喔,請你的魂魄趕快離開。魂魄趕快離開,魂魄要去哪裡?我不知道魂魄會去哪裡,但我還是跟著喊。
接著是撿骨,又確認一次。但這時已經沒有弟的樣子了,只剩盤子上的骨頭,跟名字。兩盤,媽媽說只有這樣喔。葬儀社的老闆說,很多了,「老人家的骨頭燒完更少。」
骨頭送進去研磨,出來就變成白色的灰了。包在紙袋裡,提在手上,比想像得重,感覺超過三公斤。
原來樹葬是這樣啊,一棵樹下有八個穴位 。我對媽說你選,媽要我選,最後爸說弟怕熱那麼在樹蔭下好了。我們說好啊好啊,忘了樹蔭會隨太陽移動。那時是下午一點四十五分,我們選好了穴位,爸爸把骨灰倒進穴裡。爸爸打開紙袋,說,「骨灰是白色的喔。」
──2021.08.20
2021年8月16日 星期一
住院住了半個多月的三花,終於回家了
三花,住院住了半個多月的三花,今天去接她回來,像換了一隻貓,叫聲超宏亮,超有力氣。我跟Y說是換了一隻貓回來嗎。
七月底時,三花又脫肛,我們自行把直腸塞回去後,但還是很怕她又掉出來。託朋友的福,三花進到那間我們都很信任的醫院,後來檢查發現是膀胱結石,而且有一公分!一公分!那麼小的三花可能不到三公斤的三花竟然有一公分的結石,還好有檢查出來。
等待手術的那幾天,三花不太有食慾,不曉得是因為痛還是怎樣,有兩天幾乎不吃,我們有點緊張,因為貓咪不吃很危險。還好後來打了點滴後有精神了,願意吃了。看著她大口吃飯真心覺得,大口吃飯真好,願意吃就好!
手術很順利(去除膀胱結石,還做了直腸固定),傷口復原得也很好,三花的胃口變也得好好,原來以前吃得少不是胃口小而是沒食慾。我們接回三花,三花喵喵喵,兩個兒子出來迎接。三花跟兩個兒子打完招呼後,奶黃還想再靠近,卻被三花兇了一下,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她覺得奶黃太髒XD
(真心感謝協助三花的朋友)
(也真心覺得三花好強!她做了兩項手術耶!)
(希望接下來一切平安,不要再結石或血尿或脫肛了.....嗯最後一項應該不會了)
三花:「來,讓我聞聞你的屁股.....」
奶黃:「媽妳回來啦!」
三花:「你怎麼好像有點髒......」
2021年8月12日 星期四
旺來小聲哭
今天下午兩點左右,旺來走到門口,小聲地哭。養過狗的人應該會知道那種聲音,就是沒有叫出來,很像卡在鼻腔裡的那種嗚嗚聲。但現在還不到散步時間,沒特別理牠,結果牠就一直走來走去,最後「ㄨㄤˋ」了一聲。牠很少在這個時間這樣,想必是有所求,套了胸袋開門讓牠出去,發現原來牠想去活動中心找小朋友。
小朋友一看到旺來,就叫「旺來旺來」,旺來開心的跑過去。我看那三位眼生,他們說以前讀過永安,後來搬家就轉學了,現在剛好放暑假回來。其實我說的小朋友已經不是小朋友,是青少年了,兩個國小畢業,一個國一。
我說你們雖然轉學了但旺來都記得你們耶!我覺得旺來好厲害,活動中心至少距離我們家有二十公尺,但牠竟然會知道你們在這裡!(到底是聽到聲音還是聞到味道……?)
太少拍照了沒什麼照片哈哈。這張是之前去田裡的照片。
旺來
認識旺來,是先認識叫聲。叫聲尖銳、頻率極繁。我們以為有狗被打,忍不住往叫聲的方向走去。聲音領著我們走近某戶鄰居家,發現一隻青少年犬。「他們家又養狗了,」我在心裡碎唸。狗狗被鍊著,鄰居叫牠:「旺來。」
我問這是新來的狗狗嗎?鄰居說幫朋友代養的,「朋友撿到狗啊,可是家裡不能養,我就說送來我們家,我們家很大。」鄰居家確實很大,主建築外還有一大塊空地。其實他家是不是很大也不是很重要,從前他家狗狗等於是在外邊放養,「全村都是他家」的概念,狗狗都在外邊跑,就算家裡沒院子也沒差。
我們說話時,旺來還是一直叫。我問,牠怎麼了?鄰居說不知道,「牠就一直叫啊。」我蹲下看旺來,試著靠近,伸出手讓牠聞。旺來聞了一下,接著做出想要撲撲的動作,但因為鍊著所以無法。對一個陌生人竟然想要撲撲,看來是親人的狗。
鄰居家之前養的狗,都死了。
因為在外邊放養,死了都是意外。運氣好的狗活上四、五年,運氣不好的狗還未成年就掛掉。但鄰居似乎不以為意。他們對狗,要不全放養,要不全鍊。全鍊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投訴他家狗追車、追人,他們就索性鍊著狗不放。這一鍊就沒日沒夜,只管吃喝,不管狗其他的生理需求。一直到有人又投訴,說狗太吵。吵是一定,一直被鍊的狗怎麼可能不叫?於是鄰居又放,這一放又變放養。被鄰居養的狗要看運氣,看是在外邊跑到誤食毒藥或被車撞死,或是有人投訴後被鍊回家裡不放,兩種命運二選一。
旺來有著狼犬的臉型,大大的兩隻眼睛,邊框有著細細黑圈,像描眼線。旺來聞我的手,想撲不能撲,又叫了幾聲。我看著旺來想著,你會有什麼樣的命運?
後來,旺來跑去學校了。
鄰居家旁是小學,校長對狗友善,整個學校幾乎也都對狗友善。旺來還是會回鄰居家吃飯,晚上在家外頭睡覺,但整個白天幾乎都在學校,跟小孩一起上課、一起跑步,聽小孩吹直笛。這大概是旺來最好命的時候了,牠親人,喜歡自由,牠也極少像鄰居從前放養的狗總是在外頭晃盪,大部分的時間牠都待在學校,跟學校裡的孩子一起生活。
「旺來,旺來……」小孩總是叫旺來一起來玩。旺來就這樣生活了五年。
今年五月,我們聽到鄰居家有急切的狗叫聲。叫聲持續一陣,停了。到了晚上,又是一陣叫。我們想,鄰居又養新的狗嗎?但太晚了,明天再說。隔天早上六點多,叫聲又起,這次仔細聽,叫聲好像旺來。「他們把牠鍊回來囉?為什麼?」我們出去看,果然看到旺來被鍊在樹下。
旺來看到我們,用力彈跳,像是想把鍊子扯斷。看牠跳成那樣,我來不及問鄰居,就先放開。一鬆開鍊子的扣環,旺來馬上衝出去,撒了一泡好長的尿,尿完就往學校的方向跑去。
雖然覺得鄰居不會管狗狗究竟如何,但畢竟是我放開的,所以還是打了電話。鄰居說,喔,那個旺來喔,旺來不能放喔,學校說牠咬傷小朋友。我一聽有些緊張,咬傷小朋友?是怎樣?「學校說咬傷一個幼兒園的孩子,頭上縫了三針呢。」我說這樣啊,那我去把旺來找回來。
旺來果然跑回學校,我也藉機問了校長狀況。
「旺來平常很穩定啊,那次是因為那個小孩在旺來睡覺的時候摸牠。狗在休息的時候不能摸啊,提醒小朋友很多次,但就是有小孩不聽。可是怎麼辦,就真的咬下去了,小孩被咬到頭,家長很生氣很緊張啊。雖然不是旺來的錯,那是生理反應,但我們也就不方便讓旺來待在學校了。」
我一邊聽校長說,一邊想像著旺來以後悲慘的命運。就鄰居的養法,應該就是鍊養。旺來喜歡親人又愛自由,我光用想的就覺得不忍心。
把旺來牽回鄰居家,問了鄰居有沒有可能每天固定時間帶牠去散步放風,「至少帶牠去大便尿尿?」鄰居說哪有那個時間,「我要顧兩個孫耶,」「而且牠力氣那麼大,我哪拉得動?」
我說,不然我來帶牠散步好了。鄰居說好啊,你要帶就去帶。
第一次帶旺來散步,牠又是強烈跳躍。我說旺來等一下,等一下,你這樣我很難解開。我先用牽繩扣住項圈,再鬆開鍊子。鍊子一鬆開旺來就馬上往前衝,力氣大到我差點被拖著走。旺來瘋狂爆衝,先衝到樹叢解尿,一樣尿很長;再來是瘋狂大便,每一坨都很多。就這樣我被牠拖著尿尿大便,直到走了差不多快一公里,牠的生理需求終於獲得釋放。後來想,旺來被鍊著的時候,可能不會在自己的活動範圍內大小便,所以牠一直忍尿忍大便。從前牠沒有長時間被鍊養過。
我想,這樣不是辦法。
知道旺來以後不可能再自由的去學校了,想著牠以後會被鍊養感到很不忍心,我跟伴侶討論後,決定向鄰居提出收養旺來的想法。旺來就這樣來到我們家。
旺來來到我們家,學習當隻家犬。我們家本來就有隻狗狗Migu,現在牠們可以作伴。但看著旺來待在家裡的樣子,我可以感覺到牠對自由的需求,以及跟孩子相處的渴望。有一回我們帶旺來去田裡,剛好有小孩騎腳踏車到田裡玩,小孩看到旺來,就旺來旺來的叫著;旺來一看到小孩,就開心的跟著小孩跑走了。
「讓牠去吧,等會再去帶牠回家。」
──刊載於《幼獅文藝》第812期,2021年8月出版
松本大洋的《花》
看完松本大洋的《花》。
第一個心得是──這本畫得好細?哈,其實我也只看過他的《GOGO MONSTER》;然後《兵乓》看了一半,《SUNNY》看了一半(兩套都很愛但都看一半,因為是在朋友家看的,來不及看完)。就目前這幾套看到的,我覺得《花》畫得超細,背景超細,細到像版畫。
但很妙,我唯二兩本看完的松本大洋,竟然都跟「靈」有關。其實「靈」是我超級不熟悉的領域。在現實生活裡,我不主動接觸「靈」,也不否定,畢竟這世界有許多我可能無法接觸、感知、明白的什麼。
Y問我覺得「靈」是什麼?我說我不知道啊。他又問你覺得是靈異的「靈」?還是身心靈的「靈」?還是神靈的「靈」?靈魂的「靈」?我說我不知道啊,可能都是吧?
我不知道,但我感覺自己在讀相關故事時,我不會排斥這些「概念」(對我來說,我目前還沒能真實感受過,所以我只能將它看成「概念」)。雖然我自己並不特別好奇,與之保持距離,但我相信某些人感知世界、與世界連結的方式,與我不同。
前幾天剛好讀到朋友的日記,寫了部落的媽媽邀他去參加祭典,他描述祭典中的人們,感覺自成一個世界。我覺得那似乎就像《花》一樣。擁有「花」之名的製面者,以及擁有「鳥」之名的祭舞者,松本大洋述說這兩個族群的故事。很奇妙,儘管是「花」的後代,但身為哥哥的「百合」可以感知到「祂們」,身為弟弟的「椿」卻無法感覺到「祂們」──椿會說,「什麼祂們祂們……根本就沒有那種東西吧?」「哥哥的腦袋是不是壞掉了?」
可是,感覺不到祂們的椿,卻是父親指定的製面繼承者,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這就是這個故事有意思的地方。
製面者,也就是製造面具的人。在木頭上刻出臉來,彷彿要能看見木頭裡的臉。「花」是在木頭上刻臉的人,而整本漫畫看起來也很像木刻,如前面所說,像版畫一樣。(PS.《花》的內封就真的是版面了。)
這可能是《花》為什麼以精裝大開本呈現,因為這樣才能看到那些細緻的刻紋啊!包括面具上的刻紋、臉上的刻紋、山林裡的刻紋、背景中那些象徵「祂們」的刻紋……
2021年8月7日 星期六
王鷗行,《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
讓我重來一遍。
親愛的母親:
我書寫,是為了接近妳,雖然我每寫下一字,跟妳就多了一個字的距離。我書寫,是為了回到過去,回到維吉尼亞州休息站的廁所,妳滿臉驚恐瞪視飲料販賣機上方的公鹿標本,多叉鹿角陰影映在妳的臉面。回到車上,妳不斷搖頭說:「我不明白這是幹嘛?人們看不出那只是屍體嗎?屍體就該送牠上路,而不是以那模樣永遠困住。」
現在我回想那隻公鹿以及妳的瞪視,牠的黑色玻璃眼珠有妳的倒影,扭曲困在無生命的鏡子裡。嚇到妳的不是梟首動物荒誕高掛,而是標本象徵了永不結束的死亡,人們到廁所解放,經過牠,牠便再死一次。
我書寫,是因為大家說千萬別用「因為」一詞為句首。但我不是在造句,而是想解放。因為我聽說,自由不過是獵人與獵物之間的距離。
──王鷗行,《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
◆
我才剛讀了第一頁,就覺得這可能是我今年排名前面的愛書之一。有些人的句子是這樣的,一讀就覺得鑽進你的心裡。王鷗行寫媽媽,這在我想來是接近紀實,但介紹說這是小說。但我又想,散文和小說的分別有那麼重要嗎?它被叫作什麼對我來說有差別嗎?當然這當中的差別可能是──我讀到的是紀實的故事?還是虛構的故事?紀實與虛構有影響嗎?當然有影響。但真正影響我感受的,是「他想說的」。
他寫下他想對媽媽說的,想對自己說的。他用文字慢慢接近「他們」,同時知道文字與被書寫者的距離。
王鷗行,越南裔美國人。晨間讀書時我這樣介紹王鷗行。Y說,跟黛安一樣。「黛安?喔對黛安……」我想起《馬男波傑克》裡的黛安,「黛安也是越南裔美國人,她也是寫作者。」
然後呢?沒有然後,我只是這樣想到。
我已經讀了二十頁,但才剛開始。今日大雨,很適合讀書。我要繼續讀了。
2021年8月6日 星期五
我唯一知道的路(阿巴斯)
你不在時
白天和黑夜
是分秒不差二十四小時
你在時
有時少些
有時多些
◆
猶豫,
我站在十字路口。
我唯一知道的路
是回頭路。
◆
我失去
我得到的。
我得到我失去的。
◆
今天,
如同每一天,
被我失去了。
一半用於想昨天,
一半用於想明天。
──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收錄於《一隻狼在放哨:阿巴斯詩集》
2021年8月5日 星期四
寫,需要一個想要寫的開頭
寫,需要一個想要寫的開頭
啊對我就是想寫這個
不一定會寫得完
不一定會寫得好
但總有那麼一個開頭
「這個」
眼睛看到的
腦袋想到的
身體感覺到的
一個連結
一句話
有人問我可以寫那個嗎?
當下我想到可以寫的
但沒有馬上
後來就消失了
現在要從頭再來
2021年8月4日 星期三
那條線?
我又讀了自己早上的發文,然後想起去年讀《地下鐵事件》時寫的讀書筆記──
◆
「看來皈依奧姆真理教的人們,似乎很多是為了獲得麻原所授與的『自律性運力流程』,而將所謂自我這貴重的個人資產,連同鑰匙一起託付給麻原彰晃這個『精神銀行』的保險箱。忠實的信徒們主動捨棄自由、捨棄財產、捨棄家庭、捨棄世俗的價值判基準。如果是正常的市民的話一定會訝異地說『怎麼這麼傻』吧。但相對的,對教徒來說那是非常舒服的事。因為一旦把自己交給誰之後,就不必自己一一去辛苦思考,也不必控制自我了。」
──《地下鐵事件》
讀到這段時,有些人一定覺得──那些人不就是「逃避自由」嗎?把自己的自由交給他人,只要聽從信仰領袖的命令就好。但那些人一開始其實是想要獲得「被社會奪走的自由」,他們感覺到工作不自由、人際關係不自由、居住不自由,他們可能感覺,無法好好的做自己。正常大眾可能覺得,「你們把自己交給麻原彰晃,沒有了自我意識,這樣算是什麼自由?」但是,被歸類在「所謂」正常人的這邊的人們,就真的擁有自由嗎?
◆
想到這段倒不是說,我認為相信能量說的人跟相信奧姆真理教一樣,因為信仰與迷信真是一線之隔,很難斷定。我想說的反而是「自由」這件事──奧姆真理教的人認為在世俗社會的人不自由,被金錢、被身分地位控制;而一般所謂的正常人認為奧姆真理教的信徒被他們的教主控制──所以,當我們說對方不自由的時候,自己又有多自由?我們對自身的處境是否能真的認識?
但是,「害怕自己的DNA被影響所以相信能量說」,以及「擔心這個社會被拖垮所以選擇打疫苗」,這兩者是類似的事嗎?我覺得有類似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類似的部分是──都是基於擔心;不同的部分是,我覺得後者是有跡可循的擔心。但我這樣說可能也不夠中肯,對相信能量的人來說,他們的擔心應該也是有跡可循的擔心。
所以說到後來還是各自信念的問題?但我在想的是,或說我擔心的是──「那條線」的問題。
忍不住還是想把自己對這件事的「感覺」寫一寫
我知道有些人反對疫苗,我也相信疫苗可能會帶來或大或小身體上的副作用,甚至我承認我對疫苗的生成機制不是很懂。有人說健康的人就算被傳染了也不用擔心重症,這我相信,那我為什麼選擇打疫苗?因為新冠病毒的傳染力很高,如果你不相信國外的數據,那麼可以看看台灣的數據,從五月中開始到七月這段時間病例數攀升。如果我很健康就算被感染了也不用擔心重症,但因為病毒傳染力高的緣故我必須被隔離,因為我可能會傳染給其他人,而其他人不見得都身體健康。
它跟一般感冒不同在,你感冒在家好好休息就可以,你不用被隔離。但因為新冠病毒傳染力高,病毒量高的人就是需要被隔離,就是會用到醫護資源。新冠病毒擔心的不是受感染的會死或不會好(確實致死率不算高),而是擔心大規模的病例數會「不得不」占用的醫護資源,醫護資源就那麼多,一旦被占用勢必會影響到其他病症者醫病的權利。
避免醫療資源的癱瘓、市井小民生活與經濟的癱瘓,這才是我覺得需要打疫苗的原因。
有人可能會說打了疫苗不太代表不會被感染,這確實是,但也有數據說有百分之七十的機率不被感染。打疫苗可減低罹病、重症或死亡的風險,當然,這就要看民眾是否相信。
我不反對不想打疫苗的人,畢竟身體是自己的,他人無權替你決定,政府當然也沒有。覺得自己夠健康,防疫措施做好,保護好自己也保護別人,不打疫苗當然也很好。而對於「打過疫苗的人,DNA會被影響」這個說法,我目前不予置評;但是──「接觸打過疫苗的人,身體會被影響」的說法,我只能說我的感覺不是很好。
覺得不是很好的原因是,這個說法搭配咒語、遠距能量清理、能量卡片一起出現,它跟相信此說法的人說,你可以透過以上方式來保護或修復你被傷害的DNA。一張卡片要幾十元到上百元美金。
我知道這種事情是信者恆信,不信者不信,所以我寫了應該還是很難影響到相信的人。所以我也只是抒發情緒而已。
(PS.本文不歡迎訕笑與謾罵,不論你的立場如何)
2021年8月3日 星期二
打AZ後第一個24小時記錄
昨天上午十點打針,打完後一小時左手上手臂就有感了,重重沉沉的,但不會痛(到晚上才輕微痛)。下午手臂的沉重感緩解,一度忘記自己有打疫苗。傍晚帶狗狗去散步,回來後精神也還不錯。大概晚上六點左右開始想睡覺,肌肉痠痛身體無力地症況開始出現,但因為那個時候鄰居在唱卡拉OK,所以也睡不太著(還好後來他們大概唱到六點半就結束了)。起來後吃晚餐,晚餐沒什麼食慾,吃完後超想睡覺,這時候身體的感覺像感冒一樣,叫你趕快去躺。
但我想說才八點多,還很早,轉了王冠來看,結果才看一半就不行了。我要先去睡了,我跟Y說。躺在床上覺得全身肌肉都很痠,但沒有覺得不好,這是很神奇的感覺,就像小時候感冒發燒身體不舒服就有理由好好偷懶一樣。我躺著,想說明天如果還是不舒服就可以整天廢耶,可以有理由很心安的廢。這次的肌肉痠痛很有感,我跟Y都習慣睡榻榻米當床,但昨天的肌肉痠痛讓我很想睡軟軟的床。
睡前我問Y我有發燒嗎?我自己摸不太出來。我們家沒有溫度計,只能用感覺的。Y摸了一下額頭說,還可以。睡著前覺得冷,但後來就睡著了。
半夜起床上廁所時(從昨天到今天我非常頻尿),看了一下時鐘發現,才十二點?我覺得我已經睡好久好久。躺回去前我摸了一下自己的額頭,說,好像沒有發燒。我說完後換Y摸額頭,「明明就很燙,」接著他摸手摸腿,「你全身都很燙啊。」喔喔,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摸我自己沒有發現是發燒嗎哈哈。
吞了一顆退燒藥後,就躺下睡了。早上睡到七點半,睡醒後覺得全身肌肉痠痛沉重的感覺緩解,只剩下上半身感覺比較無力,然後有一點想睡覺。
(沒有頭痛關節痛沒有吐,我覺得很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