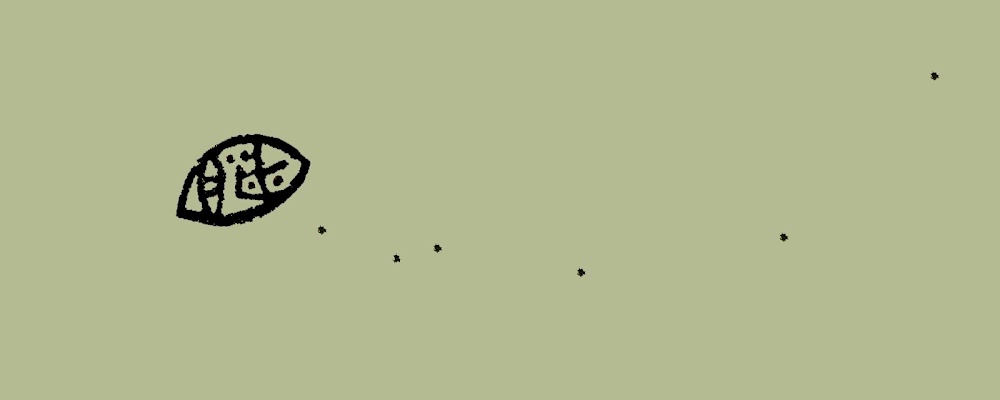2013年5月30日 星期四
跑步日誌(第34天‧20130530)真的喜歡跑步嗎?
大概是因為天氣太熱,最近這兩次跑都邊跑邊想:「到底為什麼要來跑步呀?現在在這操場上跑步的人,都那麼愛跑步嗎?」
最近在fb上看到,也有些朋友在跑步。喂,你們喜歡跑步嗎?
究竟有多少人是因為「喜歡」跑步而跑步呢?問這問題有點怪,因為,最近的我又開始在想「自己為什麼要跑步」這個問題。真奇怪,這問題有什麼好想的?有!因為對我來說,幾乎做任何事都是因為喜歡,當然,生理需求除外(有誰是因為喜歡大便而去大便?)
因為喜歡打籃球,所以去打籃球;因為喜歡畫畫,所以畫畫;因為喜歡寫,所以寫。相較之下我就沒那麼愛料理,所以也就很少做菜。我是那種幾乎只做喜歡的事的人,像「有用」或「有好處」這類原因,很少是我做某件事的動機。
就像以前別人跟我說吃苦瓜很好,可是我不喜歡就不會去吃它;現在吃苦瓜是因為懂得苦瓜的美味了(當然也跟如何料理有關),而不是因為吃苦瓜可以降火氣所以吃苦瓜。
所以我也就搞不通,自己究竟為什麼跑步呢?我所喜歡的運動項目中,跑步絕對不是第一第二,也不是第三第四。或許有些人真的覺得跑步很好玩,但我絕對不是覺得好玩的那一個。到底是什麼讓我上次抱怨完今天又來跑呢?而且邊跑邊覺得好熱但還是把預定的圈數跑完了。
因為怕自己跑不完,所以只預定了五圈。今天跑得蠻快的,大概是不耐煩吧!第五圈還加快了速度。不過起跑時我沒注意時間。
到時候
「到時候除了隔壁那一戶的阿公阿婆以外,你都看不到其他人喔!」
「到時候蟲子會很多喔!可能還有蛇喔!」
「到時候沒有卡拉姆酒可以吃囉!」
「到時候你會覺得很無聊,你沒有活動可以參加喔!」
「到時候你就沒有錢囉!」
不像老斌,他在鄉下長大,前兩年也曾去幫農,他到鄉下生活工作是絕對不成問題的。我是個道道地地的都市小孩,手不敢抓蟲,腳怕髒,對農事一竅不通;而更關鍵的是,我對「錢」,還是有一定的顧慮。
雖然媽媽一直覺得,我把錢看得很輕。
確實,跟一些覺得賺錢很重要的人相比,錢對我來說,只要夠用、可以生活就好。但是,一旦去到鄉下,在學著做農事的這段時間,「我的錢到底夠不夠用呢?」老實說,雖然我一直跟自己說不用擔心,但其實還是有一點點焦慮。
我需要用到的錢,其實已經算少了的了,除了固定的勞健保支出與醫療保險,也沒有其他大筆的花費,剩下就是生活的基本開銷。在鄉下,房租很省,吃就自己來,開始種田以後可能也不太需要買菜;水電瓦斯網路費,可能還是會花一些。接下來就是交通工具了,到了台東可能需要買一台機車,畢竟沒有捷運。
這樣算一算,目前的存款和之後一些零星的稿費,用來支付那些需要花錢的項目,應該勉強夠用。但是,習慣了每個月都有固定入帳的生活,以後沒有了,多少還是有小小的擔心。
雖然自己知道,那只是「擔心」;但是,那擔心卻也真實存在。並不是說擔心的事情存在,而是擔心的心情存在;而那擔心的心情,起於不確定感。
我感覺著自己的擔心,感覺著自己除了新鮮感以外,還有擔心。我並不想去說服自己,跟自己說沒什麼好擔心的;而是,我想知道我的不確定感,從哪裡來?
沒有人能夠確定未來。明天會發生什麼事都不曉得,怎麼可能確定未來?但人們常信心滿滿──因為我都計畫好了;我計畫好了要這樣做,我計畫好在哪個時間達到哪個目標;我計畫好每個月有多少收入,可以支出多少;我計畫好……
一旦所面對的生活是無法計畫的,可能因為那是不熟悉的領域,可能因為決定權在老天;無法計畫,無法掌握,因此有了不確定感。
可是你看斑斑,牠也不曉得明天;可是你看每一個種田的人,他們無法決定天什麼時候要下雨。
我不喜歡規範、不喜歡制度,但是習慣計畫。安排自己的用錢預算,計畫自己的工作進度。我還是覺得計畫是好的,但我想我該學著──
在能計畫的事上計畫,不能計畫的事上放手。
這話寫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所謂的擔心呀罣礙呀就是這樣。但這大概也是人特有的,我想斑斑對於我們即將要去台東,一點也不會擔心與罣礙。
半農半X的生活,我究竟會不會覺得好過?老實說,還沒到那個時候,我不會知道。說不定到時候,我會覺得我早該過這樣的生活;也說不定到時候,沒過多久我就逃回都市了。
對一個從小生活在都市的人來說,鄉下生活是一種想望。但是,得等到它真正變成生活而不只是想望,我才會知道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到時候再來看這篇文章,說不定會覺得很好笑呢!)
「到時候蟲子會很多喔!可能還有蛇喔!」
「到時候沒有卡拉姆酒可以吃囉!」
「到時候你會覺得很無聊,你沒有活動可以參加喔!」
「到時候你就沒有錢囉!」
不像老斌,他在鄉下長大,前兩年也曾去幫農,他到鄉下生活工作是絕對不成問題的。我是個道道地地的都市小孩,手不敢抓蟲,腳怕髒,對農事一竅不通;而更關鍵的是,我對「錢」,還是有一定的顧慮。
雖然媽媽一直覺得,我把錢看得很輕。
確實,跟一些覺得賺錢很重要的人相比,錢對我來說,只要夠用、可以生活就好。但是,一旦去到鄉下,在學著做農事的這段時間,「我的錢到底夠不夠用呢?」老實說,雖然我一直跟自己說不用擔心,但其實還是有一點點焦慮。
我需要用到的錢,其實已經算少了的了,除了固定的勞健保支出與醫療保險,也沒有其他大筆的花費,剩下就是生活的基本開銷。在鄉下,房租很省,吃就自己來,開始種田以後可能也不太需要買菜;水電瓦斯網路費,可能還是會花一些。接下來就是交通工具了,到了台東可能需要買一台機車,畢竟沒有捷運。
這樣算一算,目前的存款和之後一些零星的稿費,用來支付那些需要花錢的項目,應該勉強夠用。但是,習慣了每個月都有固定入帳的生活,以後沒有了,多少還是有小小的擔心。
雖然自己知道,那只是「擔心」;但是,那擔心卻也真實存在。並不是說擔心的事情存在,而是擔心的心情存在;而那擔心的心情,起於不確定感。
我感覺著自己的擔心,感覺著自己除了新鮮感以外,還有擔心。我並不想去說服自己,跟自己說沒什麼好擔心的;而是,我想知道我的不確定感,從哪裡來?
沒有人能夠確定未來。明天會發生什麼事都不曉得,怎麼可能確定未來?但人們常信心滿滿──因為我都計畫好了;我計畫好了要這樣做,我計畫好在哪個時間達到哪個目標;我計畫好每個月有多少收入,可以支出多少;我計畫好……
一旦所面對的生活是無法計畫的,可能因為那是不熟悉的領域,可能因為決定權在老天;無法計畫,無法掌握,因此有了不確定感。
可是你看斑斑,牠也不曉得明天;可是你看每一個種田的人,他們無法決定天什麼時候要下雨。
我不喜歡規範、不喜歡制度,但是習慣計畫。安排自己的用錢預算,計畫自己的工作進度。我還是覺得計畫是好的,但我想我該學著──
在能計畫的事上計畫,不能計畫的事上放手。
這話寫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所謂的擔心呀罣礙呀就是這樣。但這大概也是人特有的,我想斑斑對於我們即將要去台東,一點也不會擔心與罣礙。
半農半X的生活,我究竟會不會覺得好過?老實說,還沒到那個時候,我不會知道。說不定到時候,我會覺得我早該過這樣的生活;也說不定到時候,沒過多久我就逃回都市了。
對一個從小生活在都市的人來說,鄉下生活是一種想望。但是,得等到它真正變成生活而不只是想望,我才會知道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到時候再來看這篇文章,說不定會覺得很好笑呢!)
2013年5月28日 星期二
跑步日誌(第33天‧20130528)好熱真不想跑
好熱真不想跑好熱真不想跑好熱真不想跑……
還是去跑了。明天晚上有私人廚房,不能跑。如果今天不跑,明天又不能跑,沒有跑步的日子累積加起來就達到五天了,這樣不行。所以,雖然覺得好熱好悶,而且很想待在家裡把想寫的東西寫完,但是最後,還是決定去跑了。
今天沒有風。站著不動沒有風,跑起來居然也沒什麼風;偶爾在過彎道時,有一點點風(不曉得為什麼總是在過彎道時有風),覺得呼呼呼總算還有風這種東西存在……
33度又沒有風,跑起來真的很黏。
我才跑第一圈,就決定今天只要跑五圈就好了。沒想到最後,我只跑了四圈半。
我想動物本性是好逸惡勞吧!這種時候在我身上完全展現無疑──為什麼我要在大熱天的繞操場跑步呢?一點風也沒有好難受呀,在家裡吹電風扇不是很好嗎?要命現在才五月呀!我一邊跑著一邊問自己為什麼要跑步,一邊對從我身邊咻咻而過的跑步隊感到欽佩。
跑步隊,是我跟老斌給他們取的。一群年約四十到五十幾的男子,他們幾乎天天來跑,有時候集體跑,有時各自跑;從他們跑步的速度和圈數來看,應該是跑步跑了好幾年了。咻咻咻地,一下就跑完一圈,像是跑步不會累的機器。
他們會覺得熱嗎?會覺得悶嗎?是不是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完全沒有影響呀?
雖然今天第五圈沒有跑完,但我很慶幸自己是在三月開始跑步。那時候天氣還冷,平均溫度在15到20度,是非常適合練跑的溫度。要是現在,也就是五月的現在,我才興起慢跑的念頭,很可能才跑個一天兩天,就打退堂鼓了。
三十多度和十五、六度,兩倍的溫差呀!
在即將更熱的夏天面前,我只希望自己別間斷跑步,跑步圈數我就不打算管了,有跑就好,多跑賺到。
唉唉……我的半程馬拉松,有可能會實現嗎?
自己補記一下5月25、26、27,沒跑步在做什麼。
5月25日,星期六:下午反戰站樁。站了兩個小時,回家就想睡覺了。
5月26日,星期天:去江翠國中旁的石雕公園了解江翠樹群最新狀況。晚上和老斌的香港朋友吃飯。
5月27日,星期一:帶斑斑去看獸醫。
2013年5月27日 星期一
跑步日誌(第32天‧20130524)夏天真的來了
第31天是5月19日,第32天是5月24日,中間休息了四天。通常跑步休息三天以上,要嘛不是碰上連日緜雨,就是每個月固定休息的日子又來了。這次,下雨天跟每個月例休同步,有一種賺到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例休剛結束,也可能是因為天氣變得很熱(傍晚六點半,氣溫還有32度),我還沒開始跑,就決定這次只要跑五圈就好了。
夏天的傍晚,是越來越晚了。這樣想想剛開始跑步的時候,三月的傍晚,是五點半;五月底的傍晚,就變成六點半了。我突然想起曾經跟Y討論過「傍晚」──
「我今天傍晚要出門喔!」我說。
「大概幾點?」Y回問。
「傍晚四點左右吧!」我說。
「傍晚四點?四點......應該是下午吧!」Y說。
喔喔喔,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傍晚」這個詞的意思──「傍」「晚」,確實是「傍晚」呀!
傍晚的時間來得晚,對我來說有好也有壞。好處是,對跑步時不戴眼鏡也沒戴隱形眼鏡的我來說,視線好多了;壞處是,既然天暗得慢,也就代表現在是夏天了,往後只會越來越熱。就算是傍晚,溫度也不下30度,31、32度算是涼爽的了;35度的日子,還在後頭呢!
嗯,夏天真的來了!
2013年5月26日 星期日
我願游泳於樹海
老斌說,這件衣服有點舊了,幫我畫一下吧!
好啊好啊,有衣服給我練習畫,最好了。
昨天,我們從師大人行道上撿回了一片很大的葉子。
我試想了一下,剛好很適合今天這件灰色的T恤。
把葉子拓上去之後,
我在上頭畫了一隻魚。
魚說:「我願游泳於樹海。」
(了解江翠國中事件的人,應該都知道我為什麼這樣說吧!)
其實,這件T恤是老斌的衣服。
只是,穿在model身上,又好像變成女生的衣服了。
掛在窗邊等乾。
窗外的小紅番茄,也入鏡了。
對了,這葉子是麵包樹的葉子。
水洗過後的樣子。
2013年5月22日 星期三
2013年5月21日 星期二
跑步日誌(在鄉下跑步……會被別人笑啦!)
昨天跟今天都下雨,沒跑。
晚餐後,趁著外邊涼涼的又沒雨,跟Y去散步。最近飛蟻很多,尤其是在木造平房旁邊。我們一邊走,一邊小心飛蟻攻擊。
「如果我們搬到鄉下......鄉下的蟲是不是很多呀?」
「很多喔!喔喔你準備ㄔㄨㄚˋ ㄙㄞˋ了!」
「晚上是不是沒有路燈呀?」
「嗯,所以不要晚上出來散步。你可以白天去散步呀。也可以騎腳踏車,那個村子騎腳踏車很舒服。」
「那我可以去跑步嗎?」
「跑步?你不要跑步啦!」
「為什麼不要跑步?」
「在鄉下跑步……會被別人笑吧!」
「啊……」
「人家看到你在跑步,會想說這個人是吃飽沒事幹嗎?來幫我摘果子好了。」
「不能跑步嗎?」
「很好笑耶……」
「沒關係我不怕別人笑……」
慢跑這件事,好像是都市人才會做的事。老實說,雖然我說不怕別人笑,可我自己確實也是這麼想。
不過……呵呵……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樸食的人】Simon、小右與喵喵
Simon、小右與喵喵是一家人。
要先寫誰好呢?先寫喵喵好了。
因為喵喵跟斑斑說過「我愛你」。
喵喵跟斑斑,一隻是人一隻是兔子(是低喵喵是人不是貓喔)。喵喵兩歲,斑斑十二歲;喵喵是女生,斑斑是男生。喵喵跟斑斑說:「我愛你」,斑斑說:「我愛蘋果。」
喵喵對斑斑說「我愛你」時,老實說我有一點點嚇到──這句話來得那樣自然,而我好像沒有跟斑斑說過「我愛你」。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喵喵。喵喵的爸Simon與喵喵的媽小右,帶著喵喵來看斑斑。「喵喵很喜歡兔子。」小右說。「教會禮拜的時候,有朋友會帶小兔子去,喵喵很喜歡小兔子。」
喵喵還很小,斑斑的體型對她來說有點大,大概像是一隻小狗吧!斑斑往喵喵跳去,喵喵一開始有點躲,但沒有像小孩怕小狗那樣地叫。「他叫做斑斑,你可以摸摸他。」忘記是simon還是小右,這樣對喵喵說。
喵喵慢慢蹲下來,摸了斑斑。先摸摸斑斑背上的毛,然後摸斑斑的耳朵。斑斑的耳朵一摸就貼得平平的。喵喵笑,扭屁股。
「喵喵一高興就會扭屁股。」小右說。小右跟喵喵一起蹲著,喵喵扭屁股的時候小右也跟著一起扭。Simon站在旁邊,看著喵喵小右和斑斑玩。simon跟喵喵說話的樣子,像是一個慈祥的爸爸。
這很有趣。
平常simon或小右來拿便當時,都是一個人來,雖然也知道他們有小朋友,但當他們真的帶著喵喵來的時候,我才意識到他們「真的是小孩的爸爸媽媽耶!」
小右是外科醫師。我很晚很晚才知道小右是外科醫師,其實我早就知道她在醫院工作,但是卻一直搞不清楚她的工作內容(我有時候就是少一根筋)。當我知道小右是外科醫師的時候,心裡直呼好厲害唷!那個厲害不是因為醫生擁有高社經地位,而是因為外科醫生這種工作,我做不來。
撇開夠不夠會念書能不能考上醫學院是不是能撐完七年考上醫師執照再經過住院醫師的磨練(這一連串的過程我大概都沒辦法),我覺得當外科醫師最困難的就是,病患的生命就在自己手中。雖說醫師確實也是一種工作,但卻是一種與生命緊密相連的工作。每一個病患不只是一個case,他們是一個一個人,醫學是一種極其專業的知識,病患因為自己不懂,所以將自己交給醫生,信任醫生。光是這中間的信任,我就覺得醫生擔負起好大的責任,但卻又要懂得「對生命的事」釋懷,因為,有些關於生命的什麼,並不是人定勝天。
跳開一點點來說,我無能做也不敢做的工作,除了醫師,還有法官與消防員。醫師、法官、消防員,看出這三種工作的關聯性了嗎?他們都跟「人命」直接相關,他們的判斷、他們的作為,都可能會影響某個人的一生。我是個遜腳,這麼重責大任的工作,得要有強健的心智與靈魂,才能不愧對自己的工作;但同時又要懂得調適,不然沒被別人給壓垮,自己就先被自己壓垮了。
Simon的工作,大概也是我做不來的。喔,Simon並不是醫師、法官或消防員,而是另一個我完全不熟悉的領域──財管。喔,因為我實在太不熟悉了,所以搞不好還說錯了;Simon好像是某家公司的財務長,希望我沒有記錯他的職稱。
假如我沒記錯,但是「財務長」的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呢?實在沒什麼概念。我記得有一本繪本在跟小朋友介紹很多種不同工作的內容,不曉得裡面有沒有「財務長」這種工作,有的話又會怎麼介紹呢?
雖然財務長這工作離我實在遙遠,但Simon自己私下在推的一件NPO的工作,我很感興趣,叫做「台灣公益責信協會」。
嗯嗯,「台灣公益責信協會」這個名詞,我第一次聽的時候也聽不太懂;我只懂「台灣」跟「協會」,「公益責信」是什麼呀,明明字看得懂,意思卻不懂。後來大概瞭解了,簡單的說,公益責信協會想做的事,是希望台灣的公益團體財務能夠更透明。
我這樣講,看的人大概可能還是一知半解……嗯,有興趣的人可以點「台灣公益責信協會懶人包」」來看。
我直覺這工作真是工程浩大,得先找到願意配合公開財務報表的非營利組織,然後將那些一般人可能看不懂的報表,整理成一看就懂的資料(最好是連我這種外行人都一看就懂)。看得懂報表之後,自然就可以知道該基金會的捐款運作狀況,也就能夠決定善用自己的捐款。
我曾經問過Simon,這事是不是吃力不討好呀?基金會他們會理你嗎?他說,當然是不容易呀,但是想做的事該做的事,還是要做。
好像不知不覺講了很多工作的事。可能是因為小右和Simon的工作對我來說,都是我這輩子不可能做的工作。不同的人,做著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工作,也就有不同的生活。人生好像就是這樣。嗯,不曉得喵喵長大以後,會做著什麼樣的工作呢?
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跑步日誌(第31天‧20130519)當每天一早,發現自己又睜開眼了,我們就去做我們想做的事
如果一個月算31天,那麼實際跑步的天數加起來,整整一個月了。
時間這東西果然只會加不會減;如果你持續做,就只會累加;除非不在地球。
去台東的可能性增加了。或許,再過兩個多月,我就不是在操場上跑步了。到時候會不會過著跑步的日子,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說不定,因為要適應新生活而暫停了跑步;也有可能,因為要適應新生活而持續跑步也說不定。
我一直是個城市孩子,不管是在高雄,還是台北。不是一個在草地溪邊跑來玩去的人,不是一個習慣菜場的人,不是一個進廚房的人;是一個去公園玩的人,坐咖啡店的人,用電腦寫字的人。
一直到兩年前,我的城市生活才慢慢有了一點改變。雖然還是住在城市,但外食的次數減到極少;從前是天天外食,現在一個月外食的次數,五隻手隻頭就能數出來。雖然煮食的人不是我,但我認得的菜多了一些,使個刮刀也不再像從前一樣好似隨時會刮到手。
幾乎極少坐咖啡店了,除非是朋友開的,而且學會了老斌教的虹吸式咖啡,煮咖啡變成一種好玩的遊戲。收入減少,買東西自然也變少(其實是越來越不覺得有什麼需要買的東西);現在唯一的花費大概只有每個月的工會勞健保,以及買書,而買書如果到了台東,大概也會減少了。
習慣自己煮食,減少生活上的花費,對可能會搬到台東生活的我來說,是一個好的過渡。畢竟要一個純種都市人,一下子就變成能在田裡工作的人,實在是不太可能也不切實際。現在想,這個機緣怎麼如此剛好,先讓我在城市中過個兩年簡樸生活,然後再去到鄉下過一個真正的樸實生活。
也不說定到最後沒能去成,我還是在城市裡生活著。但我想,某些價值觀漸漸成形中,某些生活習慣也已經改變。
抽一張衛生紙撕成兩半,一半這次用,另一半下次用;洗菜水留起來,手洗衣服的水也留起來,沖馬桶都很好用。能不用電的時候就不用電,不過關於這一點還是做得糟,我經常都大半夜了還在寫字上網,看來想省電還是得早睡。
今天跟bibi聊到自然生活的事,我問了她什麼是樸門設計最近常聽。她說,樸門想做的事是永續;說著說著不曉得為什麼我們聊到了核電。我說,如果反核要成功,台灣人得改變大量用電的生活習慣才行,當然,更該改變的是高耗能的產業。
明天的事都不曉得,更別說未來的事了。但生活是這樣的──當每天一早,自己睜開眼,發現自己又睜開眼了,我們就去做我們想做的事;平淡也好,安穩也好,要很花很心思地爭取也好,要很用力地抗爭也好;這都是生活,都是要睜開眼睛才能做的事;雖然我們不曉得明天自己會不會睜開眼睛,但我們睜開了眼睛就要去做。
今天跑步的時間是晚上六點,天還很亮;跑完要回家時,天暗下來了。氣溫32度,跑步的狀況不好,但斷斷續續地也跑了十來圈,應該超過五千。
2013年5月19日 星期日
都市計畫原來的美意
今年328,士林王家強拆週年,華光社區自救會、紹興社區自救會、台北永春社區、新北市三重大同南段,以及高雄拉瓦克都來到士林王家。那天,我才第一次知道拉瓦克,而我是個高雄人。
在眾多迫牽的議題中,知道拉瓦克的人似乎相對的少;可能因為拉瓦克人少,聲音太小。拉瓦克部落在哪裡?拉瓦克族人為什麼反迫遷?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拉瓦克是一個原住民聚落,民國四十二年起落腳於高雄前鎮區的中華五路上,目前共有 26 戶,約 120 人。拉瓦克自救會表示,部落即將在今年五月中旬左右面臨拆遷,成為高雄的「亞洲新灣區計畫」中的綠地步道。
或許有人會覺得,拉瓦克整個聚落才26戶120人,人那麼少,請他們稍微配合一下政府的政策,不可以嗎?配合政府政策不是不可以,如果這個政策真的能改善高雄市民生活與促進公眾利益。
《破》報做的專題報導:「一個標榜『陸海空運輸零距離』的國際商港,在兩岸直航的背景下,吸引資本進駐、建造更多的觀光飯店、碼頭空港、數位園區、大型商場和高級住宅,……然而只要看看高雄市民實際的生活條件,就知道所謂的亞洲新灣區計劃,不過又是另一個不符需求的發展大夢。合併前高雄市只有150萬左右人口、以工人階級為主,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根據高雄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2002~2008),每個高雄市民的年收入從2002年的92萬下跌到2008年的69萬,收入不增反降,還背負著高雄捷運173億元的債務(2012年高雄市政府年度負債2175億元,來源:財政部國庫署)。」
在一場探討華光社區議題的論壇中,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曾說明都市計畫的源頭與願景:「19世紀末的都市計畫,原是為了解決都市裡嚴重的階級問題。」他並引用霍華德的話:「都市空間的享有,是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
經濟成長應該只是都市更新的一個目標而已。若都市更新只談自由經濟,那麼將只是不斷的開發、拆屋、改建、蓋樓,利益將只集中在某個階層的人身上,弱勢族群將無法感受到都市計畫原來的美意。
(原投書報社,過了七天未見刊登,應該是不會登了。相對於華光,拉瓦克的狀況更少為人知,僅以此短文表達關切,並表達一個公民對都市計畫的期望。)
2013年5月17日 星期五
「搭一個文化的台,真正唱戲的是錢。等錢唱起來,台子就拆掉了。」
大概我很習慣台灣在進行拆遷時,總有警察出動「維護秩序」,當然,所謂的維護秩序是要讓怪手方便鏟平房舍,或讓開發商得以進行工程。想想華光424那場,七早八早在423的晚上,警察就架起圍籬封路了。
因此,一開始我在《暖冬》裡,看不到中國公安像台灣警察那樣的大陣仗,心中有些疑惑……難不成在人權這件事上,台灣還真比中國落後不成?映後向導演鄭闊小小問了一下,才了解這不是哪個政府比較進步的問題,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暖冬》,不只是一部中國藝術家對抗政府強拆的紀錄片。
「搭一個文化的台,真正唱戲的是錢。等錢唱起來,台子就拆掉了。」鄭闊在接受《破》報訪問時這麼說。這說的不只是中國政府對待文化的態度,正好也是《暖冬》這部片子中那群藝術家給我的感受。
並不是維錢有什麼錯,或許那是最低限度所要爭取的,人總是要活下去。只是,如果人民要的只是錢,那麼對政府來說實在太好解決。「會吵的小孩有糖吃」,而政府更樂意小孩如果不吵,他連糖都不用給。
映後座談時鄭闊說了一句話:「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這剛好是我看完《暖冬》的感受。老實說心情是很複雜的,因為人實在太複雜了,權力這東西實在太複雜了,並不是所有人都同一種心思。「抗爭為了什麼?」「維權為了什麼?」搭同一條船,駛向同一個方向,上船的原因卻各有不同。
政府可惡,而人民卻也高明不到哪裡去。到底是什麼讓看似相對抗的兩方,看往同一個方向呢?大概只有錢有這樣的魔力吧!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看的若都是錢,不管是經濟發展還是拆遷賠償,永遠與真正的人無關。
《暖冬》,519還有一場:
http://soho.vodka.com.tw/ntpcff2013-nonews/program/subject-8/subject-8-03.htm
最後,我覺得鄭闊真是頭腦清楚呀!
因此,一開始我在《暖冬》裡,看不到中國公安像台灣警察那樣的大陣仗,心中有些疑惑……難不成在人權這件事上,台灣還真比中國落後不成?映後向導演鄭闊小小問了一下,才了解這不是哪個政府比較進步的問題,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暖冬》,不只是一部中國藝術家對抗政府強拆的紀錄片。
「搭一個文化的台,真正唱戲的是錢。等錢唱起來,台子就拆掉了。」鄭闊在接受《破》報訪問時這麼說。這說的不只是中國政府對待文化的態度,正好也是《暖冬》這部片子中那群藝術家給我的感受。
並不是維錢有什麼錯,或許那是最低限度所要爭取的,人總是要活下去。只是,如果人民要的只是錢,那麼對政府來說實在太好解決。「會吵的小孩有糖吃」,而政府更樂意小孩如果不吵,他連糖都不用給。
映後座談時鄭闊說了一句話:「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這剛好是我看完《暖冬》的感受。老實說心情是很複雜的,因為人實在太複雜了,權力這東西實在太複雜了,並不是所有人都同一種心思。「抗爭為了什麼?」「維權為了什麼?」搭同一條船,駛向同一個方向,上船的原因卻各有不同。
政府可惡,而人民卻也高明不到哪裡去。到底是什麼讓看似相對抗的兩方,看往同一個方向呢?大概只有錢有這樣的魔力吧!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看的若都是錢,不管是經濟發展還是拆遷賠償,永遠與真正的人無關。
《暖冬》,519還有一場:
http://soho.vodka.com.tw/ntpcff2013-nonews/program/subject-8/subject-8-03.htm
最後,我覺得鄭闊真是頭腦清楚呀!
在《刑場》鼓掌
他「思索著那些觀眾為何而鼓掌」,我「思索著自己為何鼓掌」。
鼓掌,在一齣戲結束之後,觀眾以鼓掌為戲結束。似乎沒有鼓掌就沒有結束。至今,我未曾看過一齣沒有鼓掌的戲。鼓掌,與戲的好壞,沒有關係。
有些人真心鼓掌。有些人等待鼓掌。有些人不鼓掌。但掌聲是一定有的。
掌聲,代表這是一齣戲。
看著人欺凌,看著人發狂地大笑、看著人被宰制,看著人痛,看著人哭。最後我們鼓掌。
在暴力現場,我無法鼓掌。雖然真有人會在暴力現場鼓掌。
在《刑場》鼓掌,因為雖然這是《刑場》,但你們似乎接近了「刑場」。雖然我不是你們,我也並未真正進入過刑場。
2013年5月16日 星期四
跑步日誌(第29與第30天‧20130515、16)有跑就要寫
昨天和今天都有跑。有跑就要寫。好像功課。雖然是自己給自己出的功課,但也有不想做的時候。
說到功課,我小時候真的很不愛寫功課,什麼國語習作,可以空白著大半本,一直到期末要抽查的時候,才拼命亂寫(平常交功課的時候到底怎麼過的,我已經都忘了)。我這個人大概有自動把不好經驗忘掉的超能力,導致我怎麼也想不起……最後我究竟是拼死拼活一個晚上把一本國語習作寫完,還是最後有很慘的下場……就算最後的結果是下場很慘,但因為我的記憶裡面沒有,所以,壓跟學不到教訓。
不過,如果是自己給自己出的功課,就算一開始犯懶,但做的時候還是開心。
(可今天好想在睡前亂看個什麼電影喔……我還是決定偷懶去了……)
昨天400八圈,今天400四圈(跑到第四圈的時候開始飄雨)。
斑斑跟媽媽
斑斑跟媽媽一樣
都是連字的發音
ㄅㄢㄅㄢ
ㄇㄚㄇㄚ
斑斑在我叫牠的時候
多半都有反應
媽媽在我叫她的時候
也是多半都有反應
除非
叫他們的時候他們沒有耳朵
母親節的時候
我打電話給媽媽
媽媽說
「我的五官都壞了
只剩下眉毛是好的」
媽媽牙痛
流鼻水
眼睛有蚊子
耳朵嗡嗡嗡
最近斑斑都爬不起來爬不起來爬不起來
斑斑左腳沒力
用右腳站
一不小心就
咕咚倒下
斑斑倒下
索性歪著身子趴著
看起來有時候像貓
有時候像狗
2013年5月15日 星期三
跑步日誌(想要自己寫的被看見)
今天早餐,讀盧駿逸的《陪孩子寫作》。
進一步說,思索「為什麼要寫作」也是寫作的一部分(對部分創作者來說,這甚至是寫作的根本)。
在陪孩子面對寫作時,對於「為什麼要寫作」這個課題,我們要做的很簡單,就是要把這個工作還給孩子,然後給孩子充分的時間去面對和思索。以我的經驗來說,這不需要花太久的時間,只要擺脫了對寫作的恐懼的孩子,往往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寫作動機。一開始也許只是「寫這個很有趣」,然後可能是「想要自己寫的被看見」,或是「有很多忍不住想說的」。當然,也可能孩子將找到一個我們畢生都不會懂得的原因。
──盧駿逸,《陪孩子寫作》
我有一種醒過來的感覺,有一種「自己幹嘛鑽牛角尖的感覺」──為什麼要寫呢?一開始不就只是「寫這個很有趣」、「想要自己寫的被看見」、「有很多忍不住想說的」……
不就只是這樣嗎?
其實到現在也還是。昨天的我想著「為什麼要寫跑步日誌,並且分享呢?」今天,盧駿逸和他所陪伴的孩子,就給了我答案。而這答案其實原本就在那兒,是我忽視它,用一個高標準看它──用一個「想要被看見是不道德的」的高標準,將自己趕進牛角尖裡。
小時候畫畫,一畫好就會「媽媽……媽媽……」,想要給媽媽看;寫了什麼有趣的東西,也想要給好朋友看。現在,不也是一樣嗎?為什麼要去否定「想要讓別人也看見」的這種心情呢?
寫了之後想要給他人讀見,並無是非;為了獲得他人的什麼而寫,其動機才為可議。
進一步說,思索「為什麼要寫作」也是寫作的一部分(對部分創作者來說,這甚至是寫作的根本)。
在陪孩子面對寫作時,對於「為什麼要寫作」這個課題,我們要做的很簡單,就是要把這個工作還給孩子,然後給孩子充分的時間去面對和思索。以我的經驗來說,這不需要花太久的時間,只要擺脫了對寫作的恐懼的孩子,往往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寫作動機。一開始也許只是「寫這個很有趣」,然後可能是「想要自己寫的被看見」,或是「有很多忍不住想說的」。當然,也可能孩子將找到一個我們畢生都不會懂得的原因。
──盧駿逸,《陪孩子寫作》
我有一種醒過來的感覺,有一種「自己幹嘛鑽牛角尖的感覺」──為什麼要寫呢?一開始不就只是「寫這個很有趣」、「想要自己寫的被看見」、「有很多忍不住想說的」……
不就只是這樣嗎?
其實到現在也還是。昨天的我想著「為什麼要寫跑步日誌,並且分享呢?」今天,盧駿逸和他所陪伴的孩子,就給了我答案。而這答案其實原本就在那兒,是我忽視它,用一個高標準看它──用一個「想要被看見是不道德的」的高標準,將自己趕進牛角尖裡。
小時候畫畫,一畫好就會「媽媽……媽媽……」,想要給媽媽看;寫了什麼有趣的東西,也想要給好朋友看。現在,不也是一樣嗎?為什麼要去否定「想要讓別人也看見」的這種心情呢?
寫了之後想要給他人讀見,並無是非;為了獲得他人的什麼而寫,其動機才為可議。
2013年5月14日 星期二
跑步日誌(第28天‧20130513)為什麼要分享自己的跑步日誌呢?
寫跑步日誌是為了希望自己能夠持續跑步,以及持續寫作;這點,我是明白的。但是,為什麼要「分享」呢?
知道有些朋友讀著自己的跑步日誌,知道有些人被其中的某些話鼓勵了。自己的日誌鼓勵了某些人,這也鼓勵了我;可是,這個跑步日誌不是為了勵志,不是為了勵志他人,也不為了勵志自己。
我要很清楚這一點。不是為了勵志而寫,也不是為了分享在fb上而寫。雖然,我在寫的過程中被自己鼓勵了;雖然,我也因為他人被這份日誌鼓勵了而感到高興。
「人有那麼一種心理,痛悔、內疚,等等,放在心裡深思即可。一出聲,就俗了,就要別人聽見──就居心不良。人想要博得人同情、叫好,就是犯罪的繼續。文學是不許人拿來做懺悔用的,懺悔是無形無聲的,從此改過了,才是懺悔。否則就是,至少是,裝腔作勢。要懺悔,不要懺悔錄。」
──《文學回憶錄》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
昨天,我在隱匿的fb讀到上面這段文字。如果就木心的話,那麼,跑步過程中的疲累、辛苦、覺得自己沒有力,一旦分享出來,就是要博得別人的讚,博得別人的認同。寫日誌並分享出來,是裝腔作勢。要跑步,不要跑步日誌。
是這樣嗎?
為什麼我要分享自己的跑步日誌?我可以很誠實很誠實地,面對自己嗎?
在我想清楚,並釐清寫出來之前,我還是會繼續寫,繼續分享。雖然或許對木心這樣層次的人來說,「這種事,放在你自己心裡面想就夠了。」
昨天以「短程中速度」,跑了七趟,約2100公尺。速度加快,真的容易累。
知道有些朋友讀著自己的跑步日誌,知道有些人被其中的某些話鼓勵了。自己的日誌鼓勵了某些人,這也鼓勵了我;可是,這個跑步日誌不是為了勵志,不是為了勵志他人,也不為了勵志自己。
我要很清楚這一點。不是為了勵志而寫,也不是為了分享在fb上而寫。雖然,我在寫的過程中被自己鼓勵了;雖然,我也因為他人被這份日誌鼓勵了而感到高興。
「人有那麼一種心理,痛悔、內疚,等等,放在心裡深思即可。一出聲,就俗了,就要別人聽見──就居心不良。人想要博得人同情、叫好,就是犯罪的繼續。文學是不許人拿來做懺悔用的,懺悔是無形無聲的,從此改過了,才是懺悔。否則就是,至少是,裝腔作勢。要懺悔,不要懺悔錄。」
──《文學回憶錄》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
昨天,我在隱匿的fb讀到上面這段文字。如果就木心的話,那麼,跑步過程中的疲累、辛苦、覺得自己沒有力,一旦分享出來,就是要博得別人的讚,博得別人的認同。寫日誌並分享出來,是裝腔作勢。要跑步,不要跑步日誌。
是這樣嗎?
為什麼我要分享自己的跑步日誌?我可以很誠實很誠實地,面對自己嗎?
在我想清楚,並釐清寫出來之前,我還是會繼續寫,繼續分享。雖然或許對木心這樣層次的人來說,「這種事,放在你自己心裡面想就夠了。」
昨天以「短程中速度」,跑了七趟,約2100公尺。速度加快,真的容易累。
2013年5月12日 星期日
0512下雨天,在家畫T恤
T恤的size是L的,適合男生穿。
不過,穿在女生的人檯身上,
看起來就好像女生的衣服。
不過,是我自己要穿的,所以也確實是女生的衣服。
看出來了嗎?拓的是南瓜的葉子。
這株植物,我就不曉得她的名字了。
這件是我跟老斌一起畫的。
類似接力畫這樣完成的。
T的底較白。
這件是老斌要穿的。
2013年5月11日 星期六
老天爺所做的事
蕭疙瘩突然說話了,那聲音模糊而陌生:「學生,那裡不是砍的地方。」李立轉過頭來看蕭疙瘩,將刀放下,有些驚奇地問:「那你是說哪兒呢?」蕭疙瘩仍坐著不動,只把左手微微抬起,拍一拍右臂:「這裡。」李立不明白,探過頭去看,蕭疙瘩張開兩隻胳膊,穩穩地立起來,站好,又用右手指住胸口:「這裡也行。」大家一下省悟過來。
(中略)
李立有些惱了,想一想,又很平和地說:「這棵樹砍不得嗎?」蕭疙瘩手不放下,靜靜地說:「這裡砍得。」李立真的惱了,沖沖地說:「這棵樹就是要砍倒!它佔了這麼多地方。這些地方,完全可以用來種有用的樹!」蕭疙瘩問:「這棵樹沒有用嗎?」李立說:「當然沒有用。它能幹什麼呢?燒柴?做桌椅?蓋房子?沒有多大的經濟價值。」
蕭疙瘩:「我看有用。我是粗人,說不來有什麼用。可它長這麼大,不容易。它要是個娃兒,養它的人不能砍它。」
李立煩躁地晃晃頭,說:「誰也沒來種這棵樹。這種野樹太多了。沒有這種野樹,我們早完成墾殖大業了。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這種野樹,是障礙,要砍掉,這是革命,根本不是養什麼小孩!」
蕭疙瘩渾身抖了一下,垂下眼睛,說:「你們有那麼多樹可砍,我管不了。」李立說:「你是管不了!」蕭疙瘩仍垂著眼睛:「可這棵樹要留下,一個世界都砍光了 也要留下一棵,有個證明。」
李立問:「證明什麼?」蕭疙瘩說:「證明老天爺幹過的事。」
──鍾阿城,〈樹王〉
◆
〈樹王〉的故事背景是在中國文革時期。故事裡的知青們,要將滿山「沒用的樹」砍倒後燒山,然後再種上「有用的樹」。
蕭疙瘩有一身砍樹的本領,但卻以肉身護樹。故事的最後,巨樹還是被砍了,整座山都給火燒了。蕭疙瘩之後就病了,一倒不起。
蕭疙瘩下葬在距離那棵老樹一丈遠的地方。當天有大雨,下了一整個星期。一個星期後,被燒過的山,這裡那裡開始冒出細細的草;那棵老樹雖然斷了,但土底下的根系龐大,大雨一澆便發了新芽;新芽亂竄,便將蕭疙瘩的墳給脹開。
後來,人們將蕭疙瘩的遺體火化,就埋在原來下葬的地方。後來,這個地方漸漸長出一片草,生白花。懂得的人說,那草是藥,是能夠醫得刀傷的藥。
◆
蕭疙瘩護樹,終究註定是個悲劇;蕭疙瘩一個人,阻擋不了以革命為名的開發。
前天去江翠國中,看著那群護樹志工們在那高高的圍籬外邊,守著老樹,一邊聊天;他們聊著自己的生活,也聊著還可以做些什麼。
「擋不擋得了?」我心裡其實一直這麼問。「如果現在知道,最後還是擋不了,你們還是會繼續守候著樹群嗎?」我心裡這樣問,但沒有問出口。
有的人已經守了好多年了,有的人每天晚上從泰山來到江翠;有的人就住在江翠旁邊,他們白天來巡,晚上來守。
「很有可能五月會來砍樹,可是到底是什麼時候不知道,政府不會告訴你。」而現在是五月。
他們阻擋得了以「發展」為名的開發嗎?或者該這樣問,「我們」阻擋得了嗎?
昨天夜裡一陣大雨。雨剛下來的時候,是零星的一滴兩滴,慢慢地,掉下來的雨越來越多,越來越快,最後嘩嘩嘩地,雨聲大到驚醒熟睡的人。
如果站出來的人越來越多,最後我們也可以變成一場大雨,將熟睡的人驚醒,將世界清洗乾淨。
從前的人砍樹,是親手持斧,親手放火;縱然他們認為自己做著「該做」的事,但是,當樹倒的時候,當火劈哩啪啦燒著山的時候,砍樹的人不會「沒有感覺」。
如果我們像蕭疙瘩一樣,到最後只有自己;但是,「老天爺所做的事」,要讓人們明白。
2013年5月10日 星期五
跑步日誌(第27天‧20130510)那掉下來的雨
晚上有事,加上天看起來陰陰的,本來不打算跑的,但已經兩天沒跑了,於是趁著雨還沒掉下來時,抓緊時間去跑。
還沒走到學校操場,就被一滴雨打到了。我看看天空,嗯,希望那片灰壓壓的雲層可以頂住,好歹也讓我跑個幾圈再讓雨往下掉吧!
今天跑的方式是短程中速度跑。什麼叫做「短程中速度」呢?短程是一次跑大概300公尺,中速度是介於快跑和慢跑中間的速度……其實根本沒有「短程中速度」這種名詞,是我自己亂定義的。
原本的計畫是,跑300公尺,走100公尺(約休息1分鐘的意思),這樣循環十次;累計起來大概可以跑3000公尺,中速度則可以訓練自己的心肺。不過,所謂的「計畫」,在還沒完成之前真的都只是「計畫」而已,我才跑到第四趟,也就是累計起來才跑了1200公尺的時候,灰雲已經頂不住,雨開始一滴一滴掉下來了。
其實,在暖身的時候,我抬頭看著天空,右邊一大片烏雲,左邊一大片烏雲,只剩中間一條細細白白的縫,沒有雲;那個樣子看起來好像兩片烏雲縫合的時候,天空就會開始下雨。
是在我跑步的時候,兩片烏雲縫合成一大片的嗎?水氣全部集合起來了,雲再也承受不了水滴的重量,變成雨一滴一滴地掉下來。
昨天去江翠國中。九點剛到時候,只有少少的兩個人。後來人陸陸續續出現,到了我要離開的時候,大概有七個人在那兒守著老樹,聊天。
今天去五六運動。去的時間是晚餐後的八點多,聚集的人數大概有100人左右吧。
水氣持續聚集,雲層會慢慢變厚;人持續聚集,有一天一定會下場傾盆大雨,將這個世界清洗乾淨。
2013年5月9日 星期四
2013年5月8日 星期三
跑步日誌(第26天‧20130507)自暴自棄
昨天只跑了三圈。昨天不想寫。
昨天覺得寫文章好累。現在正寫著的自己也是這樣的感覺。
昨天跑的時候,覺得自己真不是一個可以吃苦的人;昨天的我試著把步伐邁大一些,結果不消兩圈就很累。
「我一定是被村上洗腦了,才會來跑步。打籃球不是好玩多了?打桌球不是好玩多了?一直跑一直跑,到底有什麼好玩?有病的人才一直跑……」
說是這樣說,昨天早上的我想到晚上要去跑步,還很開心呢!是在開心什麼咧?
莫名其妙!
慢跑跑不下去了,乾脆休息一下來個衝刺的。好久好久沒有用跑百米的速度快跑了,喔喔喔……身體好輕喔……喔喔喔……原來我的腳步也可以跨那麼大……喔喔喔……快跑的時候感覺自己好像好厲害喔……
不只跑的時候感覺很輕,連跑完以後都覺得自己很輕。
慢跑就不是了,跑著跑著,腳步會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還要繼續跑。
慢跑,真不是正常人會喜歡的運動。
昨天跟今天處於一種自暴自棄的狀態。連寫都是。真是。(雖然我還是努力把覺得該寫的東西寫完了。)
2013年5月7日 星期二
回應法務部回函──所謂的依法行政,是依對自己有利的法嗎?
朋友寫信給行政院,詢問關於法務部拆除華光社區違占戶是否違反「兩公約」,收到了法務部來信回覆。法務部以「人權公約所指之居住權,應係指具合法權利者而言」,表示處理並無不妥。
在最近許多的社會議題中,政府遭疑執法過當,政府已經令人民產生了不信任感。雖然法律不是我們的專業,但我們不能因此讓政府用法綁架,或許自力救濟的方式是──直接走進現場,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解這些社會議題;並參與相關的法學論壇,試著去了解「究竟什麼是法律」。
在一場〈正義或不正義的法?華光社會事件法律考〉法學論壇中,我得知那群一直被法務部指稱違占戶的華光居民,其實是有請求土地所有權的權利的。
民法第769條:「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民法第770條:「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這兩條法律背後的想法,是因應了當時歷史背景,將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與情感包含進去。可惜,這樣的法條對華光社區的居民來說,看得到,拿不到。因為多數的居民並不曉得自己有請求土地所有權的權利;而另一種情況是,當居民知道自己有請求權並且去申請時,被法務部駁回。
因為不是當事者,所以也不清楚被駁回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對土地有規劃,因此駁回他們的請求。但若真是如此,在華光社區裡住了幾十年的這些居民,在「不知可請求土地所有權」以及「請求土地所有權被駁回」的情況下,被法務部稱為違占戶,實在有失公允。
另外,就算被認定為非法違占戶,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4號一般性意見書所提及適當住房權的使用權,其實是包含了「非正規住區」,並非法務部所說的具合法權利者才擁有居住權。
法務部的回函頭頭是道,但仔細去了解法務部並未提及的法條,才知道整個事件仍有其他可能處理的辦法。所謂的依法行政,是依對自己有利的法嗎?
2013年5月6日 星期一
身體還在,但精神已死
這是一篇法務部回應關於拆除華光社區違占戶是否違反〈兩公約〉的文章。嗯,法務部真不愧是法務部,好厲害,好會依法合理自己的不合理行為。每次看到這種東西就很生氣,沒辦法只好又要自己把法條找出來讀(X的!我也想要悠閒地看漫畫看電影呀!),看看究竟是不是法務部說的那麼一回事!
(以下藍色部分為法務部回應,紅色是我標明的重點)
敬啟者,您好:
您於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之電子郵件,經轉至本部處理,有關所陳本部拆除華光社區違占戶,違反「兩公約」一事,本部敬復如下:
一、華光社區違占建戶無權占有國有財產,已違反民法上對財產權之保障,機關依據現行國有財產管理相關法令規定,本於對國家財產權之維護、促進全民福祉與公共利益,並踐行法定程序收回土地,係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第4條規定對相關權利予以限制之要件。況人權公約所指之居住權,應係指具合法權利者而言,華光社區國有土地上部分房屋為不法居民占用,此等不法居民若賴著不走而要求政府給予依法無據之利益,對其他合法住戶且配合搬遷者及全民而言,將造成不公不義,反而是違反公理與居住正義。
我查到的法條與我的解讀: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第四條: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民享受國家遵照本公約規定所賦予之權利時,國家對此類權利僅得加以法律明定之限制,又其所定限制以與此類權利之性質不相牴觸為準,且加以限制之唯一目的應在增進民主社會之公共福利。
法務部用經社第四條來合理化自己拆除華光社區的行為,但是法務部似乎忘了,它的前提應在增進民主社會之公共福利。請問「台北六本木」可以增進多數人民的公共福利嗎?趕走華光居民後在金磚上要起造的建設,我想可能不是大多數公民玩得起的金錢遊戲。
另外,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4號一般性意見中提及「適當住房權」;其中,關於使用權的法律保障,詳列如下:
使用權的法律保障。使用權的形式包羅萬象,包括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設施、合作住房、租賃、房主自住住房、應急住房和非正規住區,包括占有土地和財產。不論使用的形式屬何種,所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以保證得到法律保護,免遭強制驅逐、騷擾和其他威脅。締約國則應立即採取措施,與受影響的個人和團體進行真誠的磋商,以便給予目前缺少此類保護的個人與家庭使用權的法律保護。
法務部一直說華光社區居民非法,先不論這「非法」是否有其歷史因素,從意見書中可以看到──就算是非法也受到保障。這並不是說法律要保障非法,而是說法律也會顧到非法者的一般人權。政府應該要進行「真誠」的協商,而不是「程序上」的協商;不是「我有發文給你喔,我有要找你們協商喔,是你們自己不同意協商條件,沒辦法我只好告你們。」
◆
二、按經社文公約第11條第1項規定及第7號一般性意見第11、13、14及15點,雖敘明人人有免遭強制驅逐、騷擾和其他威脅之權,但並非所有的驅逐行為都是不合理的。驅逐如係按照與「公約」不相牴觸之法律規定執行,且被驅逐的人有可資援用的法律救濟途徑;驅逐行動牽涉到多數人時,已先與受影響的人磋商,探討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以避免或儘可能地減少使用強迫手段;執行時也已嚴格遵從國際人權法相關規定,符合合理和適當比例的一般原則;並提供被驅逐的人適當的法律程序上保護,則此類驅逐當屬合理。
我的解讀:這個我前面寫了。政府該做的是實質上的協商,而不是程序上的協商。法務部究竟有沒有跟華光居民探討「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以避免或儘可能地減少使用強迫手段」?去問一下華光社區的當事者就知道了。
◆
三、又國際人權專家於今(102)年3月1日出具之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第47點雖對華光社區表示關切,然而,本部所屬機關於95年間(兩公約於國內施行前)進行相關土地全面清查工作,確認土地遭占用之狀況後,即已先透過聲請調解之程序,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提出減免不當得利等有關義務之替代方案與居民進行協商,對協商未果或無法成立調解者,始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且訴訟案判決前依法仍有替代方案可據以協商成立和解,判決後亦可透過上訴程序進行救濟,相關處理過程已符合前述第7號意見第11點、第13點之意旨;同時,有關強制執行時應遵循之原則及程序,均係透過法院依據相關法令辦理,亦注意法律程序之各項保護,執行時並酌量個案狀況進行疏處,已符合第14點及第15點之規範;
又本部所屬機關於處理過程中發現違占建戶屬弱勢者,已適時通報相關社福機關介入了解確認及協助處理,以避免其中確屬弱勢者因配合拆遷而有無家可歸之狀況。綜上,本部所屬機關依據法令規定,循法定程序辦理拆遷工作,係屬具正當性之行政作為,符合國際人權標準。本部希望各界以理性態度來看待華光社區拆遷問題,共同維護社會公益與居住正義。
我的解讀是:法務部說了一堆自己如何如何協調,如何如何幫助弱勢,其實這個部份,去到華光現場,就會知道根本是屁。其中有個法務部絕對不會提的事──法務部一直說華光居民非非,但是當華光居民去申請合法的土地所有權時,全部都被法務部駁回。
民法第769條:「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民法第770條:「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這兩條法律背後的想法,就是因應當時歷史背景,將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與情感包含進去。可惜,這樣的法條對華光社區的居民來說,看得到,拿不到。多數的居民,並不曉得自己可以去請求土地所有權;而當法務部來告他們,他們才知道有請求登記土地所有權這回事;而當他們請求登記土地所有權時,卻受到受理單位的百般刁難。
「你們住在這塊土地上,是以什麼樣的意思?是『所有』的意思,還是『使用』的意思?」
一般的民眾根本搞不清楚他問「所有」跟「使用」,到底用意是什麼?像我,我就覺得土地又不是生產的,當然不是我所有,我只能使用它;所以,如果是我可能就會回答「使用」。但這樣一來就糟了,因為辦事人員會笑嘻嘻地指著法條說:「這上面寫,要以『所有』的意思。」
那如果我改口說,喔喔喔,我的意思是,我使用這塊土地這麼久了,幾十年了,我想我應該擁有這塊地的所有權……(不過老實說,我個人還是一直覺得人能夠擁有土地的所有權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是沒辦法,如果我不想被趕走,我只好這樣說)
這時辦事人員可能就會要求你:「那麼請你舉證,你當初在這塊地上蓋房子,是以『所有』的意思,而不是『使用』這塊地的意思……」
我的天呀!這是在玩文字遊戲嗎?我可以說這樣根本就是刻意刁難嗎?完全違背了那兩條民法當初設立的善意。
我終於明白法律死了是什麼意思──就是身體還在,但精神已死。
2013年5月5日 星期日
跑步日誌(第25天‧20130505)一直跑一直跑,當然一定會跑到某個地方;但卻不是為了那個地方而跑。
晚上六點四十分,室外溫度24度。十圈,4000公尺。
一圈一圈跑著時,我想起昨天公視播的《前進南極》登頂畫面。「這就是南極的最高峰嗎?這就是文森峰嗎?」畫面中的人一面說著,在電視前的我一面看著他所見到的風景。
「這就是南極的最高峰嗎?這就是文森峰嗎?」他說了不只一次,好像有一點不可置信,「就是這樣嗎?這就是南極的最高峰文森峰?就是這樣嗎?」
當然我無法體會說話的人的心情。因為我在電視機前,而他在文森峰上。我們聽著畫面中的人說著「就是這樣嗎?就是這樣嗎?」的時候,Y問,那些人究竟為什麼要跑到那麼遙遠那麼艱困的地方?這句問話的意思其實是──做這樣的事,到底是為了什麼?
「就是這樣嗎?就是這樣嗎?」聽起來有一種「我們那麼那麼辛苦,走過了自己一開始都沒有想像過的辛苦的路,來到的這個地方,就是這樣嗎?」我無法知道他們真實的心情,但是那句話聽起來的感覺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嗎?」不代表那些人失望。「就是這樣嗎?」想著這句話的同時我突然覺得,所有事情的意義都只在那件事情本身而已。最後你所去到的地方,就只是最後必定會到達的終點;不論那個終點,是不是一開始所預期的終點。
我一圈一圈跑著;跑了兩千公尺,跑了四公里;或許以後可以跑十公里,也希望有機會能夠跑馬拉松。但並不是為了馬拉松而跑著,也不是為了任何的什麼而跑著。
或許一開始是。但是,在跑著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就只是在跑著而已。雖然跑就一定會向前,卻不是為了向前而跑。
一直跑一直跑,當然一定會跑到某個地方;但卻不是為了那個地方而跑。
你可以從新店跑到淡水,也可以坐捷運去。你跑去淡水並不是為了去淡水,而是為了跑去淡水。
跑步日誌(第24天‧20130504)下午兩點半,那個男人穿著剛剛好短的短褲
這天是五四,晚上有關廠工人晚會。下午兩點半去跑步,跑回來之後吃老斌包的水餃,然後去小小,接著去關廠工人晚會。
忘記是下午兩點半,穿了黑色的T恤。還好室外溫度只有24度,不太熱,有微風,也有大片的雲。
跑第一圈的時候鞋帶鬆了,不得不停下來好好把鞋帶綁好。在跑之前就應該先檢查鞋帶的。跑到一半停下來,呼吸都不順了。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樣,今天只跑了八圈,而且喘喘的。不過我想這應該是藉口吧。
大概是因為是下午兩點半,操場上一開始只有我一個人跑著。後來有一男一女外國人加入。他們經過我的時候,我的眼睛很難離開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是外國人,而是因為女生腿長而且穿細肩帶,男的則是只穿了一件剛剛好短的短褲。
那短褲是這樣的──如果上半身中間細進去的地方叫做腰,那麼那件短褲剛好卡在腰部下方七、八公分的地方。從視覺上來看就是再下去一點就要看屁股了。雖然跑步的時候很多男人都裸著上半身,不過穿得那麼低的短褲,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不過也多虧了他穿得那麼低,他跑到我前方的時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腰部的肉,隨著他一步一步往前跑而晃動著。嗯嗯,看來跑步也是可以瘦腰,雖然腰部應該不是主要運動到的部位。
那一男一女都跑得很快。不過女生沒跑太多圈就停下休息了;短褲男人則是繼續跑著,跨步很大,很難不去看晃動的腰肉。
2013年5月4日 星期六
2013年5月3日 星期五
跑步日誌(第23天‧20130502)跑完10圈的這一天
跑完10圈的這一天,距離3月17日,隔了46天。差不多是一個半月的時間。
室外溫度20度,時間是晚上七點鐘左右,我花了大概35分鐘,跑完四公里。
3月17日那天,在不休息的狀態下,那個時候的我只能跑4圈,也就是1600公尺。嗯,不曉得能不能這樣算──我現在的體力,大概是3月17日的2.5倍。
跑完10圈的這一天,沒有想像中的有什麼;大概是因為循序漸進地跑吧,跑10圈是想當然之中的事。接下來的目標是10公里,也就是25圈。
老斌說你不行啦!你那麼肉腳。我說我那麼肉腳還是有腳呀,慢慢跑一定還是可以跑完的。一點一點地增加,10圈、12圈、15圈……慢慢增加下去,有一天一定可以跑完25圈。
那個時候我可以買美津濃的慢跑鞋嗎?
● 跑步日誌(第八天‧20130317)不曉得一次可以跑10圈的那一天,是什麼樣的日子?
明天
明天為什麼是明天呢?
是天明之後就是明天
還是明聽起來像眠
睡了一眠,醒來就是明天
可是有時無法入眠
有時天黑壓壓地無法天明
看不到明天
明天好像不來
但是明天還在
明天沒有不見
無法入眠
但依舊閉上了眼睛
明天再見
(給關廠工人、苑裡反瘋車、華光、拉瓦克部落、以及所有的被壓迫者)
2013年5月2日 星期四
【樸食的人】桂先生
桂先生不姓桂,而是名字裡有個「桂」字。
桂先生的老家在高雄。
會特別提起桂先生的老家是因為,有一回他來拿便當的時候說:
「我老家在高雄……,我阿嬤……」糟糕,我的記性真差,「……」的部分代表我忘記了。我只記最後一句話:「所以我的名字裡面有一個『桂』字。」
雖然他前面說的我都忘光光了,但是對於他名字裡的「桂」字與他的家鄉有關,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他在說的時候,有一種──
「嘿!你的老家也在高雄,你應該知道為什麼我的名字裡會有『桂』吧!」
「我的名字裡面有『桂』字,你知道吧,這樣你應該知道我住在高雄哪裡吧……」
我有這樣的感覺。
而對於他覺得我應該知道的事,我這個「高雄人」可是一點都不知道。
後來,我把「桂」跟「高雄」丟進google,發現高雄小港區有好多「桂」字頭的街──桂文街、桂華街、街江街、桂誠街、桂忠街、桂仁街、桂州街……
這一查,嘿!桂先生的名字跟其中一條街的名字一樣耶(同音不同字)!嗯嗯,那麼桂先生的老家應該是在高雄小港區的某條桂字街上吧……(自己亂猜)。
怎麼一直繞著桂字打轉呢?
桂先生第一次訂便當的時候,我跟老斌一直在猜這個人是女生還是男生(因為他的名字很中性)。後來見了面當然知道是男生;是一個任勞任怨、為民服務的男生。
這樣形容他可能有點太誇張了。不過,從他去年六月幫他自己和他上班的公司訂便當到現在,他是唯一的值日生;訂便當是他幫大家訂,拿便當也是他幫大家拿。有幾次是另外一個女生來拿,但那是因為桂先生放假或出差。有時候我在想,吃飯的事每個人都有份,不管是老闆還是同事,輪流一下當個值日生,是不是比較好呢?不過我沒有這樣直接問桂先生,因為他每次都匆忙地來拿便當又匆忙地走。
每次來拿便當,我按了對講機開了外邊大門,桂先生總是小跑步進來,問了我今天便當多少錢然後寒暄個幾句,馬上又小跑步離開。「有沒有那麼趕呀?」我這樣想。後來才知道,銀行工作某些職務好像沒有午休時間,要自己抓緊時間吃飯;像桂先生還要幫大家拿便當,吃飯時間想必更是少之又少。
雖然我們說話的時間很少,不過桂先生還是會在這短短的時間中發現一些小小的事。有一次,他看到我們掛在窗邊的絲瓜布,就說:「我媽都會自己曬絲瓜,下次我回高雄再帶一些上來給你們。」下次他來拿便當的時候,果然帶了一整袋絲瓜布來。我們問他要多少錢(因為我們在台北買都要錢),他直說不用不用,反正媽媽平常都在曬,曬好的絲瓜都拿來送給人。
「不過在用之前,要記得先把絲瓜裡面的子打出來。」拿便當離開前,桂先生這樣提醒我們。
叫他「桂先生」,聽起來好像有點年紀;其實不是,他跟我和老斌年紀差不多,而且平常我們其實是連名帶姓三個字叫,像叫國小同學那樣。
有些人好像就是很有那種服務大家的心腸,像我就沒有。我就是看心情,很任性。
大家都到齊了,可以開始討論了。
「嗯嗯,大家都到齊了,可以開始討論了。」
「叫我們來是要討論什麼呀?」
「今天早上……新北市政府開了一場江翠國中『樹木移植說明會』……」
「ㄟ……什麼!我不知道耶!」
「我們怎麼會知道,他又沒有找我們植物代表出席……」
「喔喔……那怎麼辦?他們想要做什麼?」
「因為沒有被邀請,所以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想幹嘛……,不過也沒什麼好驚訝的,他們人類做事從來就沒有問過我們呀……
「對呀對呀,說要保護我們,其實也只是把我們當做『資產』……」
「把我們移來移去……」
「你有聽過樹木銀行嗎?」
「那是什麼?」
「就是存我們的地方啦!」
「什麼?我們又不是錢!」
「聽說錢存進銀行會變多,那如果我被存進樹木銀行,我也會變大嗎?」
「傻TREE……還沒進去之前,你就會變小了……」
「ㄟ……我現在已經很小了耶……」
「不過江翠國中的那些老樹好像不是要存到樹木銀行耶!」
「那人類要把他們搬去哪裡?」
「好像是泰山……」
「泰山……那個喔咿喔的泰山嗎?」
「不是那個泰山啦……」
「聽起來好像很遠……」
「會死掉嗎?」
「已經很老了又搬那麼遠……可能會死掉喔……」
「那怎麼辦怎麼辦?你告訴我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們人類那麼厲害!」
「那我們來絕食抗議好了!」
「傻TREE,你又不是人,絕什麼食?」
「反正長大以後還是會被他們砍掉,不如我自己先絕食好了……」
「長什麼大……你是薑芽耶!」
「喔喔……所以我不會長大喔……」
「嗯,我們已經被摘下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
「嗯,那個把我們放在紅色桌子上,讓我們假裝說話的人說,等我們開完會討論結束之後,她就會把我們放到盆栽裡。」
「喔喔……那我們會長大嗎?」
「就跟你講我們不會長大啦!不過應該會變成土吧!」
「那江翠國中那些樹要怎麼辦?」
「留給那個把我們放在紅色桌子上的人去傷腦筋啦!畢竟禍是他們人類闖出來的。而且他們人類那麼厲害,越厲害的人就是要負起越多責任呀!不然那麼厲害是要做什麼?來破壞全世界嗎?」
2013年5月1日 星期三
跑步日誌(第22天‧20130430)安靜著但仍有強度
今天跑了八圈,3200公尺。
還是覺得肌耐力這件事非常神奇。嗯,應該說,因為反覆進行同一個件事,而從中獲取力量的這件事,很神奇。雖然,人都是這樣長大的;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們「不知不覺」地因為反覆同一個動作,比如用爬行,比如搖搖晃晃地用兩隻腿往前進,比如用手指抓東西;我們反覆地使用或操作自己的腳、腿,和手;我們不斷地看,不斷地聽;我們學會了走路、學會了握筆寫字,學會了說話。
這些與持續跑步,不完全相同。但相同的是,因為長時間持續地跑步,我的大腿和小腿肌肉耐力變強了;就好像小時候剛開始走路腿還不夠有力,總是歪歪斜斜,但走著走著,兩隻短短的腿,漸漸地越來越有力氣了。
不同的是,小時候的我並不意識著自己身體的變化(或許有意識,但我忘了?);而現在我卻是在感受著自己身體的情況下,發現自己身體的變化。小時候的自己就那樣成長著,長到有一天再回頭看小時候的自己,才突然發現已經長得不一樣了;而現在的我仔細觀察與感覺在跑步的自己,記錄那些微小的改變。
今天,在跑第五圈的時候,我以為自己今天想跑十圈的話,應該沒問題。但「以為」永遠只是「以為」,事情還沒發生都不算數。跑第六圈的時候,大腿外側開始有點微痠,也開始覺得喘了;第七圈跟第六圈差不多;第八圈跟第七圈差不多。當第八圈跑完的時候,我的腿和我的心臟我的肺都覺得累了,但如果我想要逼她們再跑一圈,她們應該也是會承受下來;不過我自己覺得今天夠了,就先這樣好了。
在跑步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這些,感覺到自己的腿的強度,自己心臟的強度。但是當我平常在說話的時候,打電腦寫文章的時候,吃飯的時候,吹頭髮的時候,我完全感覺不到自己的腿和心臟的強度。這麼說並不正確,腿和心臟在不需要她們發揮強度的時候,她們當然不會發揮,我當然就感覺不到。應該這麼說比較接近──現在的我和跟兩個月前的我做著一樣的事,一樣吃早餐,一樣陪斑斑玩;但是我的腿和心臟不一樣了,但是不跑步的話,不會發現。
這些好像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但好像又不是不知不覺。跑步的時候我感覺著我的身體;不跑的時候她們就安靜著;安靜著但仍有強度。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