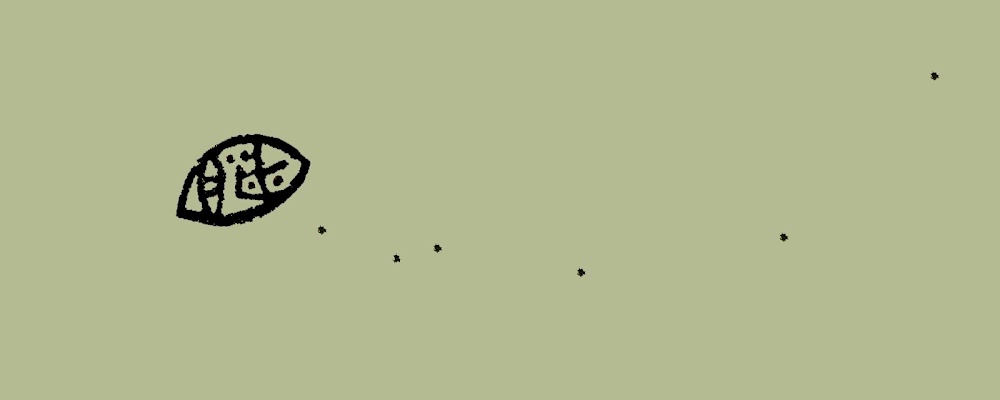寫《滌這個不正常的人》之前,我沒想到有一天我會參與繭居議題論壇。那時繭居對我來說,還是個人的問題,屬於「我們家」的問題。開始與滌對話,書寫之後,我才慢慢地跨了出去,先是與宋文里老師取得了聯繫,開啟了我對心理治療不同的看法,透過與宋老師對話以及閱讀羅哲斯的《成為一個人》,我梳理了自己的害怕與擔憂,也因此能更進一步去面對我與滌對話時所遇見的困難。但這些仍然不夠。
我說的不夠是指,我期待能夠有用。不是指這本書必須有用,而是我期待自己能做些「更有用」的事。更有用指的是什麼?滌願意改變?願意走出去?我不是說我只是想跟滌好好說話嗎?我並非想指導他?但為何我又覺得不夠?
讀《空橋上的少年》時,我也讀到了類似的矛盾──
「我只是在想,也許,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你回學校。那可能是一開始我找你會談的原因,但今天我坐在這邊聽的時候,我愈來愈覺得,那並不是我和你會談的目的,也不應該是。」
「……月底又要開會討論你這件事,我總還是有種,如果沒能夠讓你回到學校,作為一個醫師,我的治療好像失敗了的感覺。」
以上兩段對話,出自蔡伯鑫與拒學少年張朋城的會談。蔡伯鑫是《空橋上的少年》的作者,也是個精神科醫師,而張朋城是青少年日間病房的個案。我似乎很能明白蔡伯鑫的矛盾,這矛盾並不對立,而是真實。
作為想了解對方,與對方建立關係的人,我們著重在「當下」好好與對方說話,說話的時候不去想「有沒有用」,就是好好的聽對方說,並把自己說出來。但我作為滌的姐姐,我同時感受到除了對話當下之外的現實,那包括了滌與父母同住所導致的彼此生活空間的限縮、心理壓力,以及對於未來的擔心,包括生活照顧與經濟。那是清清楚楚的問題,不是「好好對話」就能解決。而蔡伯鑫作為張朋城的醫生,我想他所面對的是類似的現實,比如個案的求學之路、管道,能給對方什麼建議?如何協助個案處理家人關係?
對話很重要,但單純只有對話無法解決現實問題。對話是基礎,但我需要更多的資源來協助我面對現實課題,比如:「如果滌表達想要工作的意願,但畢竟他與社會脫節近十年,我能做些什麼減低阻力?社會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或是「現在只有我可以跟媽媽談滌的事,但媽媽會不會需要其他人跟她談?比如心理師?或是類似我們家情況的家屬?」「如果我自己想更多了解心理諮商,我還能做些什麼?有哪些管道?」
寫完《滌》之後,我開始思考這些現實問題,一步步找尋資源與方法,希望自己能走出去更多一些。但似乎有些晚了。或許不該說晚,而是當我準備再做些什麼的時候,滌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
在繭居論壇中,伯鑫問我,你接下來還會想參與跟繭居相關的活動嗎?我說,我不確定自己在這件事上能出多少心力,但如果我遇上了,我能做些什麼就會試著去做,「因為我明白那種孤立無援,不曉得方向在哪的感覺。」
「雖然滌離開了,但類似處境的家庭一定存在。像今天這樣的論壇,光是能將因為繭居而遇到困難的人聚在一起說說話,就是個很好的開始。」
異化、孤立感、重新整合
當天的論壇約三十多人參與,而所謂的「因繭居而遇到困難」的人並非都是繭居者本人,主要是繭居者的手足與親屬,其他是關注繭居議題的心理師或社工。早上先安排了兩場講座,接著是小組討論。我與伯鑫是當天的講者,我對他的演講非常有共鳴,他提出的每一個觀點,幾乎都能對應上我對滌的觀察。
伯鑫說,他面對的個案是拒學,而非繭居,因此他分享的是拒學者的案例。其中一例個案說,覺得自己與他人對話是「浪費時間」,覺得「自己跟所有人都融不進去」。聽到這時我想起滌,想起滌不想與他人對話也是因為覺得浪費時間,「他們都是白癡」,滌曾這樣表達心裡的不屑。
但為什麼那位拒學者會這樣呢?為什麼滌會這樣呢?「他為什麼不想與他人連結?」「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這是拒學者與繭居者家屬都想問的問題。
伯鑫在分享中提出三個詞彙(先說明,這是提供思考與討論的方向,並非定論或研究成果)。第一個詞彙:Alienation,這詞出自於馬克思,翻譯為異化或疏離,原意是指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線中被工具化,失去了人該有的樣子。伯鑫將此概念延伸到拒學──我們的學校是否將學生工具化了呢?拒學的孩子是否因為不想被異化而拒絕上學呢?學校無法讓學生成為他自己的樣子,無法適應者便逃離學校?
我忍不住想到滌。那麼滌呢?滌不是他自己的樣子嗎?我一直覺得滌是他自己的樣子。但仔細回想,滌在必須當兵時,無法是他自己的樣子,在投入職場時,無法是自己的樣子。那些必須標準化的環境,是滌之所以繭居的原因嗎?那麼滌就學時期為何沒有拒學呢?是因為他的學業表現使得他獲得成就感嗎?(這是另一個需要花篇幅思考的問題)
第二個詞彙:Isolation,孤立感。因為不想被異化,因此拒絕上學或繭居在家。但這只是單純的不上學或不進入社會嗎?這只是單純的挫折嗎?伯鑫提到「孤立感」這個詞時,我想到了兩種狀態──
1. 一個是「心理」上的孤立──雖然覺得跟別人說話是浪費時間,但心裡仍舊渴望對話,卻找不到那個可以說話的對象
2. 另一個是「現實生活」中的孤立──不想融入主流社會,但也找不到可以自立的方法
這樣整理起來,似乎只要解決當事人心理上與生活上的孤立,問題就解決了啊?問題是──這兩個問題本身就是困難的問題── 一旦當事者拒絕對話,要再開啟對話需要極其漫長的過程;而當事者既然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大眾對他的期待卻是「只要去找工作就好啦」,那麼進一步退兩步的過程只是讓他們越退越進入那個繭居的殼。
來到第三個詞彙,Reincorporation,重新整合。不是要他們變回「正常的樣子」,也不是要他們回去那個他們逃離的網絡,而是重新找到對話的方式、有別於過往工作的模式。但這樣說起來好籠統,具體的方法是什麼?要是具體方法能那麼快出現,問題也就不會是問題。那這樣談「重新整合」有用嗎?我認為至少是個開始,至少,我們知道方法不會是把離開的人塞回去。
繭居是一種病嗎?繭居是一種問題嗎?
「繭居是一種病嗎?繭居要如何定義?一個人如果只是喜歡待在家裡,不造成別人的問題,自己覺得舒服自在,這樣的繭居不行嗎?」當天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伯鑫先以精神科醫師的角度說明,繭居不是一種病;當然,有人可能因病而繭居,但那不是患了一種「叫做繭居的病」。但這就牽涉到定義,如果「繭居」只是在生活上與心理上不喜與人接觸的生活型態,與啃老或尼特這樣的詞彙相比,它相對中性;因為繭居未必啃老,未必無法自食其力。
不過,「繭居」如果圈得那麼大,那麼有很多是不需擔心不需處理的。但今天這個繭居論壇想要討論的,是指繭居造成當事者的困難,與繭居者同住之家人的困難,或是更擴大,擔心造成對社會的影響。我們想處理這些困難,但對繭居的了解極少,對於該如何處理自己面臨的問題,也沒有頭緒。因此這個論壇,是邀請繭居者本人或繭居者家人,或關心繭居議題的心理師或社工,先交流彼此的困境,再將討論整理成政策建議。
能把無法說出口的話說出來,就是一種自我療癒
因此小組討論也是當天的重點,我與伯鑫幾乎參與了全程。小組討論分三階段,礙於討論的複雜度與內容龐大,我無法做細部的分享,僅分享我在情感上最深刻的感受──
現場有位參與者,她在我與伯鑫分享完之後發問:「如果對方就是不願意說話,到底要怎麼開啟對話?」我說:「對話很難,一開始總是會被拒絕,必須來來回回。」我說完後覺得自己的回答很籠統,但我們也不可能在當下就給出辦法。後來分組,我與那位參與者同組,我才知道她的身分是媽媽。那天大家都戴著口罩,但她說話時聲音哽咽,似乎要哭。我馬上對應到自己的媽媽,開始想像她所承受的壓力,那壓力與其說是生活經濟上的負擔,更多是因為沒有情緒的出口。我發現與手足相比,父母容易將繭居者之所以繭居歸咎在自己身上,他們想要改變現況卻苦無辦法,更苦的是無處可說。
而相較父母可能會有的自責心理,手足則是擔心無力承擔。不一定是沒有意願,而是擔心自己沒有能力,或是不想被要求,被認為自己該為對方的人生負責。「有沒有可能有那條線,告訴我其實沒有法律上的責任,我可以憑著自己的能力與意願來決定要做到哪裡?」一位參與者提出這樣的想法。擔心無力承擔,卻也容易有「罪惡感」──他在那裡駐足不前,爸爸媽媽跟他一起被困在那裡,我可以自己一個人過好生活嗎?
這是很矛盾的情結。一方面不希望因為手足繭居,自己也因此被綁住;但另一方面卻又對自己過著「好生活」有罪惡感。這與我在書寫滌時的感受十分雷同,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感覺;但後來我發現,先把自己的生活「過好」,父母才不用再多擔心一個孩子;我把自己的生活過好,才有能力再去做些什麼。
當天的場合製造了一個能讓大家抒發的機會──因為彼此不認識,不用擔心人際關係,不用擔心某個親戚會怎麼說,不用擔心自己的同事或朋友或怎麼看;彼此不認識卻擁有相似的困境,自己說的話對方似乎都懂。
能夠有機會,將無法說出口的話說出來,就是一種自我療癒。
--
註:文中所提的繭居議題論壇,指的是由「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所推動110年青年好政 Let's Talk 系列活動,以「探討青年繭居的樣貌、需求與繭出之路」為題辦理之公共審議論壇。詳細活動內容請見網址:https://reurl.cc/akY8nD
──刊載於 OKAPI: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5595?loc=writer_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