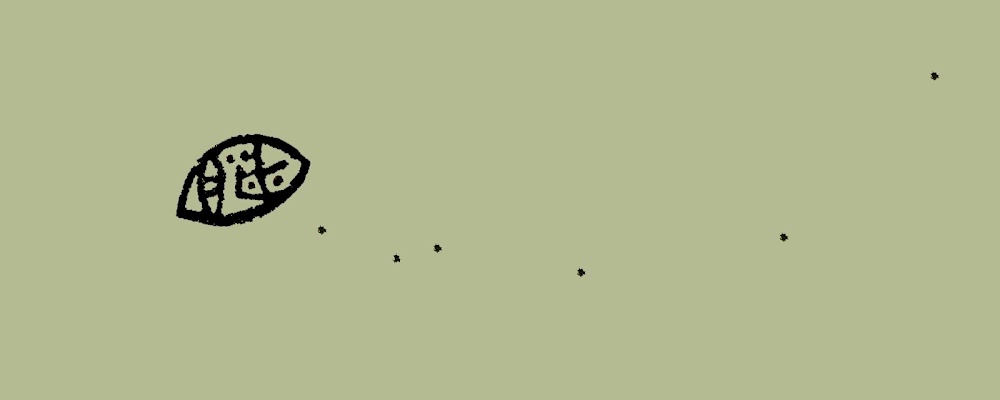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鹽澤,跟你說個祕密吧──
聽說,每個人總有一天都會死呢。」
──松本大洋,《東京日日》
◆
忘記是幾月,讀完《東京日日》。讀完時好捨不得,什麼時候才能等到第二集?還未翻開時,我以為這是一集就結束的漫畫,但明明人家封面上有個「1」。
「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你的漫畫給人的感覺都是空蕩蕩的。」
鹽澤這樣對長作說,我讀到時心臟快跳出來。現實世界真的有編輯會這樣對作者說嗎?尤其對方是人氣漫畫家,這種情節大概只會出現在漫畫吧?像是《響──成為小說家的方法》,裡頭也有這種指著人氣作家劈頭就罵的情節。不過,這位鹽澤先生客氣多了,說完後補了一句:「啊……抱歉……這畢竟只是我個人的感想……請不用太過放在心上。」
怎麼可能不放在心上?尤其當對方說的,作者自己本身也知道。
「空蕩蕩……?拎北才想要哭哩……還用得著你說……我當然也……」長作心想。
我當然也什麼?廢話,我當然也知道自己的作品空蕩蕩,還用得著你說?我可是作者呢!自己畫的東西自己知道。明明知道,卻假裝不知道;明明是那麼回事,卻假裝不是那麼回事。要等到有人直白的說出來,說出大家都知道但不敢說的廢話。「還用得著你說……」但沒有人敢在長作面前說。
這種廢話不是既存事實,是心知肚明。心知肚明但沒人敢說,因為不容易說,但編輯鹽澤說出來了。這種是沒人敢說的廢話。
還有一種是,明明大家都知道,卻經常忘記的廢話。
「聽說,每個人總有一天都會死呢。」立花老師這樣對鹽澤說。
廢話,每個人總有一天會死,誰不知道,還要你說。但這個大家都知道的廢話,卻經常被忘記。這種廢話是既存事實,但不一定不用被說。而最有力量的廢話是,明明大家都知道,卻經常忘記。直到有人說,才突然醒過來,對耶,是耶,是這樣沒錯。
對編輯來說,對漫畫家來說,對寫作者來說,人生都只有一次。真是廢話。可是明明知道是這樣,卻花了大半時間在編在畫在寫空空的東西。「但這還要你說嗎?我也知道人生只有一次,總有一天會死,我也不想要空空的啊!」
所以有些廢話真的是很厲害。讀到「聽說,每個人總有一天都會死呢。」當下沒發現這是廢話,因為有鋪陳(小元子你說得沒錯)。立花老師過世,鹽澤去上香,想起了立花老師生前在轉換風格後所說的話。讀到那句話的當下只覺得,對耶是啊我有一天也會死喔。所以呢,身為寫作者,當然是要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像立花老師一樣。
明明是廢話,卻再次被提醒了。當然,常常被提醒可能就沒感覺,就麻木了,廢話便失去了它的力量。這樣說來,廢話本身並沒有所謂的力量,而是看它出現的時空,以及接收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