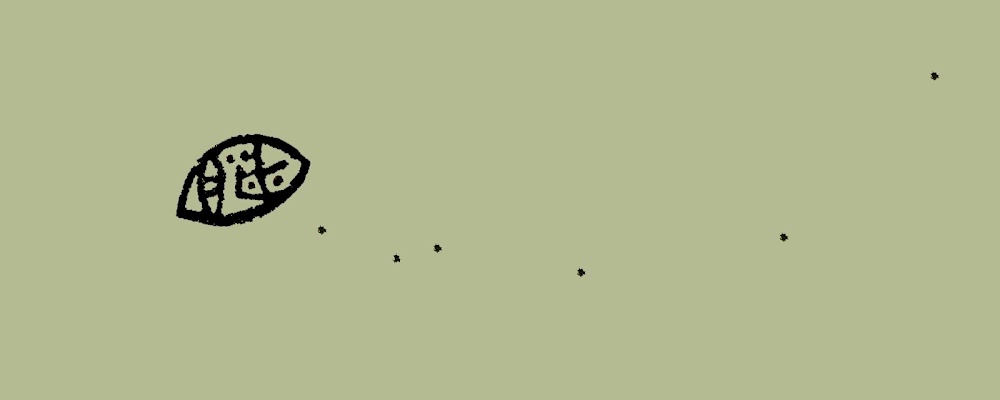因為朋友的介紹看了《年少時代》。這是一部,跟著時間會越來越進去的電影。剛開始還沒有什麼太深的感覺,你就是看著一個小男孩長大,一個小女孩長大,家庭生活、學校生活、感情生活。但當一個人十二年的生活,濃縮在三個小時裡,我看到了一個人的樣子,一個人從那樣變成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是真的看到,不是假設性的看到,不是換一個人來演。因為這部電影拍了十二年。雖然那個小男孩是在演一個角色,但那個小男孩確實從六歲長成了十八歲。
這部片我分兩次看,昨天我看那個六歲的小男孩,我無法想像他十八歲的樣子,我當然想像不到。而我好奇這部電影的編劇,他怎麼想像這個小男孩長大的樣子,他要給這個男孩什麼樣的故事?要如何決定這個男孩的角色性格?
劇情不是最重要的主軸,重點是人物的經歷與變化。那些經歷形塑了一個人的變化,是這部電影裡最最細緻的東西。男主角梅森的表情,他眼睛看事物時那似乎在想著什麼的神情,電影結束在十八歲的梅森與剛認識的朋友坐在沙灘上,兩人的說話與互動。電影結束,但梅森的故事還未結束。
看完後查資料,才知道編劇導演就是那個拍《愛在黎明破曉時》三部曲的編導。
2020年6月27日 星期六
2020年6月26日 星期五
從《十二怒漢》思考合理懷疑與人民參審
人家聽Podcast都是輕鬆的聽,我聽Podcast卻是超認真。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聽廣播的習慣,從小就沒有。我少數聽的Podcast,是懷哲的Podcast,是一邊縫衣服邊聽,像是聽朋友聊天(確實也是在聽朋友聊天)。但這次聽黃致豪律師的法客心法,我卻無法一邊做什麼事一邊聽,因為關於法律的部分我就是很想要記錄下來啊!
這集在講《十二怒漢》,從《十二怒漢》來談人民參與司法決策。題目聽起來很硬,但聽起來不會。但對我來說前面電影簡介的部分有點長(笑),因為我想聽的是法律啊XD
(不過《十二怒漢》確實是超級厲害而且必看的電影,拜託有空有興趣的人都去找來看!)
◆
關於「合理懷疑」這個東西,我覺得不管遇到幾遍,都需要再重新想一下。因為人真的很難不先入為主,很難沒有刻板印象。
「如果你們有合理懷疑,就要判無罪。」
什麼叫「合理懷疑」?當你對案件的構成要件、主要判罪細節,如果你發現有任何「合理疑慮」的問題,那就是合理懷疑。法官對陪審團說,如果你們有合理懷疑,那就要判被告無罪。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問出你覺得有合理疑慮的問題,如果沒有任何一個問題可以問得出來,你們找不出這個案件有任何值得被懷疑的問題,那這個案件就沒有合理懷疑(「負負為正」的句型真是很繞口又燒腦XD)。
這個負負得正的句型意思是說,如果你完全找不到任何值得懷疑的問題,那麼就該判被告有罪。
有些人可能會問,所以只要在證據上有「疑慮」,就不能判被告有罪喔?這時我想起黃律師提過刑法中的「謙抑思想」。因為刑法可以剝奪人的自由、財產,甚至剝奪人的生命,所以審判者理應排除所有的可能性,確認沒有無罪的可能,才能判有罪。
我找出《十二怒漢》的劇本,法官對陪審團講的話是這樣的:
「本案已經有一個人死亡,而另一個人的生死掌握在你們手上。倘若你們可以提出合理的懷疑,無法證明被告有罪,基於合理懷疑,陪審團就應作出無罪認定;如果找不出合理懷疑,你們必須基於良知,判決被告有罪,你們的決定必須一致。如果你們判被告有罪,本庭將會對他施以嚴厲懲罰,最高的刑罰會是死刑,這是一項沉重的責任。」
◆
這集有另一個法律觀點是我第一次聽,那就是人民參與審判的機制。黃在節目中簡單介紹了兩種機制:一種是「陪審制」,一種是「參審制」。
我在這裡不多加簡介,想進一步了解的人請自己搜尋關鍵字。我想分享的是,原來陪審團制度最早的起源是「同儕審判」。同儕審判簡單來說,就是去詢問與被告背景相似者的意見。這讓我發現法律設計的其中一個面向,從小就聽過「情、理、法」,所以同儕審判就類似「情」的部分?考慮被告者的背景、社經地位、處境,進一步了解被告可能的犯案動機,以期能做到罪責相當的判決?
而日本的「國民裁判員」制度則是類似「陪審制」與「參審制」的混合,由6名裁判員及3名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最後一起投票決定。這個制度聽起來很不錯,好像人民的意見與法官的意見都顧及了,我想當初設計的用意也可能如此。但黃在這裡提了一個需要注意的論點,那就是當一般民眾與法官一起在進意見交換討論時,民眾會不會容易被相對來說有「權威」身分的法官影響?
台灣之後要推的「國民法官制度」,就類似日本的國民裁判員制度。啊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寫可以想的,但我好像寫太多了。有興趣的人請自己聽這集Podcast。
→法影Ep. 1《十二怒漢》,怒什麼?談人民參審與司法決策
這集在講《十二怒漢》,從《十二怒漢》來談人民參與司法決策。題目聽起來很硬,但聽起來不會。但對我來說前面電影簡介的部分有點長(笑),因為我想聽的是法律啊XD
(不過《十二怒漢》確實是超級厲害而且必看的電影,拜託有空有興趣的人都去找來看!)
◆
關於「合理懷疑」這個東西,我覺得不管遇到幾遍,都需要再重新想一下。因為人真的很難不先入為主,很難沒有刻板印象。
「如果你們有合理懷疑,就要判無罪。」
什麼叫「合理懷疑」?當你對案件的構成要件、主要判罪細節,如果你發現有任何「合理疑慮」的問題,那就是合理懷疑。法官對陪審團說,如果你們有合理懷疑,那就要判被告無罪。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問出你覺得有合理疑慮的問題,如果沒有任何一個問題可以問得出來,你們找不出這個案件有任何值得被懷疑的問題,那這個案件就沒有合理懷疑(「負負為正」的句型真是很繞口又燒腦XD)。
這個負負得正的句型意思是說,如果你完全找不到任何值得懷疑的問題,那麼就該判被告有罪。
有些人可能會問,所以只要在證據上有「疑慮」,就不能判被告有罪喔?這時我想起黃律師提過刑法中的「謙抑思想」。因為刑法可以剝奪人的自由、財產,甚至剝奪人的生命,所以審判者理應排除所有的可能性,確認沒有無罪的可能,才能判有罪。
我找出《十二怒漢》的劇本,法官對陪審團講的話是這樣的:
「本案已經有一個人死亡,而另一個人的生死掌握在你們手上。倘若你們可以提出合理的懷疑,無法證明被告有罪,基於合理懷疑,陪審團就應作出無罪認定;如果找不出合理懷疑,你們必須基於良知,判決被告有罪,你們的決定必須一致。如果你們判被告有罪,本庭將會對他施以嚴厲懲罰,最高的刑罰會是死刑,這是一項沉重的責任。」
◆
這集有另一個法律觀點是我第一次聽,那就是人民參與審判的機制。黃在節目中簡單介紹了兩種機制:一種是「陪審制」,一種是「參審制」。
我在這裡不多加簡介,想進一步了解的人請自己搜尋關鍵字。我想分享的是,原來陪審團制度最早的起源是「同儕審判」。同儕審判簡單來說,就是去詢問與被告背景相似者的意見。這讓我發現法律設計的其中一個面向,從小就聽過「情、理、法」,所以同儕審判就類似「情」的部分?考慮被告者的背景、社經地位、處境,進一步了解被告可能的犯案動機,以期能做到罪責相當的判決?
而日本的「國民裁判員」制度則是類似「陪審制」與「參審制」的混合,由6名裁判員及3名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最後一起投票決定。這個制度聽起來很不錯,好像人民的意見與法官的意見都顧及了,我想當初設計的用意也可能如此。但黃在這裡提了一個需要注意的論點,那就是當一般民眾與法官一起在進意見交換討論時,民眾會不會容易被相對來說有「權威」身分的法官影響?
台灣之後要推的「國民法官制度」,就類似日本的國民裁判員制度。啊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寫可以想的,但我好像寫太多了。有興趣的人請自己聽這集Podcast。
→法影Ep. 1《十二怒漢》,怒什麼?談人民參審與司法決策
起床
我想控制那個狀態。卻又知道,那不是我可以控制得了。我知道自己該拋開那想要「馬上」改變狀態的念頭,那念頭卻像長了根一樣。那念頭瞬間長根,一下子就盤據了我的腦袋。我知道那念頭沒有道理,但它的根已經進去。
我開始敲自己的頭。痛好像可以讓那念頭變小。那念頭的根似乎稍稍縮小了它的範圍。但過沒多久我又被那念頭盤據。我第二次用力的敲頭,這次的力道比上次更大。敲完頭,我感覺被敲擊處的痛,以及心臟的跳動。我感覺著身體的感覺,感覺著身體的感覺,念頭就又變小了。不曉得在什麼樣的狀態下我終於睡著了。我做了個夢,夢裡我在替自己拍照。
醒來後我知道今天開始了,但要怎麼開始。只要還活著,今天就會開始。今天的光比昨天暗些,是陰天。我不想起床,但我知道起床是一瞬間。後來我一瞬間就起床了,就起床了。
我開始敲自己的頭。痛好像可以讓那念頭變小。那念頭的根似乎稍稍縮小了它的範圍。但過沒多久我又被那念頭盤據。我第二次用力的敲頭,這次的力道比上次更大。敲完頭,我感覺被敲擊處的痛,以及心臟的跳動。我感覺著身體的感覺,感覺著身體的感覺,念頭就又變小了。不曉得在什麼樣的狀態下我終於睡著了。我做了個夢,夢裡我在替自己拍照。
醒來後我知道今天開始了,但要怎麼開始。只要還活著,今天就會開始。今天的光比昨天暗些,是陰天。我不想起床,但我知道起床是一瞬間。後來我一瞬間就起床了,就起床了。
2020年6月24日 星期三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這句話好像有一種──「你感覺到的,我也可以感受得到」的意思。但是,感覺到的真的是同一種東西嗎?很有可能不完全相同。那麼,感同身受是什麼?
感同身受是,讓我們「感同身受」的來源可能有所不同,但卻觸發了我們有很類似的感覺。
所以,當有人告訴我他感同身受,我說我可以理解。但我理解的不是那個觸發他感同身受的「東西」,而是我可以理解感同身受的那個「感覺」。
感同身受是,讓我們「感同身受」的來源可能有所不同,但卻觸發了我們有很類似的感覺。
所以,當有人告訴我他感同身受,我說我可以理解。但我理解的不是那個觸發他感同身受的「東西」,而是我可以理解感同身受的那個「感覺」。
2020年6月21日 星期日
這也算是某種鄉野奇談吧
前天PO了鄰居的爸爸走失的消息。在日環蝕的這天,有好消息了!
這也算是某種鄉野奇談吧!在孫爺爺走失的第三天,大家想說把握最後的關鍵時刻,今天凌晨四點約在活動中心集合(大約有三十幾四十人吧!),分組分路線把鹿野永安永康永昌地毯式巡過一遍。因為爺爺有失智的緣故,所以指揮的人請大家──「覺得他不可能走下去的地方也要去走走看」──田裡啊、草叢啊、森林啊、溝圳啦、園子啊,全部都去走走看。有些人巡到中午,有些人巡到晚上,就在希望好像越來越渺茫的時候,社區廣播了──
孫爺爺找到了,就在活動中心旁邊的民宅裡。
原來該民宅主人外出,孫爺爺這幾天就住在人家家裡面,大概是把別人家誤以為是自己家吧!想到孫爺爺就在我們早上集結地方的不遠處,就忍不住想要笑出來,大家走到那好遠好遠的那邊,沒想到要找的人就近在邊邊。
所以,以後如果有失智老人走失,嗯,請從附近的住家先找起喔。
很開心最後是以笑得出來的結果收場。很開心老孫一家人可以放心了。
PS.孫爺爺的氣色看起來很好。
這也算是某種鄉野奇談吧!在孫爺爺走失的第三天,大家想說把握最後的關鍵時刻,今天凌晨四點約在活動中心集合(大約有三十幾四十人吧!),分組分路線把鹿野永安永康永昌地毯式巡過一遍。因為爺爺有失智的緣故,所以指揮的人請大家──「覺得他不可能走下去的地方也要去走走看」──田裡啊、草叢啊、森林啊、溝圳啦、園子啊,全部都去走走看。有些人巡到中午,有些人巡到晚上,就在希望好像越來越渺茫的時候,社區廣播了──
孫爺爺找到了,就在活動中心旁邊的民宅裡。
原來該民宅主人外出,孫爺爺這幾天就住在人家家裡面,大概是把別人家誤以為是自己家吧!想到孫爺爺就在我們早上集結地方的不遠處,就忍不住想要笑出來,大家走到那好遠好遠的那邊,沒想到要找的人就近在邊邊。
所以,以後如果有失智老人走失,嗯,請從附近的住家先找起喔。
很開心最後是以笑得出來的結果收場。很開心老孫一家人可以放心了。
PS.孫爺爺的氣色看起來很好。
如果我當時沒有站在那裡
本來對日環蝕並沒有太大興趣,但就在下午三點多時,朋友剛好有可以看日蝕的遮光眼鏡,我跟她借來看了一眼,當我看到那從下方被吃掉一口的太陽,才覺得實在好好玩。不曉得該怎麼說,雖然這幾天已經在網路上看過照片,但「實際」看到的感覺還是很不一樣。
你不透過某個東西看,它就只是亮閃閃的,就只是個圓。但透過遮光鏡看,它就缺了一口,而且越缺越大口。有一種你發現你「看到的」並不是「真相」的感覺,你得透過其他的方法,你得瞇起眼睛,你才能看見「真相」。
朋友們打算去池上看日蝕,我沒跟去。我想著回家自己也來做一個遮光片,做一個可以看日蝕的玩具。
下午三點半,距離日環蝕還有一段時間。我想到我從前做的底片詩,我把沒有字的部分剪下兩塊,夾進幻燈片夾。我拿到日光下看,喔喔喔,可以耶,可以看到。雖然沒有像朋友的遮光眼鏡那樣清楚,但是可以,有,我看到那個在幻燈片上缺角的太陽,其實更像是弦月。弦月常見,但它是太陽!我們平常不可能看到這樣的太陽對吧?
我很興奮,像是做實驗成功的小孩。這比用現成的遮光眼鏡看到日蝕還要興奮。
接著我實驗其他方法。用黑色壓力克顏料塗在透明片上,再夾進幻燈片夾。這個方法失敗了,因為壓克力顏料塗得不夠平整均勻,光線會散開。還是前一個方法比較好。
後來在四點十三、四分,差不多就是人家說日環蝕正式開始的時候,我用自製的幻燈片看,突然發現烏雲來了。烏雲來了,那太陽不就會被遮住?烏雲遮了一秒兩秒、三秒四秒......天啊,烏雲變淡了,烏雲竟然成了最好的遮光片,這成了史上可以用肉眼直視日蝕的時刻。
烏雲就在日環蝕的時刻來,而且來得剛剛好,位置剛剛好,遮的光也剛剛好。我幾乎看到了整個完整的日環蝕,像個亮閃閃的戒指一樣。當我看見那個亮閃閃的戒指過後沒幾秒,接著,烏雲就整個把它遮住了。
我問老斌,其他地方也會這麼剛好看到這片烏雲成了日環蝕的最佳遮光片嗎?Y說不一定,也是要看方位。
就那幾秒鐘的時間,那片雲來得那樣剛好。這樣的巧合有什麼樣的意義?沒有什麼意義。在我心裡卻有一種非常難以言喻的感覺。一種,我現在在這裡,看到,的感覺。這有什麼了不起嗎?沒看到會怎樣嗎?不會。但我一直在感覺那個感覺。
我現在看著老斌在那個當下拍的照片。照片就是那個當下。但如果我當時沒有站在那裡,就算我現在看著照片,我也不會有我現在心裡的這種感覺。
2020年6月16日 星期二
回到家,打開家門那一刻都像是在開獎。
今天很熱,現在想睡覺,可是又想寫東西,可是又懶。其實晚上已經涼了,可是好想睡覺。但會不會是因為我有時間,才這樣浪費時間?如果是夏夏,她是不是抓到一點點時間,就可以寫?
是不是時間很少的人,越會生出時間?
今天讀完《傍晚五點十五分》。讀的時候一直在想,夏夏用這樣的零碎時間寫出那樣不零碎而有厚度的東西,真是不容易。我應該要再多寫一點,但今天先到這裡了。
◆
每日。
我因為他的遺忘,而徒勞地忙碌。
我們各自演繹著心與亡兩字的不同組合。
當衰「亡」重重壓在「心」口上,大自然所創造的保護機制於是啟動,父親被遺「忘」掌權。此時,再也無法負荷的記憶都遭刪除,生命剩下全然的呼與吸,睡與吃,時間的刻度亦如掌紋般被磨平。
當「心」的一旁總有死「亡」如影般隨伺在側,「忙」亂取代了安寧。時鐘上的每一道刻痕都成了障礙賽需要跨越的關卡,又像是一道道索命符,催促著我的腳步快快快,動作快快快,才能勉強應付父親的需求。
每日。
回到家,打開家門那一刻都像是在開獎。
──夏夏,《傍晚五點十五分》
是不是時間很少的人,越會生出時間?
今天讀完《傍晚五點十五分》。讀的時候一直在想,夏夏用這樣的零碎時間寫出那樣不零碎而有厚度的東西,真是不容易。我應該要再多寫一點,但今天先到這裡了。
◆
每日。
我因為他的遺忘,而徒勞地忙碌。
我們各自演繹著心與亡兩字的不同組合。
當衰「亡」重重壓在「心」口上,大自然所創造的保護機制於是啟動,父親被遺「忘」掌權。此時,再也無法負荷的記憶都遭刪除,生命剩下全然的呼與吸,睡與吃,時間的刻度亦如掌紋般被磨平。
當「心」的一旁總有死「亡」如影般隨伺在側,「忙」亂取代了安寧。時鐘上的每一道刻痕都成了障礙賽需要跨越的關卡,又像是一道道索命符,催促著我的腳步快快快,動作快快快,才能勉強應付父親的需求。
每日。
回到家,打開家門那一刻都像是在開獎。
──夏夏,《傍晚五點十五分》
2020年6月11日 星期四
很久沒去信義誠品
很久沒去信義誠品。去之前先查了地圖,從市政府站到誠品該怎麼走。可走出去後還是忘了轉彎,直直走一直到新光三越。印象中沒那麼遠,本想找人問路,後來想這裡可能有免費的無線網路,就坐下開了筆電,上網搜尋。果然連上了線,果然走過了頭。我往回走,一回頭就看到誠品。
明明就離我很近,我卻看不見它,因為方向錯了。轉個角度就看見了。
走進誠品三樓,格局跟多年前印象中的差不多,但找不到閱讀書房。後來才知道閱讀書房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房間,而是時間快到前才會出現,就像夜市一樣,時間快到才會開始佈設,擺桌椅。
人比預期得多。編輯昀臻開場時請已經看過書的人舉手,有好多隻手,我想大概有超過二分之一。超過二分之一,我想今天應該有機會「對話」。結果今天真的一來一往收到了好多問題,聽到了好多想法,而且那些問題都超會問的。然後非常謝謝那些提問的人,讓我可以喘口氣休息。我發現自己好像無法一口氣說太多話,不曉得是不是不太會控制呼吸,昨天講話的時候有一度覺得氣不夠想咳嗽,還好忍住趕快換氣喝水,不然實在有點擔心突然的咳嗽會嚇到觀眾。
有個朋友在開始前很早就來了,我因此有個說話對象,可以緩解緊張。朋友E問我說,這場除了出版社的人,有其他認識的人來嗎?我回頭看了一下說,好像就只有你,和一個前一場認識的讀者。這時坐在我後面的一個男生拉下口罩,我才發現啊是我們都會跟他換米的朋友,他沒拉下口罩我都沒發現。
最後我還收到一束花。在聽了版社夥伴轉述以及讀了附在花上的小卡,我還是不知道送花的人是誰。收到花時有點驚訝,因為熟識的人應該不會送我花。我看著花,試著想要叫出那些花的名字,但我只說得出兩種。我叫不出那些花的名字。
一下子講太多話後,我就會放得很空。回家途中頭很痛,還好一倒下就睡著了,沒有因為話講太多而無法關機。醒來後替花找了個透明玻璃杯,把包裝拆開,放花進去。
謝謝昨天來的每個人,不論有說到話或沒說到話的。
明明就離我很近,我卻看不見它,因為方向錯了。轉個角度就看見了。
走進誠品三樓,格局跟多年前印象中的差不多,但找不到閱讀書房。後來才知道閱讀書房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房間,而是時間快到前才會出現,就像夜市一樣,時間快到才會開始佈設,擺桌椅。
人比預期得多。編輯昀臻開場時請已經看過書的人舉手,有好多隻手,我想大概有超過二分之一。超過二分之一,我想今天應該有機會「對話」。結果今天真的一來一往收到了好多問題,聽到了好多想法,而且那些問題都超會問的。然後非常謝謝那些提問的人,讓我可以喘口氣休息。我發現自己好像無法一口氣說太多話,不曉得是不是不太會控制呼吸,昨天講話的時候有一度覺得氣不夠想咳嗽,還好忍住趕快換氣喝水,不然實在有點擔心突然的咳嗽會嚇到觀眾。
有個朋友在開始前很早就來了,我因此有個說話對象,可以緩解緊張。朋友E問我說,這場除了出版社的人,有其他認識的人來嗎?我回頭看了一下說,好像就只有你,和一個前一場認識的讀者。這時坐在我後面的一個男生拉下口罩,我才發現啊是我們都會跟他換米的朋友,他沒拉下口罩我都沒發現。
最後我還收到一束花。在聽了版社夥伴轉述以及讀了附在花上的小卡,我還是不知道送花的人是誰。收到花時有點驚訝,因為熟識的人應該不會送我花。我看著花,試著想要叫出那些花的名字,但我只說得出兩種。我叫不出那些花的名字。
一下子講太多話後,我就會放得很空。回家途中頭很痛,還好一倒下就睡著了,沒有因為話講太多而無法關機。醒來後替花找了個透明玻璃杯,把包裝拆開,放花進去。
謝謝昨天來的每個人,不論有說到話或沒說到話的。
無題(麥可.格拉沃格)
他一向不擅長道別
他總認為要走的時候 走就對了
刻意道別鮮少能適切表達情感
不是表現得太若無其事
而傷害到別人
就是自己感情受傷
要是做得太多 感情太投入
語調就會不自然
隨之而來的便是內心的空虛
洶湧的情緒過後 人會倍感寂寞
多數的道別都太誇張了
因為大家遲早還會再見面
如果見不到了
在道別時也不會知道
◆
某條小路上 有棟房子的大門
大到能讓人騎馬穿越
門的上方是二樓的窗戶
每天黃昏都開著
窗前站著一隻大狗
牠強壯的前腳搭在窗台上
視線越過人與車 凝望遠方
帶著一股愉悅的自信
是的 那個人會來
牠的人(his human)
那個信任牠的人
讓牠自由站在窗前觀看
即便牠有那麼一丁點的可能
會墜樓而死
或許這正是構成自由的原因
也是世界愈來愈不自由的原因
自由之所以消逝
是因為人會預見災難發生的風險
並因應這些風險來規劃人生
卻不去考慮 如果拋開這些束縛
也許會發生哪些美好的事
恐懼是個可怕的同伴
這隻狗擁有可能掉出窗外的自由
正因如此
牠才是一隻不會墜樓的驕傲狗兒
就算墜樓了 牠也是快樂的
──〈無題〉,麥可.格拉沃格(Michael Glawogger)
他總認為要走的時候 走就對了
刻意道別鮮少能適切表達情感
不是表現得太若無其事
而傷害到別人
就是自己感情受傷
要是做得太多 感情太投入
語調就會不自然
隨之而來的便是內心的空虛
洶湧的情緒過後 人會倍感寂寞
多數的道別都太誇張了
因為大家遲早還會再見面
如果見不到了
在道別時也不會知道
◆
某條小路上 有棟房子的大門
大到能讓人騎馬穿越
門的上方是二樓的窗戶
每天黃昏都開著
窗前站著一隻大狗
牠強壯的前腳搭在窗台上
視線越過人與車 凝望遠方
帶著一股愉悅的自信
是的 那個人會來
牠的人(his human)
那個信任牠的人
讓牠自由站在窗前觀看
即便牠有那麼一丁點的可能
會墜樓而死
或許這正是構成自由的原因
也是世界愈來愈不自由的原因
自由之所以消逝
是因為人會預見災難發生的風險
並因應這些風險來規劃人生
卻不去考慮 如果拋開這些束縛
也許會發生哪些美好的事
恐懼是個可怕的同伴
這隻狗擁有可能掉出窗外的自由
正因如此
牠才是一隻不會墜樓的驕傲狗兒
就算墜樓了 牠也是快樂的
──〈無題〉,麥可.格拉沃格(Michael Glawogger)
2020年6月5日 星期五
讀夏夏的《傍晚5點15分》,會想到爸爸
昨天收到夏夏的《傍晚5點15分》,今天已經看了快一半。今天中午出鹿野,下午到高雄,明天再回鹿野。出門時想著要不要帶電腦,會用上筆電嗎?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我,想著帶電腦至少還可以上網。很神奇,雖然沒有手機可上網,但我似乎挺依賴網路的。
帶筆電出門,本來想說可以工作,真是想得太美好了。工作需要更靜心。但寫文章有時不用,想寫的時候,就算有聲音也可以寫。像現在,剛放下《傍晚5點15分》,我很想寫,打開電腦就寫。
今天早餐讀的時候,在火車上讀的時候,我的腦袋一直浮現爸爸。因為夏夏一直在寫她的爸爸,我也就想起自己的爸爸。我想起爸爸的時候,覺得很不好意思,我為爸爸做的事,很少很少。
夏夏的爸爸在書裡叫「邦迪亞上校」。邦迪亞上校,其實我從前在夏夏的臉書上,就看過她寫邦迪亞上校,只是我不曉得她為什麼要這樣叫他。今天看了書,我才知道,邦迪亞上校一直在重覆,而夏夏的爸爸也一直在重覆。我讀〈三場葬禮和一場(沒有舉行)的婚禮〉時,讀到夏夏帶爸爸當自己的結婚見證,登記結婚。要簽名時,爸爸問,這是幹嘛?過了一會又問,今天是在幹嘛?
補辦婚禮儀式的那天,「雖然桌上的每道菜都是我和Y親自點的,為要答謝圍坐在餐桌邊的每一位老小,我卻不記得到底吃下什麼,連味道也嚐不進嘴裡。一餐下來,只是忙著替父親夾菜、剪碎菜葉、擦手擦嘴,最後乾脆放任他用手抓著吃,無力再顧及所謂的形象。反正,已經是一家人了,我安慰自己。」
讀到這裡時,我覺得邦迪亞上校好像變成了小孩。我想著自己的爸爸會不會哪一天也變成了小孩。這件事我還在迴避,或者不是迴避,但一直沒有準備。可是父母有一天一定會老。其實他們現在就已經老了,只是還算健康,可這個健康也止於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其實耳朵早就不好了,眼睛不行了,牙齒也只能吃軟爛的食物。
讀傍晚時我一直想到爸爸。也會想到媽媽,但爸爸多一些。我想著我與爸爸的距離,一直不像我與媽媽的距離。
上個月要從老家回鹿野時,因為沒抓好上火車的時間,我收拾完行李就來不及洗自己在家裡睡覺的衣服了。我來不及了,我收起外衣褲還有毛巾,想請媽媽有空時幫我洗。媽媽剛好不在家,我跟爸爸說,「爸,你可以幫我跟媽說,請她幫我洗一下嗎?」結果爸爸說,「我來洗就好啦,我幫你洗。」
我看著爸爸,爸爸用像小孩子的眼睛看著我,「我來洗就好啦。我都會洗自己的衣服喔。」
說完後爸爸幫我提行李到門邊,對我說一路順風。我低著頭沒看爸爸,怕爸爸看到我的眼睛。
帶筆電出門,本來想說可以工作,真是想得太美好了。工作需要更靜心。但寫文章有時不用,想寫的時候,就算有聲音也可以寫。像現在,剛放下《傍晚5點15分》,我很想寫,打開電腦就寫。
今天早餐讀的時候,在火車上讀的時候,我的腦袋一直浮現爸爸。因為夏夏一直在寫她的爸爸,我也就想起自己的爸爸。我想起爸爸的時候,覺得很不好意思,我為爸爸做的事,很少很少。
夏夏的爸爸在書裡叫「邦迪亞上校」。邦迪亞上校,其實我從前在夏夏的臉書上,就看過她寫邦迪亞上校,只是我不曉得她為什麼要這樣叫他。今天看了書,我才知道,邦迪亞上校一直在重覆,而夏夏的爸爸也一直在重覆。我讀〈三場葬禮和一場(沒有舉行)的婚禮〉時,讀到夏夏帶爸爸當自己的結婚見證,登記結婚。要簽名時,爸爸問,這是幹嘛?過了一會又問,今天是在幹嘛?
補辦婚禮儀式的那天,「雖然桌上的每道菜都是我和Y親自點的,為要答謝圍坐在餐桌邊的每一位老小,我卻不記得到底吃下什麼,連味道也嚐不進嘴裡。一餐下來,只是忙著替父親夾菜、剪碎菜葉、擦手擦嘴,最後乾脆放任他用手抓著吃,無力再顧及所謂的形象。反正,已經是一家人了,我安慰自己。」
讀到這裡時,我覺得邦迪亞上校好像變成了小孩。我想著自己的爸爸會不會哪一天也變成了小孩。這件事我還在迴避,或者不是迴避,但一直沒有準備。可是父母有一天一定會老。其實他們現在就已經老了,只是還算健康,可這個健康也止於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其實耳朵早就不好了,眼睛不行了,牙齒也只能吃軟爛的食物。
讀傍晚時我一直想到爸爸。也會想到媽媽,但爸爸多一些。我想著我與爸爸的距離,一直不像我與媽媽的距離。
上個月要從老家回鹿野時,因為沒抓好上火車的時間,我收拾完行李就來不及洗自己在家裡睡覺的衣服了。我來不及了,我收起外衣褲還有毛巾,想請媽媽有空時幫我洗。媽媽剛好不在家,我跟爸爸說,「爸,你可以幫我跟媽說,請她幫我洗一下嗎?」結果爸爸說,「我來洗就好啦,我幫你洗。」
我看著爸爸,爸爸用像小孩子的眼睛看著我,「我來洗就好啦。我都會洗自己的衣服喔。」
說完後爸爸幫我提行李到門邊,對我說一路順風。我低著頭沒看爸爸,怕爸爸看到我的眼睛。
2020年6月3日 星期三
寫的過程發現什麼,那才是寫的意義。
「寫的過程發現什麼,那才是寫的意義。」
我在幼獅評《滌》的書評中,讀到了我自己在書中寫的這句話。讀的當下我想起了什麼。我想起紀州庵那場分享會後,主持人提了一個問題──「你現在應該收到了許多回饋,你有沒有什麼想跟讀者說的?」這個問題在我腦袋裡繞了幾圈,我說,有很多讀者來跟我說謝謝,我也想跟他們說謝謝;但除了謝謝之外,那時還有一個很神奇的感覺我說不清楚,我試著說,但說得很亂。
郁佳問:「你是沒有預設到讀者會有這樣的反應嗎?」我當下沒有回答,我還在想。現在,當我讀到「寫的過程發現什麼,那才是寫的意義」這句我自己寫的話之後,我才知道該怎麼說──
與有無預設無關,而是我自己好像也可以感覺得到,因為我自己在讀的時候,也有他們說的那些感覺。這聽起來很奇怪,作者明明是我,怎麼說得好像是自己在讀別人寫的東西。我想那是因為,我寫的時候一直在想,一直在發現,而那個是屬於「正在寫的那個我的東西」。所以當我寫完了,我回去讀,讀的時候我彷彿看見那個正在寫的自己腦袋裡的東西,像是看到另一個人的思考,雖然那明明是我自己的思考;但我自己的思考,又再次了提醒了我自己,或是,又讓我自己重新想了一遍。
對我來說,寫與思考是同一件事。並不是思考完,問題就解決了,或是寫完從此就變成另一個人了。但寫確實影響了當下那個正在寫的我,或者也可以這麼說──正在寫的我,在那個時候正經歷著某些變化,而我將那些變化留了下來,又影響了之後閱讀的我。
我在幼獅評《滌》的書評中,讀到了我自己在書中寫的這句話。讀的當下我想起了什麼。我想起紀州庵那場分享會後,主持人提了一個問題──「你現在應該收到了許多回饋,你有沒有什麼想跟讀者說的?」這個問題在我腦袋裡繞了幾圈,我說,有很多讀者來跟我說謝謝,我也想跟他們說謝謝;但除了謝謝之外,那時還有一個很神奇的感覺我說不清楚,我試著說,但說得很亂。
郁佳問:「你是沒有預設到讀者會有這樣的反應嗎?」我當下沒有回答,我還在想。現在,當我讀到「寫的過程發現什麼,那才是寫的意義」這句我自己寫的話之後,我才知道該怎麼說──
與有無預設無關,而是我自己好像也可以感覺得到,因為我自己在讀的時候,也有他們說的那些感覺。這聽起來很奇怪,作者明明是我,怎麼說得好像是自己在讀別人寫的東西。我想那是因為,我寫的時候一直在想,一直在發現,而那個是屬於「正在寫的那個我的東西」。所以當我寫完了,我回去讀,讀的時候我彷彿看見那個正在寫的自己腦袋裡的東西,像是看到另一個人的思考,雖然那明明是我自己的思考;但我自己的思考,又再次了提醒了我自己,或是,又讓我自己重新想了一遍。
對我來說,寫與思考是同一件事。並不是思考完,問題就解決了,或是寫完從此就變成另一個人了。但寫確實影響了當下那個正在寫的我,或者也可以這麼說──正在寫的我,在那個時候正經歷著某些變化,而我將那些變化留了下來,又影響了之後閱讀的我。
2020年6月2日 星期二
自動洗衣真偉大
應該要先寫方格子,但我剛剛看到洗衣機順利運轉,忍不住覺得洗衣機真偉大。「現在它可以自動注水、自動洗清、自動脫水喔!」老斌說。我說真的假的,從朋友那邊接收的洗衣機不是也有部分障礙嗎?老斌說那台洗衣機型號跟我們舊的剛好一樣,都是愛妻號。「我們把零件換一換,現在它又是全自動了!」
這根本是洗衣機界的器官捐贈,這個愛妻把自己的器官給另一個愛妻,將大愛遺留人間。
我本來想要把這個感人的器官捐贈故事,還有我們家第一台愛妻號是怎麼來的故事寫一寫,可是嗚嗚嗚我今天好像不夠有時間把它寫完,所以剩下的就交給老斌寫了。
但最後我還想說一件事──當你的洗衣機從「全自動」變成「半自動」再變成「全手動」,最後幾乎只剩脫水功能後(脫水功能還不一定每次都能順利運作,你得精準掌握衣服重量與分布位置來控制平衡)。這樣過了大概一年,然後有一天,當你再度體驗到「全自動」洗衣機的神奇──當你把衣服丟進去把洗衣粉倒進去然後按幾個鈕,你就可以安心的坐到電腦前面劈哩啪啦(或隨便你要幹什麼其他的事),你會覺得洗衣機真是太偉大的發明了!有沒有人想要體驗這種偉大的發明呢?請在洗衣機故障後繼續留用一年(我們好像留了不只一年好像花了更久的時間陪它衰老),你就會再次感受全自動洗衣機的偉大!
◆
老斌寫的:〈這是一段感人的機器器官捐贈的故事〉
這根本是洗衣機界的器官捐贈,這個愛妻把自己的器官給另一個愛妻,將大愛遺留人間。
我本來想要把這個感人的器官捐贈故事,還有我們家第一台愛妻號是怎麼來的故事寫一寫,可是嗚嗚嗚我今天好像不夠有時間把它寫完,所以剩下的就交給老斌寫了。
但最後我還想說一件事──當你的洗衣機從「全自動」變成「半自動」再變成「全手動」,最後幾乎只剩脫水功能後(脫水功能還不一定每次都能順利運作,你得精準掌握衣服重量與分布位置來控制平衡)。這樣過了大概一年,然後有一天,當你再度體驗到「全自動」洗衣機的神奇──當你把衣服丟進去把洗衣粉倒進去然後按幾個鈕,你就可以安心的坐到電腦前面劈哩啪啦(或隨便你要幹什麼其他的事),你會覺得洗衣機真是太偉大的發明了!有沒有人想要體驗這種偉大的發明呢?請在洗衣機故障後繼續留用一年(我們好像留了不只一年好像花了更久的時間陪它衰老),你就會再次感受全自動洗衣機的偉大!
◆
老斌寫的:〈這是一段感人的機器器官捐贈的故事〉
2020年6月1日 星期一
對話
結束了在紀州庵的第一場分享會。要謝謝的人當然很多,但要特別謝謝盧郁佳。盧郁佳真是個咖,跟她對談的時候真的是在「對談」,而不是因為這是一場對談所以我們要對談。在開始前我不知道究竟會怎麼開始,雖然我們已經通過好幾次信,雖然文訊的丹尼幫我們準備了流程表,但在開始的時候不是照著那些走,而是在我講到一個段落時,我轉頭看了盧郁佳一眼,我發現她很認真聽的表情,然後她說了一句話,問了我一個問題,然後我們就開始了。開始了「對談」,開始了「對話」。
然後我也很謝謝當天來的,那些我不認識的陌生讀者。謝謝你們願意跟我說你的想法與感覺。大熱天的,下午又可能下雨,願意特別來聽人講話兩個小時,而且還願意說自己的想法與感覺。其中有個讀者問我,是不是不喜歡簽書?她說好像有在臉書上看我這麼提過,她說,「如果你不喜歡請不要勉強,我只是想透過這個機會能說上話。」我說我不是不喜歡與不願意,而是,如果是儀式性的簽書,其實我都要想很久,我會花很多時間去想這個儀式的意義,但又不好意思拒絕,然後一邊簽名一邊思考這個行為的意義,老實說心裡實在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如果像是這種交流互動,在這種情況下在書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很願意。」我沒說的是甚至感到榮幸。我不曉得這樣是否有說清楚,我對簽書這件事的想法。
對話開始於什麼?開始於一個人認真說,一個人認真聽,然後一來一往,一來一往。真實的對話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人之間,有可能是剛認識才半小時的人,有可能是只會見一次面的短暫相遇。真實的對話無關你們兩者現有的「關係」,而是有機會對話的那個「當下」,說的人與聽的人的交會。
然後我也很謝謝當天來的,那些我不認識的陌生讀者。謝謝你們願意跟我說你的想法與感覺。大熱天的,下午又可能下雨,願意特別來聽人講話兩個小時,而且還願意說自己的想法與感覺。其中有個讀者問我,是不是不喜歡簽書?她說好像有在臉書上看我這麼提過,她說,「如果你不喜歡請不要勉強,我只是想透過這個機會能說上話。」我說我不是不喜歡與不願意,而是,如果是儀式性的簽書,其實我都要想很久,我會花很多時間去想這個儀式的意義,但又不好意思拒絕,然後一邊簽名一邊思考這個行為的意義,老實說心裡實在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如果像是這種交流互動,在這種情況下在書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很願意。」我沒說的是甚至感到榮幸。我不曉得這樣是否有說清楚,我對簽書這件事的想法。
對話開始於什麼?開始於一個人認真說,一個人認真聽,然後一來一往,一來一往。真實的對話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人之間,有可能是剛認識才半小時的人,有可能是只會見一次面的短暫相遇。真實的對話無關你們兩者現有的「關係」,而是有機會對話的那個「當下」,說的人與聽的人的交會。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