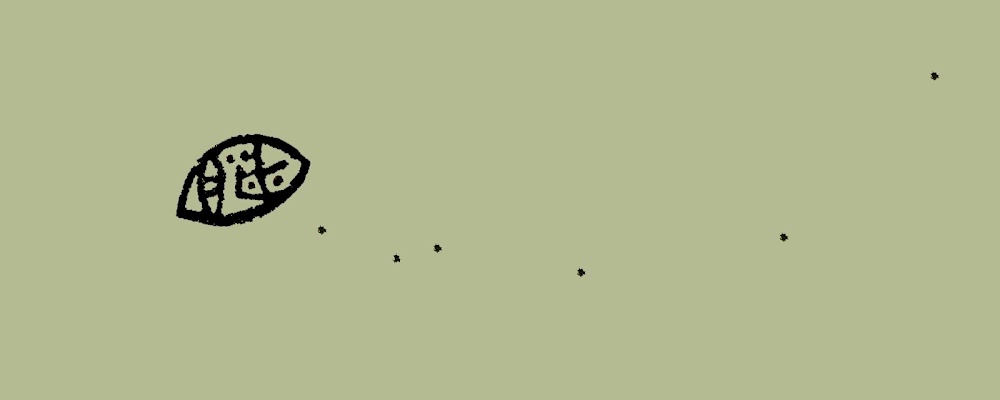一個四方的空間裡
四方的桌椅
我們面對面坐著
熱切地說話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如果一分鐘可以說三百個字
那麼一小時就是一萬八千個字
一萬八千個字
差不多是一篇短篇小說的長度
而更多的時候說的比這個更多
怎麼有那麼多話要說
兩個女人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兩個大學生
一個穿粉紅色上衣的男孩和一個綁馬尾的女孩
四個同性向的男孩
兩個OL
在白噪音的四方空間裡
我們的聲音變成一種聲音
想說話的聲音
2014年10月30日 星期四
2014年10月28日 星期二
【臺北詩歌節-兔子洞裡的宇宙:童詩閱讀講稿】──我沒有想過我會來講童詩
10月23日的童詩講座,與兩位與談者幸佳慧和林世仁談得很愉快,大概是因為彼此對詩的看法都蠻接近的。雖然我們三位對「童詩」的定義不太相同,但這樣才有意思,要是三個人講的東西都大同小異,那豈不是很無聊?
主持人楊佳嫻很會帶。她建議我們三人穿插著講,這樣的方式果然是好的,確實是對談,而不是各說各話。因為這樣,我講了一些原本沒在講稿中東西;但也因為這樣,原本準備的講稿並沒有全部講完。
對講稿有興趣的朋友,以下有約四千多字的東西,不嫌長的話可以讀讀看。
【我沒有想過我會來講童詩】
我小時候對「童詩」沒什麼好感,為什麼會那樣覺得,我也記不太清楚了,大概是因為我對讀到的「童詩」都沒什麼感覺吧。比起童詩,小時候的我更喜歡讀小說,我覺得小說有更多想像的天地。
現在竟然要來講童詩,真是誠惶誠恐。
老實說,按我自己來定義的話,並沒有「童詩」這一項分類。我這樣講,大概會被童詩專業人士說你真是外行,嗯,沒錯,我確實是外行。所以今天來,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外行人對「童詩」的想法。
◆
〈好遠好遠的雨只剩下樣子。太陽是蛋黃的樣子。海是線的樣子〉/ 瞇
我看過
可是我記不住
每一場在我眼前的景象
我看著海上的雲
想把她們的形狀顏色看來鬆軟的樣子
像照片一樣留在腦子裡
但是沒有辦法,連一秒都無法
只剩下感覺
所謂的感覺
有時會忘了一些事
比如,那蛋黃一樣的太陽
在我眼前掉進那條線的下面(後面或裡面)
我會以為
她正在緩慢地降落
以為
海是一條線
山是一條線
五分鐘
可能更長或更短
很奇怪
世界好像只剩下那顆蛋黃
但平常時候她其實也都在
海上的雨
遠遠的海上的雨
原來雨有那種樣子
一團會走路的灰色
我好像可以想像在那團灰色裡面
雨會怎樣地打在我的身上
可是好遠好遠的雨只剩下樣子了
就像好遠好遠的雲只剩下雲的樣子
而星星永遠只有星星的樣子
今年八月,我寫了上面那首詩貼在fb上。阿米在fb上留言說:「這首很童詩」。嗯,我的詩好像還沒被別人講過「很童詩」呢。我很好奇為什麼阿米會覺得那首詩很童詩。
「很像小朋友畫的圖,很像小朋友的腦袋。」阿米說。
聽阿米這樣說,我好像突然明白她所說的童詩是什麼。她所說的童詩,是寫詩的手像小孩的手,看世界的眼睛像小孩的眼睛,想事情的腦袋像小孩的腦袋。
雖然我早就不是小孩了,但我寫出來的那首詩給阿米童詩的感覺。阿米對童詩的想法,恰好與我對童詩的想法非常接近。
很多人會問:「童詩指的是小孩寫的詩?還是寫給小孩讀的詩呢?」
對我來說,童詩不一定是小孩寫的,也不一定特別寫給小孩讀的,只是寫出那首詩的那個人心裡有個小孩。這個寫詩的人可能是大人,也可能是個小孩,但不管是大還是小,他們的心裡都有個小孩。
重點不在於寫的人是誰,以及到底形式和內容該長什麼樣子。重點是那被寫出來的文字,或說出來的話,裡面有小孩。
但是,什麼叫做文字裡面有小孩呢?
我在編輯毛毛蟲《兒童哲學》 月刊時,會收到一些家長來信,他們記錄了自己還不會寫字的小孩所講的話。從這些小孩所講的話,或許我們可以稍稍碰觸到什麼是「小孩」。
小兒子兩歲五個月時,有一天我在洗澡,他來開門。我問:你要做什麼?他回答: 「我要看。」 他看到我的陰毛,問我:「那是什麼?」我說那是毛。後來我開始穿衣服,穿上衣的時候,他說:「ㄋㄟ ㄋㄟ不見了。」穿內褲時,他說:「毛,毛不見了。」穿外褲時,他說:「腿不見了。」
小兒子在地板上撿到剪下來的彎彎的指甲,問:「這是什麼啊?」 我說是指甲。 小兒子說:「好像月亮哦!爸爸我要月亮。」
有時候小兒子會說:
「不要倒好多滿。」
「我要畫爸爸的名字。」
──林桂如,〈不要倒好多滿〉,《兒童哲學03》
所以,什麼是小孩呢?對我來說,那代表觀察與思考不受既定印象侷限,表達不受語言文字該如何使用限制。
所以,如果那個小孩會寫字,他把說的話寫下來,就變成了一首詩──
〈穿衣的魔術〉
ㄋㄟ ㄋㄟ 不見了
毛不見了
屁股不見了
腿不見了
我想這大概是大人寫不出來的詩。不過也很難說。
◆
〈可不可以說〉/西西
可不可以說
一枚白菜
一塊雞蛋
一隻蔥
一個胡椒粉?
可不可以說
一架飛鳥
一管椰子樹
一頂太陽
一巴鬥驟雨?
可不可以說
一株檸檬茶
一雙大力水手
一頓雪糕梳打
一畝阿華田?
可不可以說
一朵雨傘
一束雪花
一瓶銀河
一葫蘆宇宙?
可不可以說
一位螞蟻
一名曱甴
一家豬玀
一窩英雄?
可不可以說
一頭訓導主任
一隻七省巡按
一匹將軍
一尾皇帝?
可不可以說
龍眼吉祥
龍鬚糖萬歲萬歲萬萬歲
從小孩的不侷限,可以看出大人的侷限。大人的侷限,讓香港作家西西寫出了〈可不可以說〉。可不可以說,一頭訓導主任?當然不行,冠詞用錯了,而且不敬,老師會這麼說。
還好並不是所有的老師都說不能這麼說。在小學任教的小石子,就曾帶他的學生們進行仿作,小孩們玩得非常開心(我想這應該是他們非常會玩的遊戲)。
〈可不可以說〉仿作/丁緒慈、顏昱庭、梁芷瑜、廖千慧
可不可以說
一隻毛皮大衣
兩位字典
三張樹
四架鳥
可不可以說
五株仙草
六個雀巢
七束豆花
八匹沙其瑪
可不可以說
一滴感動
一絲開心
一頓生氣
一盆難過
我覺得「八匹沙其瑪」真是經典。
◆
我覺得對小孩來說,應該沒有詩該寫成什麼樣子,就像沒有畫應該畫成什麼樣子。詩該寫成什麼樣子?畫應該畫成什麼樣子?這些都是大人教給小孩的。一旦學會了「怎麼寫詩」、「怎麼畫畫」,說不定就沒有童詩童畫這種東西了。
所以我不會教小孩什麼是詩,或怎麼寫詩。因為老實說,到底詩是什麼我也沒有辦法好好地說清楚。所以我不會跟小孩說「我來教你們什麼是詩」或「我來教你們寫詩」,我不會給小孩這些定義上的東西。不過,我會給小孩讀一些我覺得不錯的文字,或是我剛好想透過那些文字跟他們討論些什麼,而只是剛好,那些文字被叫做詩。
我在台東的瑞源國小帶小孩上自然生態寫作課。在小學上課我遇到一個難題。小孩太習慣被管,而一旦大人不管,小孩就會鬆掉;小孩整個鬆掉,課程就無法進行,也沒辦法好好地跟他們講話;但是,我不想用「管教」和「處罰」的方式來上課。我把我的困難告訴小孩,跟他們說:「我不想管你們,就像我不會去管大人一樣。但是你們一沒人管,就跑來跑去、衝來衝去、大聲尖叫,這樣我們就沒辦法好好上課。你們覺得我可以怎麼辦呢?」
小孩睜著眼睛看我,說:「老師,你可以處罰我們啊!」
「處罰,你們想要被處罰嗎?」我驚訝地問。
「不想啊,可是你不處罰我們,我們就會吵。」小孩說。
今年台北詩歌節跟我問簡介時,我在最後一句寫了「覺得帶小孩上寫作課是目前生活中最花力氣的事」。不是寫作這件事情難,而是在寫作之前的所有東西難。在寫作之前有什麼呢?有生活、有人與人的關係、有思考與感受,這些都是相較於寫作更重要的東西,沒有這些,寫作什麼也不是。
十月初上課時,我帶小孩玩了一個遊戲。我準備了十三首短詩(你也可以把它想成短短的句子就好),分別寫在十三張紙條上,然後折成小方塊。「我們來抽籤,抽到籤的人把裡面的字唸出來,然後說說看自己想到什麼。」我說。
很神奇,第一個小孩抽到的是〈修剪〉。
〈修剪〉/ 瞇
用長剪將樹木修剪成人們想要的樣子
用規範將小孩修剪成大人希望的樣子
用法律將人民修剪成政府喜歡的樣子
抽到修剪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想跟他們討論關於規範和處罰的事,沒想到一開始就被抽到了。抽到籤的小孩讀一遍,另一個小孩說想讀,又讀了一遍。讀完之後我問:「你們想到什麼?」
小孩A說:「要把我們剪成你們想要的樣子喔!」
小孩B抱著自己的頭說:「不要,不要剪我的頭髮!」
我聽了覺得好好笑。我說不是要剪你的頭髮啦,不過規範和處罰就跟剪頭髮這種東西很像喔,就是把對方剪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可是你們有你們的想法,不會想要被剪對不對,要是被剪成自己不想要的樣子怎麼辦?不想被剪,就要有自己的想法;沒有自己的想法,就會被剪。自己對自己要有想法,不管是自己的頭髮,還是自己的行為。所以我不是一直說我不想要處罰你們嗎?就是這樣的道理,我不希望你們變成沒有想法的人。
我一口氣說了好多,小孩到底有沒有聽懂,我也不曉得。有些小孩點頭,有些小孩看著我。
「不要剪我!」小孩B又說了一次。
那次上課我給小孩讀我寫的短詩,其中有幾首剛好都提到了規範與法律的荒謬。我並不是故意選這些給小孩讀,而是沒辦法這幾年台灣社會這麼亂,關於某些體制的荒謬我無法不寫。有個小孩抽到了〈紅綠燈〉:
〈紅綠燈〉/ 瞇
他想走的時候就按綠燈
叫別人停的時候就按紅燈
他說
紅燈停
綠燈走
這是交通安全
他是依法行政
抽到的小孩說她覺得這首詩很搞笑。我問哪裡搞笑(我心裡想著我可不是為了搞笑寫的)。小孩說:「因為紅綠燈不是我們用的。」
這下我不懂了:「『紅綠燈不是我們用的』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紅綠燈不是我們用的啊!」小孩又說一遍。
我想了一下,突然腦袋開竅:「你的意思是,紅綠燈不是我們想要它紅燈就自己給它按紅燈,想要它綠燈就按綠燈的意思嗎?」
「對啦。」小孩說。
你看,這種道理小孩都懂,但那些搞政治的大人們都不懂。
有個小孩抽到〈不能說不〉。
〈不能說不〉/ 瞇
被關在籠子裡在美術館展覽的八哥不能說不
動物園裡的熊貓不能說不
馬戲團裡的猴子不能說不
海洋世界的海豚不能說不
水族箱裡的孔雀魚不能說不
田裡的水牛不能說不
受安樂死的貓狗不能說不
餐桌上的豬肉不能說不
遭廢水汙染的河川不能說不
被砍掉做成紙張的樹不能說不
(可以一直寫下去)
抽到的小孩問「可以一直寫下去」的意思是可以繼續寫嗎?我說對呀,你想寫嗎?小孩想了想,寫了兩句:
被關在家裡的小孩不能說不
圖書室的書不能說不
真是厲害。第一句應該不用我解釋了。第二句我想是因為寫作課是在圖書室上課,他有感而發吧。
我沒有跟小孩說什麼是詩,也沒有跟小孩說為什麼要這樣寫(他們也不曉得那是我寫的)。對他們來說那就是一個一個句子。我發現他們還蠻喜歡讀的,不曉得為什麼竟然還搶著讀,沒讀到的還會不高興。有些讀完之後會一直笑,有些小孩讀完之後會想要學著寫。我發現小孩C很會觀察,因為我完全沒有跟他說為什麼那首詩那樣寫,但我從他學著寫出來的東西,就發現他在進行分析了。
〈做什麼〉/ 瞇
你們住在鄉下
都在做什麼
那隻兔子一直趴著
在做什麼
星星在那邊亮著
做什麼
雲從這裡飄到那裡
做什麼
◆
〈做什麼〉 / 小孩C
他們在飛機上
都在做什麼
那隻大象一直喝水
在做什麼
太陽在那邊亮著
做什麼
海從這裡流到那裡
做什麼
仔細對照小孩C和我寫的,會發現小孩C會先觀察我怎麼寫,然後再開始寫。所以他把「你們」換成「他們」,把「鄉下」換成「飛機上」,把「兔子」換成「大象」,把「星星」換成「太陽」,把「雲」換成「海」。
雖然小孩C不一定明白這首〈做什麼〉想要說的東西,但這樣的觀察與仿作對他來說或許是有趣的。但我想他極有可能明白我在說什麼,因為當他讀完我寫的〈做什麼〉,第一句說出的話是「好無聊」。
◆
我一直說無法定義詩,但這樣的說法好像有點不負責任。就算我說不出詩是什麼,但一定有「我覺得什麼是詩」的一種想法吧!
我覺得有些詩像任意門,比如蔡仁偉的詩。他的〈食物鏈〉非常經典:
〈食物鏈〉/ 蔡仁偉
剪刀
石頭
布
這首詩根本就是從這裡到那裡最短距離的代表。不過,有些詩像任意門,不代表所有的詩都是任意門。
有些詩像遊戲,許赫的〈牧羊人的晚點名〉根本就是遊戲。不過這首晚點名點太久了,我就不在這裡點名了,請原諒。想要跟著牧羊人一起點名的人,可以去找《診所早晨的晴日寫生》這本詩集,找到〈牧羊人的晚點名〉這首詩,看你是要扮演點名的牧羊人還是被點名的羊都行。
而有些詩是生命,真正影響著我的詩是生命。這種詩沒有一定的樣子,不一定是誰寫的,但你讀見它你就知道你碰觸到了生命。而有些生命是詩。
這是我最想讓人觸碰到的東西,不管是寫的人還是讀的人,不管是小孩還是大人,還是我自己。而生命是一輩子的,生命卻也是片片段段的;詩也是這樣的東西。
不曉得為什麼寫到最後有點嚴肅,那來讀一首可能會笑出來的詩好了。很多人讀到〈有用〉這首詩都會笑,那來讀讀看會不會笑好了。不過,當初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下寫出〈有用〉的呢?實在是想不起來。看來,寫出〈有用〉的腦袋,有點不太有用呀。
〈有用〉/瞇
你太有用了
你太好用了
你太容易用了
沒有人比你更好用了
你生出來就是要被用的
孩子,你要做個有用的人
主持人楊佳嫻很會帶。她建議我們三人穿插著講,這樣的方式果然是好的,確實是對談,而不是各說各話。因為這樣,我講了一些原本沒在講稿中東西;但也因為這樣,原本準備的講稿並沒有全部講完。
對講稿有興趣的朋友,以下有約四千多字的東西,不嫌長的話可以讀讀看。
◆
【我沒有想過我會來講童詩】
我小時候對「童詩」沒什麼好感,為什麼會那樣覺得,我也記不太清楚了,大概是因為我對讀到的「童詩」都沒什麼感覺吧。比起童詩,小時候的我更喜歡讀小說,我覺得小說有更多想像的天地。
現在竟然要來講童詩,真是誠惶誠恐。
老實說,按我自己來定義的話,並沒有「童詩」這一項分類。我這樣講,大概會被童詩專業人士說你真是外行,嗯,沒錯,我確實是外行。所以今天來,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外行人對「童詩」的想法。
◆
〈好遠好遠的雨只剩下樣子。太陽是蛋黃的樣子。海是線的樣子〉/ 瞇
我看過
可是我記不住
每一場在我眼前的景象
我看著海上的雲
想把她們的形狀顏色看來鬆軟的樣子
像照片一樣留在腦子裡
但是沒有辦法,連一秒都無法
只剩下感覺
所謂的感覺
有時會忘了一些事
比如,那蛋黃一樣的太陽
在我眼前掉進那條線的下面(後面或裡面)
我會以為
她正在緩慢地降落
以為
海是一條線
山是一條線
五分鐘
可能更長或更短
很奇怪
世界好像只剩下那顆蛋黃
但平常時候她其實也都在
海上的雨
遠遠的海上的雨
原來雨有那種樣子
一團會走路的灰色
我好像可以想像在那團灰色裡面
雨會怎樣地打在我的身上
可是好遠好遠的雨只剩下樣子了
就像好遠好遠的雲只剩下雲的樣子
而星星永遠只有星星的樣子
今年八月,我寫了上面那首詩貼在fb上。阿米在fb上留言說:「這首很童詩」。嗯,我的詩好像還沒被別人講過「很童詩」呢。我很好奇為什麼阿米會覺得那首詩很童詩。
「很像小朋友畫的圖,很像小朋友的腦袋。」阿米說。
聽阿米這樣說,我好像突然明白她所說的童詩是什麼。她所說的童詩,是寫詩的手像小孩的手,看世界的眼睛像小孩的眼睛,想事情的腦袋像小孩的腦袋。
雖然我早就不是小孩了,但我寫出來的那首詩給阿米童詩的感覺。阿米對童詩的想法,恰好與我對童詩的想法非常接近。
很多人會問:「童詩指的是小孩寫的詩?還是寫給小孩讀的詩呢?」
對我來說,童詩不一定是小孩寫的,也不一定特別寫給小孩讀的,只是寫出那首詩的那個人心裡有個小孩。這個寫詩的人可能是大人,也可能是個小孩,但不管是大還是小,他們的心裡都有個小孩。
重點不在於寫的人是誰,以及到底形式和內容該長什麼樣子。重點是那被寫出來的文字,或說出來的話,裡面有小孩。
但是,什麼叫做文字裡面有小孩呢?
我在編輯毛毛蟲《兒童哲學》 月刊時,會收到一些家長來信,他們記錄了自己還不會寫字的小孩所講的話。從這些小孩所講的話,或許我們可以稍稍碰觸到什麼是「小孩」。
小兒子兩歲五個月時,有一天我在洗澡,他來開門。我問:你要做什麼?他回答: 「我要看。」 他看到我的陰毛,問我:「那是什麼?」我說那是毛。後來我開始穿衣服,穿上衣的時候,他說:「ㄋㄟ ㄋㄟ不見了。」穿內褲時,他說:「毛,毛不見了。」穿外褲時,他說:「腿不見了。」
小兒子在地板上撿到剪下來的彎彎的指甲,問:「這是什麼啊?」 我說是指甲。 小兒子說:「好像月亮哦!爸爸我要月亮。」
有時候小兒子會說:
「不要倒好多滿。」
「我要畫爸爸的名字。」
──林桂如,〈不要倒好多滿〉,《兒童哲學03》
所以,什麼是小孩呢?對我來說,那代表觀察與思考不受既定印象侷限,表達不受語言文字該如何使用限制。
所以,如果那個小孩會寫字,他把說的話寫下來,就變成了一首詩──
〈穿衣的魔術〉
ㄋㄟ ㄋㄟ 不見了
毛不見了
屁股不見了
腿不見了
我想這大概是大人寫不出來的詩。不過也很難說。
◆
〈可不可以說〉/西西
可不可以說
一枚白菜
一塊雞蛋
一隻蔥
一個胡椒粉?
可不可以說
一架飛鳥
一管椰子樹
一頂太陽
一巴鬥驟雨?
可不可以說
一株檸檬茶
一雙大力水手
一頓雪糕梳打
一畝阿華田?
可不可以說
一朵雨傘
一束雪花
一瓶銀河
一葫蘆宇宙?
可不可以說
一位螞蟻
一名曱甴
一家豬玀
一窩英雄?
可不可以說
一頭訓導主任
一隻七省巡按
一匹將軍
一尾皇帝?
可不可以說
龍眼吉祥
龍鬚糖萬歲萬歲萬萬歲
從小孩的不侷限,可以看出大人的侷限。大人的侷限,讓香港作家西西寫出了〈可不可以說〉。可不可以說,一頭訓導主任?當然不行,冠詞用錯了,而且不敬,老師會這麼說。
還好並不是所有的老師都說不能這麼說。在小學任教的小石子,就曾帶他的學生們進行仿作,小孩們玩得非常開心(我想這應該是他們非常會玩的遊戲)。
〈可不可以說〉仿作/丁緒慈、顏昱庭、梁芷瑜、廖千慧
可不可以說
一隻毛皮大衣
兩位字典
三張樹
四架鳥
可不可以說
五株仙草
六個雀巢
七束豆花
八匹沙其瑪
可不可以說
一滴感動
一絲開心
一頓生氣
一盆難過
我覺得「八匹沙其瑪」真是經典。
◆
我覺得對小孩來說,應該沒有詩該寫成什麼樣子,就像沒有畫應該畫成什麼樣子。詩該寫成什麼樣子?畫應該畫成什麼樣子?這些都是大人教給小孩的。一旦學會了「怎麼寫詩」、「怎麼畫畫」,說不定就沒有童詩童畫這種東西了。
所以我不會教小孩什麼是詩,或怎麼寫詩。因為老實說,到底詩是什麼我也沒有辦法好好地說清楚。所以我不會跟小孩說「我來教你們什麼是詩」或「我來教你們寫詩」,我不會給小孩這些定義上的東西。不過,我會給小孩讀一些我覺得不錯的文字,或是我剛好想透過那些文字跟他們討論些什麼,而只是剛好,那些文字被叫做詩。
我在台東的瑞源國小帶小孩上自然生態寫作課。在小學上課我遇到一個難題。小孩太習慣被管,而一旦大人不管,小孩就會鬆掉;小孩整個鬆掉,課程就無法進行,也沒辦法好好地跟他們講話;但是,我不想用「管教」和「處罰」的方式來上課。我把我的困難告訴小孩,跟他們說:「我不想管你們,就像我不會去管大人一樣。但是你們一沒人管,就跑來跑去、衝來衝去、大聲尖叫,這樣我們就沒辦法好好上課。你們覺得我可以怎麼辦呢?」
小孩睜著眼睛看我,說:「老師,你可以處罰我們啊!」
「處罰,你們想要被處罰嗎?」我驚訝地問。
「不想啊,可是你不處罰我們,我們就會吵。」小孩說。
今年台北詩歌節跟我問簡介時,我在最後一句寫了「覺得帶小孩上寫作課是目前生活中最花力氣的事」。不是寫作這件事情難,而是在寫作之前的所有東西難。在寫作之前有什麼呢?有生活、有人與人的關係、有思考與感受,這些都是相較於寫作更重要的東西,沒有這些,寫作什麼也不是。
十月初上課時,我帶小孩玩了一個遊戲。我準備了十三首短詩(你也可以把它想成短短的句子就好),分別寫在十三張紙條上,然後折成小方塊。「我們來抽籤,抽到籤的人把裡面的字唸出來,然後說說看自己想到什麼。」我說。
很神奇,第一個小孩抽到的是〈修剪〉。
〈修剪〉/ 瞇
用長剪將樹木修剪成人們想要的樣子
用規範將小孩修剪成大人希望的樣子
用法律將人民修剪成政府喜歡的樣子
抽到修剪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想跟他們討論關於規範和處罰的事,沒想到一開始就被抽到了。抽到籤的小孩讀一遍,另一個小孩說想讀,又讀了一遍。讀完之後我問:「你們想到什麼?」
小孩A說:「要把我們剪成你們想要的樣子喔!」
小孩B抱著自己的頭說:「不要,不要剪我的頭髮!」
我聽了覺得好好笑。我說不是要剪你的頭髮啦,不過規範和處罰就跟剪頭髮這種東西很像喔,就是把對方剪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可是你們有你們的想法,不會想要被剪對不對,要是被剪成自己不想要的樣子怎麼辦?不想被剪,就要有自己的想法;沒有自己的想法,就會被剪。自己對自己要有想法,不管是自己的頭髮,還是自己的行為。所以我不是一直說我不想要處罰你們嗎?就是這樣的道理,我不希望你們變成沒有想法的人。
我一口氣說了好多,小孩到底有沒有聽懂,我也不曉得。有些小孩點頭,有些小孩看著我。
「不要剪我!」小孩B又說了一次。
那次上課我給小孩讀我寫的短詩,其中有幾首剛好都提到了規範與法律的荒謬。我並不是故意選這些給小孩讀,而是沒辦法這幾年台灣社會這麼亂,關於某些體制的荒謬我無法不寫。有個小孩抽到了〈紅綠燈〉:
〈紅綠燈〉/ 瞇
他想走的時候就按綠燈
叫別人停的時候就按紅燈
他說
紅燈停
綠燈走
這是交通安全
他是依法行政
抽到的小孩說她覺得這首詩很搞笑。我問哪裡搞笑(我心裡想著我可不是為了搞笑寫的)。小孩說:「因為紅綠燈不是我們用的。」
這下我不懂了:「『紅綠燈不是我們用的』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紅綠燈不是我們用的啊!」小孩又說一遍。
我想了一下,突然腦袋開竅:「你的意思是,紅綠燈不是我們想要它紅燈就自己給它按紅燈,想要它綠燈就按綠燈的意思嗎?」
「對啦。」小孩說。
你看,這種道理小孩都懂,但那些搞政治的大人們都不懂。
有個小孩抽到〈不能說不〉。
〈不能說不〉/ 瞇
被關在籠子裡在美術館展覽的八哥不能說不
動物園裡的熊貓不能說不
馬戲團裡的猴子不能說不
海洋世界的海豚不能說不
水族箱裡的孔雀魚不能說不
田裡的水牛不能說不
受安樂死的貓狗不能說不
餐桌上的豬肉不能說不
遭廢水汙染的河川不能說不
被砍掉做成紙張的樹不能說不
(可以一直寫下去)
抽到的小孩問「可以一直寫下去」的意思是可以繼續寫嗎?我說對呀,你想寫嗎?小孩想了想,寫了兩句:
被關在家裡的小孩不能說不
圖書室的書不能說不
真是厲害。第一句應該不用我解釋了。第二句我想是因為寫作課是在圖書室上課,他有感而發吧。
我沒有跟小孩說什麼是詩,也沒有跟小孩說為什麼要這樣寫(他們也不曉得那是我寫的)。對他們來說那就是一個一個句子。我發現他們還蠻喜歡讀的,不曉得為什麼竟然還搶著讀,沒讀到的還會不高興。有些讀完之後會一直笑,有些小孩讀完之後會想要學著寫。我發現小孩C很會觀察,因為我完全沒有跟他說為什麼那首詩那樣寫,但我從他學著寫出來的東西,就發現他在進行分析了。
〈做什麼〉/ 瞇
你們住在鄉下
都在做什麼
那隻兔子一直趴著
在做什麼
星星在那邊亮著
做什麼
雲從這裡飄到那裡
做什麼
◆
〈做什麼〉 / 小孩C
他們在飛機上
都在做什麼
那隻大象一直喝水
在做什麼
太陽在那邊亮著
做什麼
海從這裡流到那裡
做什麼
仔細對照小孩C和我寫的,會發現小孩C會先觀察我怎麼寫,然後再開始寫。所以他把「你們」換成「他們」,把「鄉下」換成「飛機上」,把「兔子」換成「大象」,把「星星」換成「太陽」,把「雲」換成「海」。
雖然小孩C不一定明白這首〈做什麼〉想要說的東西,但這樣的觀察與仿作對他來說或許是有趣的。但我想他極有可能明白我在說什麼,因為當他讀完我寫的〈做什麼〉,第一句說出的話是「好無聊」。
◆
我一直說無法定義詩,但這樣的說法好像有點不負責任。就算我說不出詩是什麼,但一定有「我覺得什麼是詩」的一種想法吧!
我覺得有些詩像任意門,比如蔡仁偉的詩。他的〈食物鏈〉非常經典:
〈食物鏈〉/ 蔡仁偉
剪刀
石頭
布
這首詩根本就是從這裡到那裡最短距離的代表。不過,有些詩像任意門,不代表所有的詩都是任意門。
有些詩像遊戲,許赫的〈牧羊人的晚點名〉根本就是遊戲。不過這首晚點名點太久了,我就不在這裡點名了,請原諒。想要跟著牧羊人一起點名的人,可以去找《診所早晨的晴日寫生》這本詩集,找到〈牧羊人的晚點名〉這首詩,看你是要扮演點名的牧羊人還是被點名的羊都行。
而有些詩是生命,真正影響著我的詩是生命。這種詩沒有一定的樣子,不一定是誰寫的,但你讀見它你就知道你碰觸到了生命。而有些生命是詩。
這是我最想讓人觸碰到的東西,不管是寫的人還是讀的人,不管是小孩還是大人,還是我自己。而生命是一輩子的,生命卻也是片片段段的;詩也是這樣的東西。
不曉得為什麼寫到最後有點嚴肅,那來讀一首可能會笑出來的詩好了。很多人讀到〈有用〉這首詩都會笑,那來讀讀看會不會笑好了。不過,當初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下寫出〈有用〉的呢?實在是想不起來。看來,寫出〈有用〉的腦袋,有點不太有用呀。
〈有用〉/瞇
你太有用了
你太好用了
你太容易用了
沒有人比你更好用了
你生出來就是要被用的
孩子,你要做個有用的人
2014年10月24日 星期五
走往松菸的路上
走往松菸的路上
有一道牆
走往松菸的路上
有道假裝成樹木的牆
走往松菸的路上
假裝樹木的牆趕走了樹
走往松菸的路上
牆生出了蛋,蛋生出沒有生命的牆
走往松菸的路上
人沿著牆走
走往松菸的路上
人看不見牆
走往松菸的路上
沿著牆一直走會走到什麼地方
走往松菸的路上
人們對著黑夜中的人造光不停拍照
走往松菸的路上
我要去讀詩
走往松菸的路上
詩算什麼
走往松菸的路上
一群人準備去聽講
走往松菸的路上
我們聽到詩了嗎
(昨天我第一次進松山菸廠文創園區。從市政府出站,沿著巨蛋工事圍牆繞了一圈,心情很複雜。我當時想著有沒有可能在童詩的演講中穿插松菸巨蛋的事?但一直沒有找到適合的切入點。回家後心裡一直掛著這件事。)
◆ 此次北上沒帶相機,手機也不能拍照,所以借用風傳媒的照片
◆ 延伸閱讀:監委調查:工程4大爭議 大巨蛋現弊端
有一道牆
走往松菸的路上
有道假裝成樹木的牆
走往松菸的路上
假裝樹木的牆趕走了樹
走往松菸的路上
牆生出了蛋,蛋生出沒有生命的牆
走往松菸的路上
人沿著牆走
走往松菸的路上
人看不見牆
走往松菸的路上
沿著牆一直走會走到什麼地方
走往松菸的路上
人們對著黑夜中的人造光不停拍照
走往松菸的路上
我要去讀詩
走往松菸的路上
詩算什麼
走往松菸的路上
一群人準備去聽講
走往松菸的路上
我們聽到詩了嗎
(昨天我第一次進松山菸廠文創園區。從市政府出站,沿著巨蛋工事圍牆繞了一圈,心情很複雜。我當時想著有沒有可能在童詩的演講中穿插松菸巨蛋的事?但一直沒有找到適合的切入點。回家後心裡一直掛著這件事。)
◆ 此次北上沒帶相機,手機也不能拍照,所以借用風傳媒的照片
◆ 延伸閱讀:監委調查:工程4大爭議 大巨蛋現弊端
2014年10月15日 星期三
擁有的什麼,與被拿走的眼睛或生命
昨天H說他們家鄉有個神算,盲眼神算。十幾歲很年輕的時候生了場病,發著高燒做著夢時,有個老人對他說:「你以後會通曉天理,你可以靠這個吃飯。你的眼睛會看不見,但是不會餓死。」醒來後那個年輕人眼睛就盲了,此後成了神算,一個眼睛看不見不會餓死非常厲害的神算。
我說還好不是我,不然實在太衰了,我非得當個眼睛看不見的神算嗎?可不可以把我的眼睛還給我。H說,不當盲眼神算可以,可是選眼睛看得見的話會窮苦潦倒一輩子喔。我說哪有這種道理,只有這兩條路可以選嗎?
因為眼睛被拿走了,所以變成神算;還是因為要變成神算,所以只好用眼睛來交換?這種事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我沒辦法知道。
不曉得是昨天吹到風還是晚上沒睡好,今早起來頭痛。不是很痛的那種,是脹脹的沒什麼精神身體軟軟的那種頭痛。懶著身子起床,吃早餐時讀村上春樹寫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唱〈Light My Fire〉。
我沒聽搖滾樂,所以一點也不曉得吉姆‧莫里森是怎麼樣一號人物,也沒聽過〈Light My Fire〉。但是村上實在太會寫了,我讀完他寫的吉姆‧莫里森後,就忍不住上youtube找〈Light My Fire〉來聽了。
其實在聽之前我就有心理預備,我可能不會像村上春樹那樣有所感動。雖說音樂這東西沒什麼界限,但有時沒有背景(我並非生長在村上聽到那首曲子時的年代),音樂所要傳遞的什麼可能不一定能完全地接收到吧!
有了這樣的心理預備後,我找到The Doors的〈Light My Fire〉來聽。嗯,果然沒什麼特別的感動耶。我喜歡那歌詞,可是音樂的部份很難在第一時間有所共鳴。
但接著聽到的〈People Are Strange〉,它的歌詞和音樂都讓我起雞皮疙瘩。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re a stranger
Faces look ugly when youre alone
Women seem wicked when youre unwanted
Streets are uneven when youre down
When youre strange
Faces come out of the rain
When youre strange
No one remembers your name
When youre strange
歌詞我沒辦法翻譯,因為一旦翻譯成中文有些東西就會跑掉,我想詩就是這樣的東西。說這首歌詞是詩一點都不為過,「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re a stranger」,這不是詩那什麼是詩?
我問老斌「When youre strange / Faces come out of the rain」該怎麼理解才好。我好像可以抓到一點點什麼,卻無法明白地說出來。
〈People Are Strange〉是一首非常才華洋溢的詩。才華洋溢好像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那是否意味著要用某些東西去換呢?吉姆‧莫里森在二十七歲時死去。我對吉姆‧莫里森的了解非常有限,我對他的了解是村上春樹對他的了解:
「吉姆‧莫里森藉著迷幻藥LSD和古柯鹼煽動頭腦,藉著波本威士忌和琴酒煽動消化器官,把陰莖從長褲拉鍊拉出來煽動觀眾席時,我們可以感覺到他那痛。」
如果神算是用眼睛換來為人指點迷津,那麼天才詩人與搖滾樂手是否是用自己的生命為這個世界的人留下詩與音樂呢?當我覺得是要眼睛還是要天機實在太難為人了,因為我不想要天機可是也不想要顛沛流離。但如果我是吉姆‧莫里森呢?我想要那種洞析人性寫出天才詩作的生命,卻也想要活著的生命,這種事好像一樣難選。還好我不是吉姆‧莫里森或盲眼神算,我不用做那種困難的選擇,雖然成為盲眼神算和天才搖滾詩人可能也不是他們自己選的。
雖然我們也正在選擇自己的生命。
我說還好不是我,不然實在太衰了,我非得當個眼睛看不見的神算嗎?可不可以把我的眼睛還給我。H說,不當盲眼神算可以,可是選眼睛看得見的話會窮苦潦倒一輩子喔。我說哪有這種道理,只有這兩條路可以選嗎?
因為眼睛被拿走了,所以變成神算;還是因為要變成神算,所以只好用眼睛來交換?這種事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我沒辦法知道。
不曉得是昨天吹到風還是晚上沒睡好,今早起來頭痛。不是很痛的那種,是脹脹的沒什麼精神身體軟軟的那種頭痛。懶著身子起床,吃早餐時讀村上春樹寫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唱〈Light My Fire〉。
我沒聽搖滾樂,所以一點也不曉得吉姆‧莫里森是怎麼樣一號人物,也沒聽過〈Light My Fire〉。但是村上實在太會寫了,我讀完他寫的吉姆‧莫里森後,就忍不住上youtube找〈Light My Fire〉來聽了。
其實在聽之前我就有心理預備,我可能不會像村上春樹那樣有所感動。雖說音樂這東西沒什麼界限,但有時沒有背景(我並非生長在村上聽到那首曲子時的年代),音樂所要傳遞的什麼可能不一定能完全地接收到吧!
有了這樣的心理預備後,我找到The Doors的〈Light My Fire〉來聽。嗯,果然沒什麼特別的感動耶。我喜歡那歌詞,可是音樂的部份很難在第一時間有所共鳴。
但接著聽到的〈People Are Strange〉,它的歌詞和音樂都讓我起雞皮疙瘩。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re a stranger
Faces look ugly when youre alone
Women seem wicked when youre unwanted
Streets are uneven when youre down
When youre strange
Faces come out of the rain
When youre strange
No one remembers your name
When youre strange
歌詞我沒辦法翻譯,因為一旦翻譯成中文有些東西就會跑掉,我想詩就是這樣的東西。說這首歌詞是詩一點都不為過,「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re a stranger」,這不是詩那什麼是詩?
我問老斌「When youre strange / Faces come out of the rain」該怎麼理解才好。我好像可以抓到一點點什麼,卻無法明白地說出來。
〈People Are Strange〉是一首非常才華洋溢的詩。才華洋溢好像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那是否意味著要用某些東西去換呢?吉姆‧莫里森在二十七歲時死去。我對吉姆‧莫里森的了解非常有限,我對他的了解是村上春樹對他的了解:
「吉姆‧莫里森藉著迷幻藥LSD和古柯鹼煽動頭腦,藉著波本威士忌和琴酒煽動消化器官,把陰莖從長褲拉鍊拉出來煽動觀眾席時,我們可以感覺到他那痛。」
如果神算是用眼睛換來為人指點迷津,那麼天才詩人與搖滾樂手是否是用自己的生命為這個世界的人留下詩與音樂呢?當我覺得是要眼睛還是要天機實在太難為人了,因為我不想要天機可是也不想要顛沛流離。但如果我是吉姆‧莫里森呢?我想要那種洞析人性寫出天才詩作的生命,卻也想要活著的生命,這種事好像一樣難選。還好我不是吉姆‧莫里森或盲眼神算,我不用做那種困難的選擇,雖然成為盲眼神算和天才搖滾詩人可能也不是他們自己選的。
雖然我們也正在選擇自己的生命。
2014年10月12日 星期日
2014年10月11日 星期六
如果沒有來到這裡(記雪山行)
這回上山沒帶相機,因為背包已經完全塞不下了,我也沒智慧型手機,所以一張照片都沒有。其實心裡是有預備的,這回搞不好不會有任何一張照片。不過,在這個幾乎人人都有數位相機和智慧型手機的時代,同行的朋友要不留下一張照片都難。
但是,不拍照還有另一個原因──我想知道自己記得的還有多少;我想知道,我會如何描述這趟雪山行。
我的記憶很差,經常會忘記究竟哪一件事發生在哪一天,但對於某些時候眼前情景的樣子,卻可以記得很清楚,像是腦海中有張照片一樣。對於某些聽過的話或說過的話,也會記得很清楚。但是名詞這種東西就不行了。在雪山東峰,我們望著遠方稜線,小四由左至右一一說出那些山的名字,那些順序我一個都記不住──品田山、南湖大山、玉山、大霸尖山......那些山到底誰在左邊誰在右邊,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山大概的樣子、雲的樣子,天空的顏色,以及聽著那些名字時候的自己的心情。
在雪山主峰時也是。那些圍繞在我們身邊的山,我無法將那些山頭與它的名字一一連上;如果現在有張考卷,上頭有著山頭與山名連連看的題目,我保證我大概只能答對一兩題,還好山上沒有這種東西。
上到能夠清楚見到雲海的高度時,阿和一邊拍照一邊說著:「如果沒有來到這裡,不會知道這裡這麼漂亮。」小四說太遜了,再重新形容一次。我聽了覺得好好笑。不過真的,有時候當我們遇上某些景象,某些自己從未見過不曉得該怎麼形容的風景,就只會說「好漂亮」、「非常漂亮」、「漂亮到不行」、「怎麼會那麼漂亮」……
我想詞窮也是對美景的一種形容吧,因為文字不足以描述眼前的風景。
但如果一定要形容呢?如果我們所述說的對象終其一生無法見到我們所見到風景。可是,我要如何描述、如何形容所見之物?
我沒有看過雲那種樣子。它們像白色奶泡一樣相互緊靠著、堆擠著;它們漫過山的稜線,從線的邊邊流下。奶泡實在是擠得太滿了,有一種山巒與山巒之間全部都是奶泡的錯覺。因為太滿了,所以只好流出來。但是流出來的奶泡下到一定的高度後就漸漸消散、不見了,而山谷中的奶泡繼續不斷膨脹、漫出、流瀉,然後消失,像一段一直重覆播放的奶泡動畫。
還有什麼呢?早晨六點多從三六九山屋往遠方望去,也有一種錯覺,這次是看到大海的錯覺。雲像白色的浪,但是是靜止的浪,又像結凍的冰。我開玩笑說如果拍張照片,帶去學校問小孩這是什麼,說不定有小孩會說這是海喔,說不定有小孩會說是冰河。
白色的雲安靜地依著山,像白色的浪靠在山的腳邊。只是浪啪搭啪搭,雲靜靜悄悄。
山頂上天氣好的時候,雲永遠在我們的下方,除非走進森林,否則沒有任何什麼可以遮住太陽。這時我才明白什麼叫做百分百紫外線,原來就是這種東西。第一天還好,第二天覺得嘴唇稍微有點腫脹,第三天差不多就烤成香腸嘴了。
儘管行程安排得鬆,但對於沒有什麼高山經驗的我來說,喘還是會喘,登頂之後頭還是會痛。「再怎麼輕鬆,身體還不能適應的時候,該有的感覺還是都會有。」我一邊拄著登山杖,一邊抬高腿向上走,一邊這樣感覺著。累雖然會累,但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而累這種東西之所以能夠忍受是因為,我們知道累的終點。
上山前有段時間,我睡前會看一兩集阿信。「窮人的苦的終點,是眼睛閉上的那一刻」,那是一種沒有出口的辛苦。當上坡的路稍長,我總是會想到那種沒有出口的辛苦,然後慶幸自己腳下的路,只要再幾十分鐘就能走完。
但為什麼要千里迢迢來爬雪山呢?好吧沒有千里迢迢,但也有百里吧!平常也不爬山的,為什麼要背著裝備來爬高山呢?這件事在走向陽的時候我就想過,但似乎沒有什麼答案。這次我想到了,這大概跟為什麼我會搬到鹿野差不了多少。
如果沒有認識小四阿春,我大概不會爬高山;如果沒有認識老斌,我大概不會搬來鹿野。但話好像也不是這樣講,如果不認識小四阿春,說不定我還是會認識其他別的什麼人,然後還是去爬高山;如果不認識老斌,我也可能會認識其他什麼人,結果還是搬到了鄉下。不過生命這種事沒有如果;如果沒有他們,會不會有別的誰,這種事我一點都不可能知道。
我能知道的是,因為他們,所以我有那麼一條線能夠順著來到鹿野,有那麼一條線能攀著往高山去。但那都只是線而已,最後決定的還是自己的手跟腳。
可是我的腳為什麼走到現在這個地方呢?因為不走到這裡就無法明白某些事情。但為什麼要走過來呢?我想都是因為人喔。
◆
補記:只會說「很漂亮」的阿和,在旅程第四天說出了超厲害的形容──
阿和指著一杯紫紅色的火龍果鳳梨果汁和一杯暗褐色的葡萄檸檬說:「這杯有夠水,那杯干嘛塞。」(請以台語發音)。
阿和看著已經被吐出來的月亮說:「半個月全食的時間,差不多是我們喝一杯飲料聊天的時間。」
但是,不拍照還有另一個原因──我想知道自己記得的還有多少;我想知道,我會如何描述這趟雪山行。
我的記憶很差,經常會忘記究竟哪一件事發生在哪一天,但對於某些時候眼前情景的樣子,卻可以記得很清楚,像是腦海中有張照片一樣。對於某些聽過的話或說過的話,也會記得很清楚。但是名詞這種東西就不行了。在雪山東峰,我們望著遠方稜線,小四由左至右一一說出那些山的名字,那些順序我一個都記不住──品田山、南湖大山、玉山、大霸尖山......那些山到底誰在左邊誰在右邊,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山大概的樣子、雲的樣子,天空的顏色,以及聽著那些名字時候的自己的心情。
在雪山主峰時也是。那些圍繞在我們身邊的山,我無法將那些山頭與它的名字一一連上;如果現在有張考卷,上頭有著山頭與山名連連看的題目,我保證我大概只能答對一兩題,還好山上沒有這種東西。
上到能夠清楚見到雲海的高度時,阿和一邊拍照一邊說著:「如果沒有來到這裡,不會知道這裡這麼漂亮。」小四說太遜了,再重新形容一次。我聽了覺得好好笑。不過真的,有時候當我們遇上某些景象,某些自己從未見過不曉得該怎麼形容的風景,就只會說「好漂亮」、「非常漂亮」、「漂亮到不行」、「怎麼會那麼漂亮」……
我想詞窮也是對美景的一種形容吧,因為文字不足以描述眼前的風景。
但如果一定要形容呢?如果我們所述說的對象終其一生無法見到我們所見到風景。可是,我要如何描述、如何形容所見之物?
我沒有看過雲那種樣子。它們像白色奶泡一樣相互緊靠著、堆擠著;它們漫過山的稜線,從線的邊邊流下。奶泡實在是擠得太滿了,有一種山巒與山巒之間全部都是奶泡的錯覺。因為太滿了,所以只好流出來。但是流出來的奶泡下到一定的高度後就漸漸消散、不見了,而山谷中的奶泡繼續不斷膨脹、漫出、流瀉,然後消失,像一段一直重覆播放的奶泡動畫。
還有什麼呢?早晨六點多從三六九山屋往遠方望去,也有一種錯覺,這次是看到大海的錯覺。雲像白色的浪,但是是靜止的浪,又像結凍的冰。我開玩笑說如果拍張照片,帶去學校問小孩這是什麼,說不定有小孩會說這是海喔,說不定有小孩會說是冰河。
白色的雲安靜地依著山,像白色的浪靠在山的腳邊。只是浪啪搭啪搭,雲靜靜悄悄。
山頂上天氣好的時候,雲永遠在我們的下方,除非走進森林,否則沒有任何什麼可以遮住太陽。這時我才明白什麼叫做百分百紫外線,原來就是這種東西。第一天還好,第二天覺得嘴唇稍微有點腫脹,第三天差不多就烤成香腸嘴了。
儘管行程安排得鬆,但對於沒有什麼高山經驗的我來說,喘還是會喘,登頂之後頭還是會痛。「再怎麼輕鬆,身體還不能適應的時候,該有的感覺還是都會有。」我一邊拄著登山杖,一邊抬高腿向上走,一邊這樣感覺著。累雖然會累,但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而累這種東西之所以能夠忍受是因為,我們知道累的終點。
上山前有段時間,我睡前會看一兩集阿信。「窮人的苦的終點,是眼睛閉上的那一刻」,那是一種沒有出口的辛苦。當上坡的路稍長,我總是會想到那種沒有出口的辛苦,然後慶幸自己腳下的路,只要再幾十分鐘就能走完。
但為什麼要千里迢迢來爬雪山呢?好吧沒有千里迢迢,但也有百里吧!平常也不爬山的,為什麼要背著裝備來爬高山呢?這件事在走向陽的時候我就想過,但似乎沒有什麼答案。這次我想到了,這大概跟為什麼我會搬到鹿野差不了多少。
如果沒有認識小四阿春,我大概不會爬高山;如果沒有認識老斌,我大概不會搬來鹿野。但話好像也不是這樣講,如果不認識小四阿春,說不定我還是會認識其他別的什麼人,然後還是去爬高山;如果不認識老斌,我也可能會認識其他什麼人,結果還是搬到了鄉下。不過生命這種事沒有如果;如果沒有他們,會不會有別的誰,這種事我一點都不可能知道。
我能知道的是,因為他們,所以我有那麼一條線能夠順著來到鹿野,有那麼一條線能攀著往高山去。但那都只是線而已,最後決定的還是自己的手跟腳。
可是我的腳為什麼走到現在這個地方呢?因為不走到這裡就無法明白某些事情。但為什麼要走過來呢?我想都是因為人喔。
◆
補記:只會說「很漂亮」的阿和,在旅程第四天說出了超厲害的形容──
阿和指著一杯紫紅色的火龍果鳳梨果汁和一杯暗褐色的葡萄檸檬說:「這杯有夠水,那杯干嘛塞。」(請以台語發音)。
阿和看著已經被吐出來的月亮說:「半個月全食的時間,差不多是我們喝一杯飲料聊天的時間。」
(照片:阿春)
早餐亂想:錢這個東西
今天吃早餐時,移動盤子時突然發現桌上有一小疊錢幣。嗯,通常我們吃飯前不是多半會先把桌子收一收,如果桌上有什麼不是這頓早餐或午飯的東西,會先擱到別的地方去。但不曉得為什麼,那疊錢幣在那裡;大概是因為它所在的位置對它來說不是很自然,我突然思考起錢這個東西的用途。
一圓錢幣、五圓錢幣、十圓錢幣疊著;其實錢幣也可以當積木來玩,當疊疊樂好像也不錯。如果設計得夠好看的話,會不會也有人會用來當裝飾性的鑲嵌呢?比如窗框、牆壁啦。但是由於錢幣這種東西承載了錢的用途,它就不再只是一個圓形的有圖案的硬幣了。一旦硬幣具備了錢的功能,它幾乎都不會再被拿來做其他的用途,除非那個硬幣的錢的功能喪失,比如一個五百年前的硬幣(當然有人認為「古董」另有其「價值」)。
鈔票就更不用說了,正常人應該都不會拿鈔票當壁紙糊在牆上吧!不過,當錢的的功能喪失就另當別論。錢的功能喪失是什麼意思呢?第一種意思是那個鈔票再也不能拿來換東西了,比如貶值貶到某個地步跟張白紙一樣。第二種意思是鈔票太多多到失去了意義,多到就算有好幾輩子都用不到的程度;雖然說現在所謂「財產」這種東西並不是真的以「鈔票」的形式存在著,而是以「數字」的概念存在。但我們還是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將「十個一百億」這個數字換成台幣千圓大鈔,那可以換成多少千圓大鈔呢?當0太多我對它就無法具體想像了,我能想像的只有那無法想像的千圓大鈔們被綑成一疊一疊堆疊著,從被製造出來的那一天就沒有被使用過,不管是拿去交換成別的東西或者當壁紙使用。
有時寫著寫著就會寫到自己原本沒想到的地方去,不寫就不會知道的地方。本來想說的是,錢幣也不過就是圓圓的具有圖案的硬硬的東西,它其實除了作為錢也可以當別的什麼,比如當小孩還不曉得錢是用來幹嘛的時候,極有可能把錢幣拿來咬,拿來疊疊樂,把鈔票拿來當色紙摺紙飛機,或是在上頭塗鴉。
2014年10月4日 星期六
雖然寫東西這件事很沒有用
今天早上讀了一篇村上春樹為高橋秀實《魁儡民主主義》所寫的解說(或稱序文)。讀到後來我笑出來。雖然我明白高橋先生應該是真的很傷腦筋,某種程度來說,我對這種傷腦筋所傷的腦筋有過之而無不及,超過的程度有時候都快要傷到身體了。不過,看到高橋先生和村上春樹可以用這樣認真又幽默的態度看待傷腦筋的事(至少在文章中的表現是這樣的),甚至用「傷腦筋」這種聽起來不傷身體的字眼來形容自己所面對和思考的事,就不得不佩服他們。
我什麼時候才能像文章中的他們,看待生命中傷腦筋的事呢?
◆
〈我們正活在這傷腦筋的世界〉
高橋秀實是個有點怪的人,每次見到面總會說「啊,傷腦筋,好洩氣。」(中略)沒結論,這當然是當時他的主要煩惱。越是認真地親自用腳跑採訪,實際花時間去聽很多人的話之後,結論越出不來。知道和那件事有關的各種人的情況,某種程度也知道出現不同想法的來龍去脈,就不可能將各種要素俐落地區分為白或黑,簡單地順口說出「各位,這就是正確的結論!」之類的話。
我非常了解高橋所感覺到的,想說的事,瞭解得真痛的地步。我在寫關於沙林毒氣事件的《地下鐵事件》時也深深感覺到,世上的事情,很多情況往往沒有什麼結論。尤其是越重要的事,那種傾向越強。自己親自用腳跑過所收集的第一手情報越多,採訪所花的時間越多,事情的真相越混濁、方向越迷失。結論離得越來越遠,觀點變得更分歧。不得不變那樣。結果,我們也束手無策。逐漸搞得不清楚什麼是正確/不正確,哪一邊在前,哪一邊在後了。
不過,我確信,有些情況是非要穿過這種混濁才能看得見的。在那看得見的情景之前需要花時間,看得見的那情景要以簡短語言明確傳達給讀者是非常困難的。不過如果不經過這個階段,應該無法產生稍微有點價值的文章。因為寫作者的任務(無論是小說,或非小說)原則上都不是在傳達單一的結論,而是在傳達情景的總體。
當然或許我也可以說「高橋先生也是專業作者,也有你的生活,如果把工作當工作想開了,在這裡只要適度製造出一個結論加上去就行了。這樣編輯和讀者都可以接受」給他一個現實的建議。不過我說不出那種話,這種事情高橋先生應該也辦不到。
因此以我來說,結果,我就變得不得不說「嗯,那個有點沒辦法啊」。於是兩個人便交抱雙臂,事情總算結束了。
本書讀過一遍,我首先感覺到的是,「這本書沒錯百分之一百是高橋秀實的書」。
1.調查得很詳細。
2.以正當方式洩氣(不得不)。
3.把那盡量寫成親切的文章。
──村上春樹,〈我們正活在這個傷腦筋的世界〉,《雜文集》
◆
以上三個特質我最做不到的就是「以正當方式洩氣」了。我一洩氣起來真是沒完沒了,自己都有一種「是要洩到沒氣為止的地步嗎?」當然我現在能這樣寫,已經沒有在洩氣了。
雖然我經常覺得寫文章沒有用,比起許多事來寫東西這件事一點用處也沒有。但我自己卻經常被別人所寫的東西打氣了,比如村上春樹。
「打氣」,在洩氣的時候讀到打氣的文章真的是被打氣了。我什麼時候可以像文章中的他們,淡然地看著洩氣的事或洩氣的自己呢?搞不好沒有這樣的一天。但是我知道,在洩氣時我總是以為自己會這樣永無止境地洩氣下去,但其實有時候吃個飯就好了,睡個覺就好了,起來上個廁所就好了。
雖然寫東西這件事很沒有用,有時候還會覺得很不好意思。但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
我什麼時候才能像文章中的他們,看待生命中傷腦筋的事呢?
◆
〈我們正活在這傷腦筋的世界〉
高橋秀實是個有點怪的人,每次見到面總會說「啊,傷腦筋,好洩氣。」(中略)沒結論,這當然是當時他的主要煩惱。越是認真地親自用腳跑採訪,實際花時間去聽很多人的話之後,結論越出不來。知道和那件事有關的各種人的情況,某種程度也知道出現不同想法的來龍去脈,就不可能將各種要素俐落地區分為白或黑,簡單地順口說出「各位,這就是正確的結論!」之類的話。
我非常了解高橋所感覺到的,想說的事,瞭解得真痛的地步。我在寫關於沙林毒氣事件的《地下鐵事件》時也深深感覺到,世上的事情,很多情況往往沒有什麼結論。尤其是越重要的事,那種傾向越強。自己親自用腳跑過所收集的第一手情報越多,採訪所花的時間越多,事情的真相越混濁、方向越迷失。結論離得越來越遠,觀點變得更分歧。不得不變那樣。結果,我們也束手無策。逐漸搞得不清楚什麼是正確/不正確,哪一邊在前,哪一邊在後了。
不過,我確信,有些情況是非要穿過這種混濁才能看得見的。在那看得見的情景之前需要花時間,看得見的那情景要以簡短語言明確傳達給讀者是非常困難的。不過如果不經過這個階段,應該無法產生稍微有點價值的文章。因為寫作者的任務(無論是小說,或非小說)原則上都不是在傳達單一的結論,而是在傳達情景的總體。
當然或許我也可以說「高橋先生也是專業作者,也有你的生活,如果把工作當工作想開了,在這裡只要適度製造出一個結論加上去就行了。這樣編輯和讀者都可以接受」給他一個現實的建議。不過我說不出那種話,這種事情高橋先生應該也辦不到。
因此以我來說,結果,我就變得不得不說「嗯,那個有點沒辦法啊」。於是兩個人便交抱雙臂,事情總算結束了。
本書讀過一遍,我首先感覺到的是,「這本書沒錯百分之一百是高橋秀實的書」。
1.調查得很詳細。
2.以正當方式洩氣(不得不)。
3.把那盡量寫成親切的文章。
──村上春樹,〈我們正活在這個傷腦筋的世界〉,《雜文集》
◆
以上三個特質我最做不到的就是「以正當方式洩氣」了。我一洩氣起來真是沒完沒了,自己都有一種「是要洩到沒氣為止的地步嗎?」當然我現在能這樣寫,已經沒有在洩氣了。
雖然我經常覺得寫文章沒有用,比起許多事來寫東西這件事一點用處也沒有。但我自己卻經常被別人所寫的東西打氣了,比如村上春樹。
「打氣」,在洩氣的時候讀到打氣的文章真的是被打氣了。我什麼時候可以像文章中的他們,淡然地看著洩氣的事或洩氣的自己呢?搞不好沒有這樣的一天。但是我知道,在洩氣時我總是以為自己會這樣永無止境地洩氣下去,但其實有時候吃個飯就好了,睡個覺就好了,起來上個廁所就好了。
雖然寫東西這件事很沒有用,有時候還會覺得很不好意思。但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
2014年10月3日 星期五
2014年10月2日 星期四
變厚
昨天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竟然在一個月內做了三百個帆布袋拓繪,想想我這一年多來也才做了兩百件左右的T恤。在短時間累積起一定的量,雖然不是自己計畫的,但是拓繪的功力好像在一次一次上色按壓中慢慢變厚,就像油漆隨著一層一層塗刷會一點一點變厚一樣;我握筆那隻手的大拇指下方連接掌心的那塊肌肉好像也變厚了,捏捏另一隻手就會知道。
「變厚」大概是這三百個稻子拓繪的關鍵詞了。
我一開始還覺得怎麼可能,真正做起來才發現這三百個拓繪跟有些事比起來,還真是小CASE。什麼事呢?大概就是自己的心情吧。這一個月來有些事情在想著,有些只有自己知道的,不清不楚的事在想著;這種狀態很麻煩,像流不乾淨的月經一樣,量不多卻滴滴答答的,不曉得何時會結束。
這種狀態代表自己一定有些什麼跟之前不一樣的地方,所以她才會一直流;所以好像也急不得,就只能等,把該流的流乾淨了,說白話一點就是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自然就會停了。但是究竟什麼時候會想清楚,或是會停了,某種程度好像也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事。
不曉得算是幸運還是不幸,這個莫名其妙的狀態跟這三百個帆布袋拓繪的工作期恰好撞在一起。「一定是工作太累了才會這樣怪怪的」,會讓人有這樣的錯覺。但我自己知道不是,我只是因為某種心裡的小事在鑽牛角尖而已。
我有時一邊鑽牛角尖,一邊做著拓繪,因為不這樣進度無法完成。有時候會想,我能不能乾脆放著就先任性地鑽牛角尖呢?可惜我已經不是十年前的我了,這樣的事我現在做不到。但也因為這樣,反覆做著拓繪的過程,會稍稍將我從牛角尖中拉出來一點點。我是個自私又任性的人,不過這十年來應該還是有一點點長進吧。
拓繪按著進度完成了。因為心裡有著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完成的時候,也不太有什麼很開心的感覺。不過終究是完成了,沒有因為自己的緣故,對不起什麼人。
然後非常奇怪地,在完成的那一天晚上,我竟然睡得出奇地好。這一個月來沒有睡得那麼好了。放在心裡的事雖然還沒有解決,但似乎沒那麼重了。好像水龍頭被關緊了,莫名其妙的東西沒有再滴滴答答地流出來了。不過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再被打開。
不過,我似乎不擔心這樣的事。雖然莫名其妙的時候很累,身邊的人也累,但我想我應該有慢慢地變厚了。慢慢變厚,厚到可以保護。
我竟然在一個月內做了三百個帆布袋拓繪,想想我這一年多來也才做了兩百件左右的T恤。在短時間累積起一定的量,雖然不是自己計畫的,但是拓繪的功力好像在一次一次上色按壓中慢慢變厚,就像油漆隨著一層一層塗刷會一點一點變厚一樣;我握筆那隻手的大拇指下方連接掌心的那塊肌肉好像也變厚了,捏捏另一隻手就會知道。
「變厚」大概是這三百個稻子拓繪的關鍵詞了。
我一開始還覺得怎麼可能,真正做起來才發現這三百個拓繪跟有些事比起來,還真是小CASE。什麼事呢?大概就是自己的心情吧。這一個月來有些事情在想著,有些只有自己知道的,不清不楚的事在想著;這種狀態很麻煩,像流不乾淨的月經一樣,量不多卻滴滴答答的,不曉得何時會結束。
這種狀態代表自己一定有些什麼跟之前不一樣的地方,所以她才會一直流;所以好像也急不得,就只能等,把該流的流乾淨了,說白話一點就是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自然就會停了。但是究竟什麼時候會想清楚,或是會停了,某種程度好像也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事。
不曉得算是幸運還是不幸,這個莫名其妙的狀態跟這三百個帆布袋拓繪的工作期恰好撞在一起。「一定是工作太累了才會這樣怪怪的」,會讓人有這樣的錯覺。但我自己知道不是,我只是因為某種心裡的小事在鑽牛角尖而已。
我有時一邊鑽牛角尖,一邊做著拓繪,因為不這樣進度無法完成。有時候會想,我能不能乾脆放著就先任性地鑽牛角尖呢?可惜我已經不是十年前的我了,這樣的事我現在做不到。但也因為這樣,反覆做著拓繪的過程,會稍稍將我從牛角尖中拉出來一點點。我是個自私又任性的人,不過這十年來應該還是有一點點長進吧。
拓繪按著進度完成了。因為心裡有著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完成的時候,也不太有什麼很開心的感覺。不過終究是完成了,沒有因為自己的緣故,對不起什麼人。
然後非常奇怪地,在完成的那一天晚上,我竟然睡得出奇地好。這一個月來沒有睡得那麼好了。放在心裡的事雖然還沒有解決,但似乎沒那麼重了。好像水龍頭被關緊了,莫名其妙的東西沒有再滴滴答答地流出來了。不過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再被打開。
不過,我似乎不擔心這樣的事。雖然莫名其妙的時候很累,身邊的人也累,但我想我應該有慢慢地變厚了。慢慢變厚,厚到可以保護。
(照片:楊老斌)
(照片:大眼睛)
2014年10月1日 星期三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