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續讀《如刀的書寫》,有種更確定自己方向的感覺。回想五月至今對自己書寫的質疑,質疑自己是否無法寫「另一種東西」;我質疑自己靠直覺書寫,是否會經不起考驗?現在回想,那有點是為了挑戰而挑戰,為了證明而證明,為了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寫「虛構」,我想試著將一個想寫的東西寫成「小說」,卻有種不服貼的感覺。
讀安妮‧艾諾,知道她也曾為了寫小說而寫小說,但後來她找到自己的敘事方式,她打破虛構小說與自傳體小說的界線,寫出不是虛構也非自傳的「集體價值」──
「那是以『我』為出發點的自傳故事所帶出的集體價值,比起『普遍價值』,我更偏好集體價值一詞,畢竟沒有什麼經歷是普遍的。『我』的集體價值,亦即文本世界的集體價值,在於它超出了個人經歷的獨特性。」(p.62)
從前我不太明白為何滌可以引起某些人的共鳴,我覺得我就是寫自己,現在好像有點明白了。當我讀到安妮‧艾諾的《位置》、《一個女人》、《沉淪》,在我還不知道她對書寫的思考時,我先被她的書寫吸引。剛開始我以為那些是她以「我」為基底然後稍加改造的虛構小說,後來才知道不是,她就是在寫自己。但她不去說這是小說,或不是小說。當我讀到她的思考時,我更加確認了自己書寫的位置。
我在還不清楚為何要這麼寫的時候,直覺這麼去寫,後來卻對自己有所質疑,認為所有的東西都可以這樣寫嗎?如果我只能這樣寫,那我是不是不算會寫?那陣子讀鄧九雲的《女二》,讀《最初看似新奇的東西》,深受改造現實與虛構吸引。我看到好多人寫小說,我也想試著寫看看,我想知道自己能不能駕馭虛構;還有就是──我想寫的那個東西,把「我」擺出來的風險太高了,躲在小說後面感覺比較安全。
但最近發生的事,我去看自己,我重新思考書寫對我的意義。我發現「寫」與「我」的連結極深,那個連結是我為何要寫的基底。當那個不得不寫的東西出現,寫作這件事會自然的發展下去,長出她自己的樣子。
我現在有點明白,那個以我父母與彩色沖印為主題的新書稿,為何總是卡卡不順,雖然一方面是因為題材不夠熟悉,但更大的原因可能是──我認為它「該寫」,但對我來說還不算是「不得不寫」。但寫作者可以只寫「不得不寫」的東西嗎?但為什麼不行呢?
我沒有要放棄那份書稿,而是想重新回到原點來看。沒有什麼是「該寫」,只有「想寫」的東西。當我回到這個原點,再去看那份書稿以及採訪過程中所留下的,哪些東西最後會被寫出來,會很自然的出現。當我回到原點,取捨就不會是困難的事,不會有「我花了那麼多時間力氣所做的採訪該怎麼辦?」我也不再急著馬上要拾起書稿。
當然也不會一直放著,我會看現狀來安排。雖然我現在有更想寫的,已經開始寫的東西。而對這兩者我都不急,我能做的就是規劃寫作時間,回到像是每日長跑的狀態,每天跑一些,每天寫一點。
◆
昨天跟鄧九雲討論「取消」。「取消」,是她在空總讀劇的計畫。她說:「我的書寫要取消什麼?才能對等妳取消虛構。」
看到這問題我第一個感覺是:她為什麼要思考這個問題?第二個感覺是:我是取消虛構嗎?看起來好像是,但更接近的是「取消界線」。取消像是拿掉,拿掉什麼,不要被什麼綁住。我想拿掉文體的界線。我不想被界線綁住,不想被框住。不論是書寫或是人生。
然後我問九雲,在寫作這件事上,你「真的有」想要「取消」的什麼嗎?還是為了思考要取消什麼,而去思考要取消什麼?當我聽了她的回答後,我發現當我思考取消時,是以「我」為出發,「我」要取消什麼?這個我是真實本體的我。而九雲思考「取消」時,感覺是一種模擬,像是思考實驗,「在書寫這件事上,『我』可以取消什麼?」這個「我」不見得是她自己,而是虛擬的「我」的角色。
光是從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來看,就可看出我們在寫作上做了不同的選擇。「在寫作這件事上,你最怕的是什麼?」我問。「我怕我只能把經歷過的寫得好。我怕我的經驗大於我的能力。」九雲說。
九雲怕自己只能寫經歷過的,她不想被這個綁住。而我是只能寫自己經歷過的,從前我怕自己被這個綁住,但現在我不怕了。
「你有看過里米尼紀錄劇團嗎?」
「沒有。已經好久好久沒看戲了。」
九雲拍了《日常專家:你不知道的里米尼紀錄劇團》的書頁內容給我。我讀到其中兩段:
「虛構(fiction)和虛構性(fictiousness)源於拉丁語fingere,原意是指組成、形成、塑造,也就是有意賦予事物形式的行為;拉丁語動詞延伸的含意則是編造和假裝,所以我們應該把『虛構』理解成大致上來說是個發明,尤其是在由語言創造的世界中的發明。在這樣的虛構世界裡,真和假的範疇變得毫無意義。」
「伊瑟爾認為,虛構行為的本質是選擇和組合,即使被選擇和組合的元素不是虛構的,選擇和組合的行為本身就是虛構化的過程。」
這兩段話再次打破我對虛構的認識。誰說虛構就是不存在,就是編造?所以我再也不用怕自己不會虛構?因為即使是書寫自己的經驗,也可以說是虛構?
2023年9月14日 星期四
以「我」為出發的集體價值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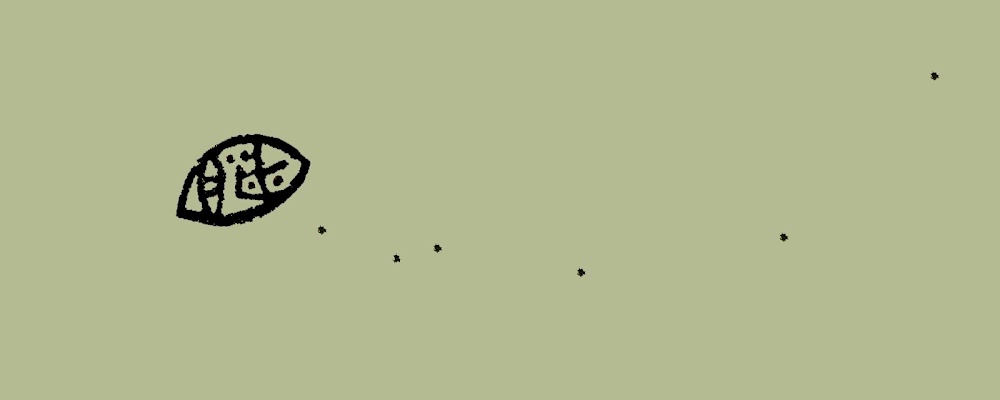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