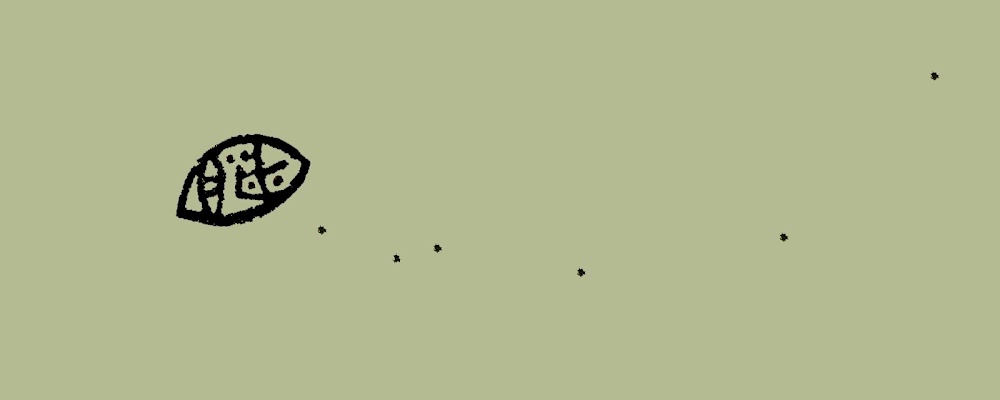回到台北朋友住處,簡單打一下現在腦袋裡的東西。
今天一下火車,就直跑慕哲咖啡館。黃致豪律師要講王景玉案。早上我才看過判決,可是有很多看不懂。並不是真的完全不懂,我整個快速看過,挑看得懂的看,多少還是可以拼出一些脈絡。到了會場,黃律師問我,看了判決有什麼心得嗎?有解決我心中的疑惑嗎?我當時才剛到會場,還有點喘,肚子有點餓,腦袋空空,什麼都講不出來。我本來想要趁講座前趕快吃一點麵包,但很快講座就開始了,我打開筆電,開始聽講做記錄。
我開始聽講,我很想專心,但大概是一路戴了很久的口罩,火車上四小時,加上現在,加上現場人多,我覺得呼吸有點不順。我肚子很餓,我很想吃一口麵包,但因為我坐在最前面,兩位講者就在我面前,我不好意思拿麵包出來吃。這時候我想,如果是滌,肚子餓了應該就會把麵包拿出來吃吧,因為這個麵包又沒有很重的味道,不會影響到別人。但我不是滌,而且我坐最前面,而且我很想聽。
過了一個小時,肚子比我想像得餓,而且我開始覺得有點頭暈。這時彭醫師剛好在講精神鑑定,在講有沒有行為能力,在講控制。這時我覺得,現在的我的腦袋根本沒辦法控制我的腦袋,喔不,我正控制著自己不要吃麵包,不要離開座位,但是我無法控制我腦袋的思考,這時候如果有人突然問我,對台上講者內容的反應,我一定什麼都說不出來。
我那時閃神,我想著,我是一個所謂的「正常人」,但我完全無法思考我的思考。這時如果突然有人要我分析什麼,我一定分析得亂七八糟。過了一個小時半,我覺得我的頭有點暈,肚子,好像有點怪怪的,我很想上廁所,我想不行我不能再顧及什麼禮貌了。我還是很想聽QA,但我知道我繼續坐在那裡也沒有意義,因為我的腦袋已經不是我的腦袋了。當黃律師和彭醫師講到一個段落後(我甚至在等一個段落),我拿起隨身包和麵包,走出講座會場,到旁邊的咖啡廳。
我先去上廁所,一脫褲子我嚇一跳。好多血。我以為我的月經已經結束,但她又來了,量很多,而且屬於會滴的那種。我吸一口氣,還好我還墊著護墊,雖然都滿出來了。量很驚人,我坐著等她滴完,想著難怪剛剛覺得頭有點暈。然後我想著還好我有帶隨身布包,有衛生棉,還好廁所有衛生紙,雖不多但剛好夠用。
我花了一點時間清理,清理好後走出廁所。我點了一杯卡布,然後拿出麵包開始吃。吃麵包的時候,我發現店員在看我,我想著是不是不能用外食。但我實在是不行了我一定要馬上吃,我想著怎麼會把自己弄得那麼不舒服。店員繼續看我,我繼續吃。
我想著如果是滌,一定不會解釋自己為什麼在吃麵包。但我不是滌,我知道店員看我的原因。店員送咖啡來的時候,我主動說,請問不能用外食對嗎?店員點頭。我說不好意思因為我現在人很不舒服,我一定要馬上吃點東西。店員點頭表示可以理解,她說沒關係你的麵包沒有什麼味道,而且現在已經很晚了。
我想著在所有可能引發不解的時候,如果其中一方願意主動說明什麼,那麼誤解就可能減少。但那是因為我還有餘裕。如果我當下不舒服的程度比那個願意說話的自己高上五倍呢?我還願意說明自己的狀況嗎?我可能不願意說明因為我顧不到。但店員有可能因此認為這個人奇怪,不知道咖啡館禁用外食嗎?他不會知道我不舒服。
後來我一邊吃麵包,一邊聽著會場內黃律師的聲音。我想到他剛剛講的刑法,他說刑法與刑事訴訟設計的用意,是為了保護被告的權益。保護被告的權益?我覺得這聽在一般大眾的耳朵裡,應該覺得不可思議。「他們是犯罪的那一方耶!為甚麼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我發現法律上所講的罪,跟一般大眾所認為的罪,似乎有著定義上的落差。一般大眾所認為的罪,是「犯行」;而法律上所認為的罪,是一個人是否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能力,這個人是否有「完全責任能力」?
可是什麼叫做「完全責任能力」?一個人究竟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到什麼地步?
我們都直覺的覺得,一個人一旦成人,不是笨蛋不是白痴,他應該就要能為自己負責。可是我想著我自己剛剛的狀態,自己那個很不舒服的狀態,我可以覺察到那個時候我的判斷能力比「平常」要低。這不是說我無法判斷,但我有可能做出比較差的判斷,或是我的判斷就跟著身體或情緒的狀況走。
我想著如果把我的不舒服放大到十倍,或是一百倍,那我還能做出好的判斷嗎?我還能為我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嗎?但我又可以想像有人一定會說,「那你為什麼要讓自己落入很慘的處境?」嗯,這個社會似乎認為一個人若落入很慘的處境,一定與他自己有關,他該為自己負責。
確實我剛剛也想著,我幹嘛要把自己弄成這樣,我為什麼要那麼趕?我為什麼要提著行李走爬四層樓的樓梯導致出血?我為什麼不多走點路坐電梯?我不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嗎?我知道啊為什麼我沒有避免?
但我沒有影響到別人,看起來沒有,因為我努力讓自己的不舒服,不要影響到別人。但如果有些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某些行為呢?「那他就不要出來,不要出來外面亂走。」我想起有次有個鄰居說,「你弟為什麼都走地下室停車場的坡道?他為什麼不走大門?為什麼我問他他不回答?為什麼他很兇地看我?」
我試著解釋給對方聽,我說我弟走地下室是因為他不喜歡碰到人,所以他選人少的地方走,「你覺得你怕他,其實他才怕你。」「那他為什麼要那種眼神?他為什麼要罵人?」我說,他罵的對象不是你這個人,而是你說的話讓他直接反應,他覺得他走地下室又不關你的事,「他對你沒有敵意,他碎唸白癡是因為你說的話。他不想回答你是因為他覺得沒必要回答,他也是住戶,為什麼不能走自己大樓的地下室?」
我試著解釋給鄰居聽。我可以感覺到那一觸即發的可能危險。比如當下如果他繼續逼問我弟,那我弟會怎樣?或對方會怎樣?還好後來事情往好的方向走,大樓管理員是一個想要試著了解我弟的叔叔,他對鄰居說我弟有自閉,「他高功能自閉。」「自閉症會這樣嗎?自閉症會很兇的看人?」「他亞斯啦!」
管理員試著用名詞來解釋我弟的狀況。我不喜歡簡單的被貼標籤,但在那個鄰居身上似乎有用。那個鄰居在知道了「原因」之後彷彿稍稍鬆下來,似乎貼了標籤後他就能理解我弟。「那他有沒有去治療?你們做家人的有沒有帶他去治療?」
這問題的問法令人不舒服,也很難回答。我吸一口氣,試著從另一個方向說給鄰居聽。我簡單說了滌的狀況,沒辦法說得很詳細,只能先概略的說,把重點擺在──
「他挑少人的地方走,就是想要避開人群──這樣的行為其實不會影響到他人──但別人不了解的話可能會害怕,所以我也才想要說弟弟的狀況給你聽。」我說,「如果有像你們這種『理性』的人願意多一點了解,如果社區有人看到我弟那樣覺得奇怪,你就可以幫忙講給他聽,那我弟就不會是問題。」
我故意把他大姊拉成像是一夥,說她是理性的人。大姊看起來也比之前緩和。雖然,她對我弟的理解仍舊是標籤的理解。這談起來很複雜,但至少跨出第一步,至少讓她不要怕,讓她不要以為我弟有敵意。
但我又可以想像,如果有類似我弟這樣的人,如果他沒有有餘裕能夠理解他的家人,如果大樓管理員和社區的人都帶著敵意,那麼情況只會變糟。那麼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了什麼」,那像這樣的人,他屬於有完全責任能力的人嗎?他究竟可以為自己付上多少責任?該為自己付上多少責任?家人的責任呢?社區的責任呢?刺激他的人的責任呢?
黃律師談到刑法中的「謙抑思想」。因為刑法可以剝奪人的自由、財產,甚至剝奪人的生命(如果這個國家還沒廢死),所以它在下判斷的時候,必須「努力」瞭解被告在行為當下的方方面面,以期判決「罪」「責」「相當」。
可是到底什麼是「罪」「責」「相當」?這又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但至少我理清一點,刑法的設計不是用來還被害者「公道」的(這句話說出來可能會令許多人搖頭),它反而是在政府動用權力時,保護被告的權益,所以才會有無罪推定,才會有刑法第19條。
「可是,如果刑法不是用來還被害者公道,那被害者該怎麼辦?」最後黃律師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我已經寫得太多了,我本來要簡單寫,卻從昨天晚上寫到今天早上(請不要擔心我有睡覺),我要先休息了。
邊想邊寫,寫得很亂。對法律若有理解錯誤的部分,請指正。
2020年5月29日 星期五
2020年5月25日 星期一
奇怪的名字
奇怪本來沒有名字
他只是奇怪
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有的奇怪不說話
有的奇怪會大叫
有的奇怪喜歡動來動去
有的奇怪喜歡數數
有的奇怪長得特別高
有的奇怪特別聰明
有的奇怪比較慢
奇怪不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一點都不奇怪
可是一旦跟別人在一起
奇怪就變得很奇怪了
人們不知道該怎麼跟奇怪相處
人們說
我們來給奇怪一個名字吧
給一個名字
再給個定義
「那種奇怪的人
就叫做XXX、OOO、XXXXOOO」
「它就是因為什麼什麼,怎樣怎樣
所以很奇怪喔」
「像那種奇怪的人,
就應該這樣這樣,那樣那樣」
人們給了奇怪一個奇怪的名字
彷彿給了名字之後
自己就知道該怎麼跟奇怪相處
奇怪得到奇怪的名字
他還是跟原來一樣
人們叫著奇怪的名字
但他們還是不會跟奇怪相處
他只是奇怪
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有的奇怪不說話
有的奇怪會大叫
有的奇怪喜歡動來動去
有的奇怪喜歡數數
有的奇怪長得特別高
有的奇怪特別聰明
有的奇怪比較慢
奇怪不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一點都不奇怪
可是一旦跟別人在一起
奇怪就變得很奇怪了
人們不知道該怎麼跟奇怪相處
人們說
我們來給奇怪一個名字吧
給一個名字
再給個定義
「那種奇怪的人
就叫做XXX、OOO、XXXXOOO」
「它就是因為什麼什麼,怎樣怎樣
所以很奇怪喔」
「像那種奇怪的人,
就應該這樣這樣,那樣那樣」
人們給了奇怪一個奇怪的名字
彷彿給了名字之後
自己就知道該怎麼跟奇怪相處
奇怪得到奇怪的名字
他還是跟原來一樣
人們叫著奇怪的名字
但他們還是不會跟奇怪相處
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
寫到最後發現原來我適合做教育,但做教育不適合我
中自學生的課程到一段落。亞問我,有什麼感覺。我一時說不出來,我說,很複雜。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很複雜,甚至複雜到想哭。那個想哭的感覺是什麼?竟然說不出來。亞和其他一些家長一直說我很厲害,可以跟這些自學生混。其實我覺得自己真的不厲害。不是客套。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好多有意思的東西,但同時我又覺得很累。我覺得很累,但如果他們表現出有那麼一點想要試試看,我就還是會繼續做。這代表這件事對我有意義?當然,我幾乎不會勉強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所以如果同理在他們身上,雖然他們覺得好像莫名其妙地完成了一件事,不是全主動但也沒有不要,這件事應該也是在他們身上發生意義,這個我知道。但我不清楚他們處在這件事中的感覺,但我真的不清楚嗎?其實我知道一些。
我想那個很大的落差感可能是,我在想那個失落的感覺。其實在非全主動的情況下,他們已經很願意去試跟做了,這個我可以感覺到。所以現在我才發現,原來我期待得更多,我希望他們每個人都跟我一樣全心投入,但是怎麼可能?「心」這種東西沒有辦法去要求。所以我一邊跟自己說要鬆,我的心要鬆一點,我不能拿自己的標準去要求他們。我不是完全不能鬆,當我鬆的時候我也能看到他們的好與特質,而且真心覺得他們都很棒。
但另一邊我又可以感覺到自己在丟太多東西進去之後的失落,可是那是因為我自己丟太多,我不能怪別人。
我真的不適合做教育。我會把自己掏空。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很複雜,甚至複雜到想哭。那個想哭的感覺是什麼?竟然說不出來。亞和其他一些家長一直說我很厲害,可以跟這些自學生混。其實我覺得自己真的不厲害。不是客套。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好多有意思的東西,但同時我又覺得很累。我覺得很累,但如果他們表現出有那麼一點想要試試看,我就還是會繼續做。這代表這件事對我有意義?當然,我幾乎不會勉強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所以如果同理在他們身上,雖然他們覺得好像莫名其妙地完成了一件事,不是全主動但也沒有不要,這件事應該也是在他們身上發生意義,這個我知道。但我不清楚他們處在這件事中的感覺,但我真的不清楚嗎?其實我知道一些。
我想那個很大的落差感可能是,我在想那個失落的感覺。其實在非全主動的情況下,他們已經很願意去試跟做了,這個我可以感覺到。所以現在我才發現,原來我期待得更多,我希望他們每個人都跟我一樣全心投入,但是怎麼可能?「心」這種東西沒有辦法去要求。所以我一邊跟自己說要鬆,我的心要鬆一點,我不能拿自己的標準去要求他們。我不是完全不能鬆,當我鬆的時候我也能看到他們的好與特質,而且真心覺得他們都很棒。
但另一邊我又可以感覺到自己在丟太多東西進去之後的失落,可是那是因為我自己丟太多,我不能怪別人。
我真的不適合做教育。我會把自己掏空。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病症的對號入座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人,那麼你「不正常」他們就無法接受。但如果你的「不正常」有個「名字」,他就可以把你對號入座,這樣他就能理解,原來你就是因為「生病」,所以這麼「奇怪」。
然後他就比較可以接受你的「不正常」,但不是真正的「接受」。
「生病了就該看醫生、該治療、該變成『正常』。」
如果你被認為正常,但有不正常的行為,「那你就該透過自己的力量導正自己。」
如果你被認為不正常,那有不正常的行為就很正常,「那你就該透過外在的力量導正自己。」
不管你正常與否,只要你的行為不正常你就該被導正。這個社會究竟能不能真正的接受不正常?這個問題很爛,因為社會由各式各樣的人組成,它不是「一種人」,它不是由同一種人所組成的社會。所以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的接受?有多少人是試著接受?有多少人假裝接受?有多少人不得不接受?有多少人無法接受?
「接受」是什麼?什麼叫做接受?
我的意思是要大家接受全部嗎?不是,也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在想,到底什麼叫做接受?
然後他就比較可以接受你的「不正常」,但不是真正的「接受」。
「生病了就該看醫生、該治療、該變成『正常』。」
如果你被認為正常,但有不正常的行為,「那你就該透過自己的力量導正自己。」
如果你被認為不正常,那有不正常的行為就很正常,「那你就該透過外在的力量導正自己。」
不管你正常與否,只要你的行為不正常你就該被導正。這個社會究竟能不能真正的接受不正常?這個問題很爛,因為社會由各式各樣的人組成,它不是「一種人」,它不是由同一種人所組成的社會。所以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的接受?有多少人是試著接受?有多少人假裝接受?有多少人不得不接受?有多少人無法接受?
「接受」是什麼?什麼叫做接受?
我的意思是要大家接受全部嗎?不是,也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在想,到底什麼叫做接受?
病症的對號入座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人,那麼你「不正常」他們就無法接受。但如果你的「不正常」有個「名字」,他就可以把你對號入座,這樣他就能理解,原來你就是因為「生病」,所以這麼「奇怪」。
然後他就比較可以接受你的「不正常」,但不是真正的「接受」。
「生病了就該看醫生、該治療、該變成『正常』。」
如果你被認為正常,但有不正常的行為,「那你就該透過自己的力量導正自己。」
如果你被認為不正常,那有不正常的行為就很正常,「那你就該透過外在的力量導正自己。」
不管你正常與否,只要你的行為不正常你就該被導正。這個社會究竟能不能真正的接受不正常?這個問題很爛,因為社會由各式各樣的人組成,它不是「一種人」,它不是由同一種人所組成的社會。所以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的接受?有多少人是試著接受?有多少人假裝接受?有多少人不得不接受?有多少人無法接受?
「接受」是什麼?什麼叫做接受?
我的意思是要大家接受全部嗎?不是,也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在想,到底什麼叫做接受?
2020年5月16日 星期六
人的時間
我聽著風扇在轉
我的腦袋在轉
我滑著螢幕
一個字都沒有出來
我想著我在浪費時間
可時間要怎麼浪費
時間要怎麼抓住
人的時間不是貓的時間
不是水的時間
不是嬰兒的時間
人的時間不見
時間不會不見
人的時間
不是時間的時間
我的腦袋在轉
我滑著螢幕
一個字都沒有出來
我想著我在浪費時間
可時間要怎麼浪費
時間要怎麼抓住
人的時間不是貓的時間
不是水的時間
不是嬰兒的時間
人的時間不見
時間不會不見
人的時間
不是時間的時間
ㄒㄧㄚˋㄒㄧㄚˋ來了?
下下來了
雨下下來了
靈感下下來了
還有什麼下下來?
貓下下來了
□□下下來了
那有上上來嗎?
上上來了
火上上來了
那有上下來嗎?
這個課上下來
真是超燒腦的
下下來了
老斌說
蛤?ㄒㄧㄚˋㄒㄧㄚˋ來了?
雨下下來了
靈感下下來了
還有什麼下下來?
貓下下來了
□□下下來了
那有上上來嗎?
上上來了
火上上來了
那有上下來嗎?
這個課上下來
真是超燒腦的
下下來了
老斌說
蛤?ㄒㄧㄚˋㄒㄧㄚˋ來了?
2020年5月15日 星期五
地下鐵事件──關於「對面」與「理解」
《地下鐵事件》讀了兩個月,今天在村上春樹撰寫的後記中結束。老實說,後半段越讀越快,雖然知道這些讀到後來感覺「類似」的故事,明明是「一個」「一個」「不同的人」的故事,他們都有各自的生活與人生,只是剛好在1995年3月20日的早晨,遇到了沙林毒氣;這明明是每個不同的人的切身經驗,但當這一個一個故事積累起來,卻免不了感覺重複。
我想起有朋友說讀這本書感到無聊,我是不會感覺無聊,但卻也察覺到自己在剛開始讀前半段時,可以一篇一篇細讀,慢慢感覺每個人生的「差異」,但讀到後來,我感覺到的卻是每個人生的「相似」。我想起前陣子有朋友在臉書上po的北野武說的一句話:「人命並不是死了兩萬人這樣一件事。與此相反,它代表的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北野武說的當然沒錯,這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但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人感覺到的──卻都是「死了兩萬人」這樣的感覺比較多。這很無奈,雖然明明知道是「一個」「一個」的人。
◆
「看來皈依奧姆真理教的人們,似乎很多是為了獲得麻原所授與的『自律性運力流程』,而將所謂自我這貴重的個人資產,連同鑰匙一起託付給麻原彰晃這個『精神銀行』的保險箱。忠實的信徒們主動捨棄自由、捨棄財產、捨棄家庭、捨棄世俗的價值判基準。如果是正常的市民的話一定會訝異地說『怎麼這麼傻』吧。但相對的,對教徒來說那是非常舒服的事。因為一旦把自己交給誰之後,就不必自己一一去辛苦思考,也不必控制自我了。」
──《地下鐵事件》
讀到這段時,有些人一定覺得──那些人不就是「逃避自由」嗎?把自己的自由交給他人,只要聽從信仰領袖的命令就好。但那些人一開始其實是想要獲得「被社會奪走的自由」,他們感覺到工作不自由、人際關係不自由、居住不自由,他們可能感覺,無法好好的做自己。正常大眾可能覺得,「你們把自己交給麻原彰晃,沒有了自我意識,這樣算是什麼自由?」但是,被歸類在「所謂」正常人的這邊的人們,就真的擁有自由嗎?
讀地下鐵時,我感覺到一種奇妙的氛圍──那樣多那樣多的人,每天早上搭同一班車,忍受著擁擠的車廂與長時間的通勤,一邊抱怨,卻也年復一年;有的人在察覺身體不舒服後(那時還不曉得是因為沙林毒氣的關係),第一個反應卻是──那上班該怎麼辦?或是不管再怎麼不舒服,只要身體還可以爬到公司,也要努力的爬到公司。在社會價值觀看來是一種「負責」的行為,但仔細想來卻好像違背自由。當然如果訪問他們,「你覺得自己自由嗎?」他們可能不會說自己不自由,但現實上卻有許多「不得不」──因為應該沒有人喜歡天天這樣擠地下鐵吧?怎麼想都不覺得是因為喜歡所以做這樣的選擇。擠地下鐵絕對不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而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
村上在後記中寫著:
「你有沒有對誰(或什麼)交出自我的一部份,而接受作為代價的『故事』呢?我們是否對某種制度=體系,交出人格的一部份讓人代管呢?如果是的話,那制度是否有一天會向你要求某種『瘋狂』呢?」
村上試圖抽出看似不同的兩邊的人,其中的同質性。當然他也一再強調──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會變成麻原彰晃(或他的信徒)。他想說的是如果我們習慣一刀切開兩個世界,以為邪惡就是邪惡,正義就是正義,那麼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這個事件能帶給我們的意義。
我說的意義(以下是我說的,不是村上),不是那種我們要從慘痛事件中學到什麼教訓的那種意義。但這個有點難說清楚。我說的意義有點接近,因為你嘗試去理解對面的人,因為這樣的連結,或許「有機會」讓那種難以挽回的事情,發生的少一點。
最近常在講什麼「對面」、什麼「理解」,講到自己都覺得有點煩了。但是還是忍不住一直講。
我想起有朋友說讀這本書感到無聊,我是不會感覺無聊,但卻也察覺到自己在剛開始讀前半段時,可以一篇一篇細讀,慢慢感覺每個人生的「差異」,但讀到後來,我感覺到的卻是每個人生的「相似」。我想起前陣子有朋友在臉書上po的北野武說的一句話:「人命並不是死了兩萬人這樣一件事。與此相反,它代表的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北野武說的當然沒錯,這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但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人感覺到的──卻都是「死了兩萬人」這樣的感覺比較多。這很無奈,雖然明明知道是「一個」「一個」的人。
◆
「看來皈依奧姆真理教的人們,似乎很多是為了獲得麻原所授與的『自律性運力流程』,而將所謂自我這貴重的個人資產,連同鑰匙一起託付給麻原彰晃這個『精神銀行』的保險箱。忠實的信徒們主動捨棄自由、捨棄財產、捨棄家庭、捨棄世俗的價值判基準。如果是正常的市民的話一定會訝異地說『怎麼這麼傻』吧。但相對的,對教徒來說那是非常舒服的事。因為一旦把自己交給誰之後,就不必自己一一去辛苦思考,也不必控制自我了。」
──《地下鐵事件》
讀到這段時,有些人一定覺得──那些人不就是「逃避自由」嗎?把自己的自由交給他人,只要聽從信仰領袖的命令就好。但那些人一開始其實是想要獲得「被社會奪走的自由」,他們感覺到工作不自由、人際關係不自由、居住不自由,他們可能感覺,無法好好的做自己。正常大眾可能覺得,「你們把自己交給麻原彰晃,沒有了自我意識,這樣算是什麼自由?」但是,被歸類在「所謂」正常人的這邊的人們,就真的擁有自由嗎?
讀地下鐵時,我感覺到一種奇妙的氛圍──那樣多那樣多的人,每天早上搭同一班車,忍受著擁擠的車廂與長時間的通勤,一邊抱怨,卻也年復一年;有的人在察覺身體不舒服後(那時還不曉得是因為沙林毒氣的關係),第一個反應卻是──那上班該怎麼辦?或是不管再怎麼不舒服,只要身體還可以爬到公司,也要努力的爬到公司。在社會價值觀看來是一種「負責」的行為,但仔細想來卻好像違背自由。當然如果訪問他們,「你覺得自己自由嗎?」他們可能不會說自己不自由,但現實上卻有許多「不得不」──因為應該沒有人喜歡天天這樣擠地下鐵吧?怎麼想都不覺得是因為喜歡所以做這樣的選擇。擠地下鐵絕對不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而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
村上在後記中寫著:
「你有沒有對誰(或什麼)交出自我的一部份,而接受作為代價的『故事』呢?我們是否對某種制度=體系,交出人格的一部份讓人代管呢?如果是的話,那制度是否有一天會向你要求某種『瘋狂』呢?」
村上試圖抽出看似不同的兩邊的人,其中的同質性。當然他也一再強調──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會變成麻原彰晃(或他的信徒)。他想說的是如果我們習慣一刀切開兩個世界,以為邪惡就是邪惡,正義就是正義,那麼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這個事件能帶給我們的意義。
我說的意義(以下是我說的,不是村上),不是那種我們要從慘痛事件中學到什麼教訓的那種意義。但這個有點難說清楚。我說的意義有點接近,因為你嘗試去理解對面的人,因為這樣的連結,或許「有機會」讓那種難以挽回的事情,發生的少一點。
最近常在講什麼「對面」、什麼「理解」,講到自己都覺得有點煩了。但是還是忍不住一直講。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書寫的「實驗」性質?
那天跟隸亞聊了一個多小時。沒有見過面的兩個人,講電話(FB語音)一個多小時。我講電話會緊張,但「討論事情」不會;就像要去人很多的社交場合會緊張,但如果進入自己感興趣的主題深入的聊,就不會。有時還會不小心變得話太多。訪談(聊天)結束後我說,這篇稿子可能會很難寫吼?因為我們講了超多但你的篇幅應該有限。
那天我們聊到《滌》在書寫上的「實驗」性質。我問他什麼是實驗性質?他說因為很少看到有人這樣寫,這種把書寫內容給書寫對象看,然後再把書寫對象的回應寫進去的寫法。我後來又把這個問題想了一下,我想,我不是想著要實驗一種新的寫法所以這樣去寫,而是這種來來回回的對話,是我長期以來一直很想做的事。
我一直很希望能夠透過書寫去「對話」,讓不同立場不同價值觀的人,有機會去接近跟自己不同的人。但我發現這很難。每天在臉書上,總是會看到許多人說話,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不對嗎?當然沒有不對,甚至很應該,因為我們都有自己站著的那個地方,我們一定有所立場。但是有所立場,就有沒機會了解跟自己不同的人的想法嗎?
每個站在自己立場說話的人,說話的時候希望能夠改變對方,改變那個跟自己不一樣的人──「他們為什麼可以那樣生活?他們怎麼可以做那樣的事?他們怎麼可以那樣主張?」我們氣憤,想要改變那些不對的人(或是也沒有想要改變,只是想要罵)。但人是這樣的,一旦被罵就會開始武裝,然後他可能也覺得你很奇怪啊,「你為什麼會那樣想?你為什麼會那樣做?」雙方沒有交集,也不想要去接近對方。
可是,不想去了解不行嗎?我就是很生氣、無法接受啊!難道要我打開心胸、假裝可以接納對方嗎?當然也不是。
還不想對話的時候,就不要勉強,只要去感覺自己的不想要或想要。是「想要」但還沒有辦法?還是真的「不想要」?不想對話就很難對話,只是想要改變對方就很難對話。對話是「想要接近」,兩邊都一樣。
我從前有時會陷入沮喪,特別是與議題有關的書寫,我常覺得自己講的那些,好像都沒有用。因為跟我想法一樣的人,本來就跟我一樣;而跟我想法不同的人,卻看不見他們移動。我在想為什麼?我後來想,想我覺得他們不了解我們,但我們其實也不了解對方?我如果沒有想要去了解對方,對方又怎麼會想要了解我?
所以在寫滌的時候,在跟滌、跟爸媽說話的時候,我努力把我自己寫出來,把自己對他們的觀察和感覺寫出來。以往的書寫,可能到「寫出來」就停了,但我把我寫出來的東西給他們看;剛開始給他們看的時候會很ㄔㄨㄚˋ,他們可能也會不舒服,但慢慢兩邊都接受了這樣的方式。但有時這種互動也是因人而異,目前在三個家人身上,我發現因為這樣的互動而變化最多的是媽媽。媽媽從前許多事經常不說,現在她會努力說。(啊嚴格說起來變化的還有我自己,我也是移動的那方)
而這樣的方式是不是就真的「有用」?是不是對「所有人」都有用?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個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親疏遠近,不一定剛好有機會建立起這樣的連結。
我現在回想從前的「對話」經驗。我從前是超級不會對話的,有什麼什麼情緒,就把自己關在盒子裡,關在黑盒子裡。但我也不會去苛責從前的自己,去苛責自己不會說。從前的我就是那樣啊,那就是從前的我。
https://ent.ltn.com.tw/news/paper/1371719
那天我們聊到《滌》在書寫上的「實驗」性質。我問他什麼是實驗性質?他說因為很少看到有人這樣寫,這種把書寫內容給書寫對象看,然後再把書寫對象的回應寫進去的寫法。我後來又把這個問題想了一下,我想,我不是想著要實驗一種新的寫法所以這樣去寫,而是這種來來回回的對話,是我長期以來一直很想做的事。
我一直很希望能夠透過書寫去「對話」,讓不同立場不同價值觀的人,有機會去接近跟自己不同的人。但我發現這很難。每天在臉書上,總是會看到許多人說話,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不對嗎?當然沒有不對,甚至很應該,因為我們都有自己站著的那個地方,我們一定有所立場。但是有所立場,就有沒機會了解跟自己不同的人的想法嗎?
每個站在自己立場說話的人,說話的時候希望能夠改變對方,改變那個跟自己不一樣的人──「他們為什麼可以那樣生活?他們怎麼可以做那樣的事?他們怎麼可以那樣主張?」我們氣憤,想要改變那些不對的人(或是也沒有想要改變,只是想要罵)。但人是這樣的,一旦被罵就會開始武裝,然後他可能也覺得你很奇怪啊,「你為什麼會那樣想?你為什麼會那樣做?」雙方沒有交集,也不想要去接近對方。
可是,不想去了解不行嗎?我就是很生氣、無法接受啊!難道要我打開心胸、假裝可以接納對方嗎?當然也不是。
還不想對話的時候,就不要勉強,只要去感覺自己的不想要或想要。是「想要」但還沒有辦法?還是真的「不想要」?不想對話就很難對話,只是想要改變對方就很難對話。對話是「想要接近」,兩邊都一樣。
我從前有時會陷入沮喪,特別是與議題有關的書寫,我常覺得自己講的那些,好像都沒有用。因為跟我想法一樣的人,本來就跟我一樣;而跟我想法不同的人,卻看不見他們移動。我在想為什麼?我後來想,想我覺得他們不了解我們,但我們其實也不了解對方?我如果沒有想要去了解對方,對方又怎麼會想要了解我?
所以在寫滌的時候,在跟滌、跟爸媽說話的時候,我努力把我自己寫出來,把自己對他們的觀察和感覺寫出來。以往的書寫,可能到「寫出來」就停了,但我把我寫出來的東西給他們看;剛開始給他們看的時候會很ㄔㄨㄚˋ,他們可能也會不舒服,但慢慢兩邊都接受了這樣的方式。但有時這種互動也是因人而異,目前在三個家人身上,我發現因為這樣的互動而變化最多的是媽媽。媽媽從前許多事經常不說,現在她會努力說。(啊嚴格說起來變化的還有我自己,我也是移動的那方)
而這樣的方式是不是就真的「有用」?是不是對「所有人」都有用?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個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親疏遠近,不一定剛好有機會建立起這樣的連結。
我現在回想從前的「對話」經驗。我從前是超級不會對話的,有什麼什麼情緒,就把自己關在盒子裡,關在黑盒子裡。但我也不會去苛責從前的自己,去苛責自己不會說。從前的我就是那樣啊,那就是從前的我。
https://ent.ltn.com.tw/news/paper/1371719
2020年5月11日 星期一
沒關係你有好多個瞬間
跟T聊天,T是個很愛寫東西的自學生。
他剛給我好多首他寫的餅乾詩。
我說,那麼會寫,
以後叫你餅乾詩詩人好了。
T說:
「你這樣說,讓我一瞬間想不出來。」
我說:
「沒關係你只有一瞬間想不出來,你還有好多個瞬間。」
他剛給我好多首他寫的餅乾詩。
我說,那麼會寫,
以後叫你餅乾詩詩人好了。
T說:
「你這樣說,讓我一瞬間想不出來。」
我說:
「沒關係你只有一瞬間想不出來,你還有好多個瞬間。」
2020年5月10日 星期日
有孩子的我媽與沒有孩子的我
〈有孩子的我媽與沒有孩子的我〉
人生嘛
要嘛就是有孩子要嘛就是沒有孩子
有孩子的我媽對著沒有孩子的我說
你沒有孩子
你不懂
沒有孩子的我對著有孩子的我媽說
我沒有孩子
我確實不懂
我媽已經是我媽了
無法變成一個沒有孩子的媽媽
而我已經是我了
我沒有孩子
我不是媽媽
我是孩子
我不懂媽媽但是我懂我媽
──2014.01.30
這首詩是六年前寫的。今天重讀這首詩,讀到最後,我想著,我真的懂我媽嗎?
去年九月,再次跟媽媽提起想要出版《滌》的事。那時年金計畫已經交稿了,我媽以為沒事了,所以我跟她提的時候,我媽一臉不可思議地說,「你還沒有放棄啊!」
然後當天,我們有了爭執。我平常很少生氣,但那天卻很激動。激動是因為我媽的這句話:「這個東西對其他人來說,有什麼重要!有沒有出版,有那麼重要嗎?」
「有什麼重要!有什麼重要?」我當下突然覺得,過去一年寫的東西,我跟她之間曾經有過的對話,有什麼意義?說了那麼多,到底有什麼意義?我覺得不被理解,我沒有要她一定要答應,我可以理解她不願意的原因。我可以理解她不願意,她還無法,但是她怎麼可以直接否定我的想法?我就是覺得重要,才會一次又一次徵詢她的意願。現在她丟一句「有那麼重要嗎?」我到底要怎麼反應?
回台東後,難過了幾天,後來我想起媽媽說的一句話:「你覺得我不理解你,可是妳也不理解我啊!兩個人彼此都不理解啊!」我想著這句話,我突然明白一件事──人與人之間本來就不可能真正的互相理解,所以重點不是能不能完全的理解,而是「有沒有」那個「想要」去理解對方的心。
於是我寫了信給媽媽。我跟媽媽說,「我說我覺得自己不被你理解,可是我再仔細想,在過程中其實我有感覺到──你有『想要』理解我。不然你也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去讀我寫的東西,去了解我覺得在意的事情。」
過了一個月再回家的時候,媽媽試著想要解釋她之前說的那句話。
媽媽說,她說的對其他人來說有什麼重要的意思是,這是我們家的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可是對其他人來說,真的有那麼重要嗎?這是她試著想要說明的第一件事。然後第二件事,是我想都沒想過的。
「我那時候想,有沒有出版,真的有那麼重要嗎?這件事真的有那麼嚴重嗎?」媽媽說,我現在這樣講,你可能不一定會懂,我那時候想,我年輕時候遭遇的那些事,完全沒有錢,下個月的生活費,不知道在哪裡,「然後我在想,只是有沒有出版,這件事真的有那麼嚴重嗎?對生活會造成影響嗎?」聽到這裡,我知道媽媽在感覺出版這件事對我的意義。
「然後我又想,出版這件事,真的有那麼嚴重嗎?如果跟我以前發生的那些事比,好像也沒那麼嚴重吧……」聽到這裡,我發現媽媽轉了個彎,「如果真的出版了,我雖然會有一點點擔心,但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只是女兒出版了一本書而已……」
聽到這裡我突然覺得很不可思議。我突然覺得我真的不了解我媽是怎麼想。為什麼身為母親可以做到這樣?現在媽媽說的意思是……沒有那麼嚴重,所以她可以接受……
昨天收到朋友的訊息,說他讀完後印象最深刻的是:「滌媽心理素質很強」。我看了之後說,「哈哈哈,好,我會跟她說。」
我也覺得媽媽的心理素質,真是超強大的。
人生嘛
要嘛就是有孩子要嘛就是沒有孩子
有孩子的我媽對著沒有孩子的我說
你沒有孩子
你不懂
沒有孩子的我對著有孩子的我媽說
我沒有孩子
我確實不懂
我媽已經是我媽了
無法變成一個沒有孩子的媽媽
而我已經是我了
我沒有孩子
我不是媽媽
我是孩子
我不懂媽媽但是我懂我媽
──2014.01.30
這首詩是六年前寫的。今天重讀這首詩,讀到最後,我想著,我真的懂我媽嗎?
去年九月,再次跟媽媽提起想要出版《滌》的事。那時年金計畫已經交稿了,我媽以為沒事了,所以我跟她提的時候,我媽一臉不可思議地說,「你還沒有放棄啊!」
然後當天,我們有了爭執。我平常很少生氣,但那天卻很激動。激動是因為我媽的這句話:「這個東西對其他人來說,有什麼重要!有沒有出版,有那麼重要嗎?」
「有什麼重要!有什麼重要?」我當下突然覺得,過去一年寫的東西,我跟她之間曾經有過的對話,有什麼意義?說了那麼多,到底有什麼意義?我覺得不被理解,我沒有要她一定要答應,我可以理解她不願意的原因。我可以理解她不願意,她還無法,但是她怎麼可以直接否定我的想法?我就是覺得重要,才會一次又一次徵詢她的意願。現在她丟一句「有那麼重要嗎?」我到底要怎麼反應?
回台東後,難過了幾天,後來我想起媽媽說的一句話:「你覺得我不理解你,可是妳也不理解我啊!兩個人彼此都不理解啊!」我想著這句話,我突然明白一件事──人與人之間本來就不可能真正的互相理解,所以重點不是能不能完全的理解,而是「有沒有」那個「想要」去理解對方的心。
於是我寫了信給媽媽。我跟媽媽說,「我說我覺得自己不被你理解,可是我再仔細想,在過程中其實我有感覺到──你有『想要』理解我。不然你也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去讀我寫的東西,去了解我覺得在意的事情。」
過了一個月再回家的時候,媽媽試著想要解釋她之前說的那句話。
媽媽說,她說的對其他人來說有什麼重要的意思是,這是我們家的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可是對其他人來說,真的有那麼重要嗎?這是她試著想要說明的第一件事。然後第二件事,是我想都沒想過的。
「我那時候想,有沒有出版,真的有那麼重要嗎?這件事真的有那麼嚴重嗎?」媽媽說,我現在這樣講,你可能不一定會懂,我那時候想,我年輕時候遭遇的那些事,完全沒有錢,下個月的生活費,不知道在哪裡,「然後我在想,只是有沒有出版,這件事真的有那麼嚴重嗎?對生活會造成影響嗎?」聽到這裡,我知道媽媽在感覺出版這件事對我的意義。
「然後我又想,出版這件事,真的有那麼嚴重嗎?如果跟我以前發生的那些事比,好像也沒那麼嚴重吧……」聽到這裡,我發現媽媽轉了個彎,「如果真的出版了,我雖然會有一點點擔心,但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只是女兒出版了一本書而已……」
聽到這裡我突然覺得很不可思議。我突然覺得我真的不了解我媽是怎麼想。為什麼身為母親可以做到這樣?現在媽媽說的意思是……沒有那麼嚴重,所以她可以接受……
昨天收到朋友的訊息,說他讀完後印象最深刻的是:「滌媽心理素質很強」。我看了之後說,「哈哈哈,好,我會跟她說。」
我也覺得媽媽的心理素質,真是超強大的。
2020年5月9日 星期六
寫作的成本
昨天睡前,腦袋還繞著這個問題。
寫這種事與耕種這件事,某些層面真的很像。比如某些阿嬤種菜,菜是種來自己吃,也沒要賣。我們自己種的許多作物,香蕉、芭蕉、草莓,這個豆那個豆,也都沒在賣,就是自己吃或分著吃。有些作物的量太少,就算想賣也沒得賣;而有些是量多一點,但如果你去算那個時間成本,再把時間成本算成錢(按照所謂的市場價格算成錢),最後會發現價格會高到自己買不下手(或是有人會想要買那樣高價的東西嗎),索性就不想賣的事了,自己吃或分朋友吃,快樂一些。
當然不是說我們種的所有作物這樣。有時朋友問我們種什麼,我說,經濟作物是鳳梨。這麼說的意思是,這類作物是有規劃地去種,算了面積、算了產量、算了成本,最後得出一個可以賴以為生,我們又自覺「合理」的價格。「合理的」價格,這個我之前常常講,我跟老斌常常討論。但現在我想談的不是合理價格,而是那些我們沒有打算做為經濟作物,但確實也付出心力的農作,要怎麼算那個成本?
我發現這個問題的背後,有一種所有東西都可以、也該轉換成「錢」的預設。你花了多少時間、用了多少心力,這些都是成本。可是,我們沒有把它換成錢,我們就虧到了嗎?究竟是沒有換成錢是虧到?還是換成錢才真的是虧到?
傷腦筋,講著講著好像有一點點散開出去。我想說的是,我們做某些事情,如果沒有換成錢,就等於白做嗎?哎呀,越講越不清楚,好像我很不在意錢的樣子,也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當然需要錢,但有些東西不一定可以等值的換成錢。
像是教學的成本要怎麼算?教學的成本沒辦法算,你沒辦法算備課的心力,你腦袋的思考,你的情緒。你能算的只有鐘點,當然鐘點費有高有低,但能算的也只有鐘點。
那麼寫作的成本呢?你現在寫出來的東西,是累積在你經驗過的生活、腦袋的運作,以及從前寫過每一個字,還有情緒勞動。這些要怎麼算?沒辦法算。能算的只有變成「商品」的部分。這裡的商品是中性詞,指能被定價的,被買賣的。最後能算的只有──訂閱金額、訂閱人數;或是一篇有稿費的文章,一個字多少錢;或是寫的字出成了書,每本書售出之後的版稅;而還不是出了就會有錢,而是要有人買才會有錢。
吃早餐時,我的腦袋還繞著這個問題。我問老斌:寫作的成本要怎麼算?老斌說,怎麼算?跟做人一樣,沒辦法算。
寫這種事與耕種這件事,某些層面真的很像。比如某些阿嬤種菜,菜是種來自己吃,也沒要賣。我們自己種的許多作物,香蕉、芭蕉、草莓,這個豆那個豆,也都沒在賣,就是自己吃或分著吃。有些作物的量太少,就算想賣也沒得賣;而有些是量多一點,但如果你去算那個時間成本,再把時間成本算成錢(按照所謂的市場價格算成錢),最後會發現價格會高到自己買不下手(或是有人會想要買那樣高價的東西嗎),索性就不想賣的事了,自己吃或分朋友吃,快樂一些。
當然不是說我們種的所有作物這樣。有時朋友問我們種什麼,我說,經濟作物是鳳梨。這麼說的意思是,這類作物是有規劃地去種,算了面積、算了產量、算了成本,最後得出一個可以賴以為生,我們又自覺「合理」的價格。「合理的」價格,這個我之前常常講,我跟老斌常常討論。但現在我想談的不是合理價格,而是那些我們沒有打算做為經濟作物,但確實也付出心力的農作,要怎麼算那個成本?
我發現這個問題的背後,有一種所有東西都可以、也該轉換成「錢」的預設。你花了多少時間、用了多少心力,這些都是成本。可是,我們沒有把它換成錢,我們就虧到了嗎?究竟是沒有換成錢是虧到?還是換成錢才真的是虧到?
傷腦筋,講著講著好像有一點點散開出去。我想說的是,我們做某些事情,如果沒有換成錢,就等於白做嗎?哎呀,越講越不清楚,好像我很不在意錢的樣子,也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當然需要錢,但有些東西不一定可以等值的換成錢。
像是教學的成本要怎麼算?教學的成本沒辦法算,你沒辦法算備課的心力,你腦袋的思考,你的情緒。你能算的只有鐘點,當然鐘點費有高有低,但能算的也只有鐘點。
那麼寫作的成本呢?你現在寫出來的東西,是累積在你經驗過的生活、腦袋的運作,以及從前寫過每一個字,還有情緒勞動。這些要怎麼算?沒辦法算。能算的只有變成「商品」的部分。這裡的商品是中性詞,指能被定價的,被買賣的。最後能算的只有──訂閱金額、訂閱人數;或是一篇有稿費的文章,一個字多少錢;或是寫的字出成了書,每本書售出之後的版稅;而還不是出了就會有錢,而是要有人買才會有錢。
吃早餐時,我的腦袋還繞著這個問題。我問老斌:寫作的成本要怎麼算?老斌說,怎麼算?跟做人一樣,沒辦法算。
2020年5月8日 星期五
寫書是一回事,賣書是另一回事。
寫書是一回事,賣書是另一回事。
就像務農,種是一回事,賣又是另一回事。
先把寫和種的事情,做好,問心無愧,這是基本。再來,東西生出來就是要賣,不管是寫還是種,不然再好的東西卻賣不出去,也是可惜。
那麼,要怎麼賣?你可以選擇要自己賣,或是交給別人賣。想要自己賣的人可以考量自己是否有管道,而更重要的是個性,「我自己做得來嗎?我做得了這些事嗎?」如果喜歡做,也做得來,就可以考慮自己出版或自己賣,這時當然相關的營收就是你個人可以決定,可以控制。
但如果你需要交給別人賣,那麼這時就是分工。找到你願意能夠信任,願意一起工作的人很重要。彼此互相理解很重要,你會很放心的把東西交給對方,對方也會很樂意讓東西有機會被需要的人看到。
然後實際面,究竟要怎麼讓可能有需要的人接觸到這個東西?可能是網路的曝光,可能是實體的平台,但這都要有人去接觸、去談。去談的人是誰?去接觸的人是誰?成本就在誰那一方。
然後出貨,出貨有包裝的成本、物流的成本。東西量大,就會有倉儲的成本。同樣,這些成本的壓力在哪一方,收入的比例分配也該那樣。
如果從頭到尾都是自己來,沒話說收入該是自己的。但如果不是,那麼該按分工和成本壓力來分配,我想是基本合理。這還沒有談到與自己合作的對方,所付出的心。心這東西就難計算了。
就像務農,種是一回事,賣又是另一回事。
先把寫和種的事情,做好,問心無愧,這是基本。再來,東西生出來就是要賣,不管是寫還是種,不然再好的東西卻賣不出去,也是可惜。
那麼,要怎麼賣?你可以選擇要自己賣,或是交給別人賣。想要自己賣的人可以考量自己是否有管道,而更重要的是個性,「我自己做得來嗎?我做得了這些事嗎?」如果喜歡做,也做得來,就可以考慮自己出版或自己賣,這時當然相關的營收就是你個人可以決定,可以控制。
但如果你需要交給別人賣,那麼這時就是分工。找到你願意能夠信任,願意一起工作的人很重要。彼此互相理解很重要,你會很放心的把東西交給對方,對方也會很樂意讓東西有機會被需要的人看到。
然後實際面,究竟要怎麼讓可能有需要的人接觸到這個東西?可能是網路的曝光,可能是實體的平台,但這都要有人去接觸、去談。去談的人是誰?去接觸的人是誰?成本就在誰那一方。
然後出貨,出貨有包裝的成本、物流的成本。東西量大,就會有倉儲的成本。同樣,這些成本的壓力在哪一方,收入的比例分配也該那樣。
如果從頭到尾都是自己來,沒話說收入該是自己的。但如果不是,那麼該按分工和成本壓力來分配,我想是基本合理。這還沒有談到與自己合作的對方,所付出的心。心這東西就難計算了。
2020年5月6日 星期三
有那一個所謂的分岔點嗎?
我這麼問的時候,彷彿眼前有個叉路。往右是一條路,往左是一條路。岔路一直都有,問的是:「走哪一條比較好?」可是有走哪條路就「比較好」這種答案嗎?岔路的下面,還有岔路,人生有數不盡的岔路。而這些岔路,又不像你玩紙上迷宮,你無法看見地圖的全貌(但有的地圖儘管看見全貌,你仍然不會走)。人生的岔路不是紙上迷宮,也沒有所謂的正確出口。
但是我們又必須要選,必須要走。
可是真的「必須」嗎?「必須」這個詞用得很硬,彷彿就是得要,有人推你。可是我們剛出生時,有那個「必須」嗎?我們只是活著。我們只是自然地活著,自然地呼吸,吃奶、大便。我們不是必須活著、必須呼吸、必須吃奶大便。雖然我們不呼吸不吃奶不大便就會死,但那不是我們的腦袋意識著自己必須。或許你會說這是身體有必須活下去的意識?那好吧,身體覺得自己要這樣運作才能活下去。但身體那時只想著要活下去。身體那時候開始「選」了嗎?我們開始「選」了嗎?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選的呢?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走這條路才好?走那條路不好?可是你又看不見前方的前方,你又怎麼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選」?什麼時候開始「必須」?一開始幾乎不是自己選的,從父母開始就不是自己選的,出生的方式也不是自己選,喝奶粉還是喝母乳也不是自己選。有些父母沒有「選」,他們只是照著自己父母的方式做。那這樣不是「選」嗎?他們還不是為自己的小孩做了一個決定?可是這樣是「選」嗎?在他們的眼前有選項嗎?
有的人眼前有選項,有些人沒有。沒有的人依舊要活下去,依舊要做許多決定。無法讓小孩去上學,或只好讓小孩去上學;無法自己帶小孩,或只好自己帶小孩。而眼前有選項的那些人,開始想著哪一個選擇「比較好」?哪一條路「比較好」?
走到了不只是父母幫你選,你也開始為自己選的,那個路口;你是怎麼選擇眼前的路?你是因為看見了某一條路比較好嗎?你的「好」跟你的父母一樣嗎?不一樣嗎?很早你就知道,你的好跟父母的好,不一樣。但更久之後你才知道,「我所做的選擇,不是因為預知了哪條路是好的。」
我永遠無法預知,我只能去選。我選並不是因為預知了好,我做不是因為「那樣比較好」。但我心中難道沒有好壞的判斷嗎?當然是有,當然會有。身而為人,我幾乎,已經無法不判斷了。我始終在判斷,但我又知道,我的好不是絕對,壞不是絕對。
我的好不是絕對,壞不是絕對,但我仍舊做出了選擇。我做了選擇,那麼,我篤定嗎?既然沒有絕對,那麼也沒有篤定。「你搬到鄉下生活,你篤定嗎?」我不知道未來好不好啊,但我現在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我一直都覺得很好。在不好的時候,我仍舊覺得很好。因為怎麼可能一直好下去呢?總是有不好的時候。可是什麼是不好?跌倒是不好嗎?痛是不好嗎?昨天我覺得身體很不舒服,不舒服不好嗎?當然我也不會說好。可是,不舒服不好嗎?不舒服代表你有感覺。生氣不好嗎?生氣代表你有感覺。
活著就是要「好」嗎?會不會就是那個要活得好的好,反而使得人們都活得不好了呢?人們以為,有一個所謂的分岔點,選錯的分岔點。「要是我當初……」因為走了這條岔路,所以遇到了下一個岔路,「如果選擇另一個岔路,就不會遇到那個後來讓我很慘的岔路……」
可是站在岔路上的你,不是你自己選的嗎?可是,真的是你自己選的嗎?有時我可以很確定,有時我無法確定。有時我認為掌握權在自己手上,有時又不那麼肯定。
──刊載於《幼獅文藝》第797期,2020年5月出版
但是我們又必須要選,必須要走。
可是真的「必須」嗎?「必須」這個詞用得很硬,彷彿就是得要,有人推你。可是我們剛出生時,有那個「必須」嗎?我們只是活著。我們只是自然地活著,自然地呼吸,吃奶、大便。我們不是必須活著、必須呼吸、必須吃奶大便。雖然我們不呼吸不吃奶不大便就會死,但那不是我們的腦袋意識著自己必須。或許你會說這是身體有必須活下去的意識?那好吧,身體覺得自己要這樣運作才能活下去。但身體那時只想著要活下去。身體那時候開始「選」了嗎?我們開始「選」了嗎?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選的呢?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走這條路才好?走那條路不好?可是你又看不見前方的前方,你又怎麼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選」?什麼時候開始「必須」?一開始幾乎不是自己選的,從父母開始就不是自己選的,出生的方式也不是自己選,喝奶粉還是喝母乳也不是自己選。有些父母沒有「選」,他們只是照著自己父母的方式做。那這樣不是「選」嗎?他們還不是為自己的小孩做了一個決定?可是這樣是「選」嗎?在他們的眼前有選項嗎?
有的人眼前有選項,有些人沒有。沒有的人依舊要活下去,依舊要做許多決定。無法讓小孩去上學,或只好讓小孩去上學;無法自己帶小孩,或只好自己帶小孩。而眼前有選項的那些人,開始想著哪一個選擇「比較好」?哪一條路「比較好」?
走到了不只是父母幫你選,你也開始為自己選的,那個路口;你是怎麼選擇眼前的路?你是因為看見了某一條路比較好嗎?你的「好」跟你的父母一樣嗎?不一樣嗎?很早你就知道,你的好跟父母的好,不一樣。但更久之後你才知道,「我所做的選擇,不是因為預知了哪條路是好的。」
我永遠無法預知,我只能去選。我選並不是因為預知了好,我做不是因為「那樣比較好」。但我心中難道沒有好壞的判斷嗎?當然是有,當然會有。身而為人,我幾乎,已經無法不判斷了。我始終在判斷,但我又知道,我的好不是絕對,壞不是絕對。
我的好不是絕對,壞不是絕對,但我仍舊做出了選擇。我做了選擇,那麼,我篤定嗎?既然沒有絕對,那麼也沒有篤定。「你搬到鄉下生活,你篤定嗎?」我不知道未來好不好啊,但我現在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我一直都覺得很好。在不好的時候,我仍舊覺得很好。因為怎麼可能一直好下去呢?總是有不好的時候。可是什麼是不好?跌倒是不好嗎?痛是不好嗎?昨天我覺得身體很不舒服,不舒服不好嗎?當然我也不會說好。可是,不舒服不好嗎?不舒服代表你有感覺。生氣不好嗎?生氣代表你有感覺。
活著就是要「好」嗎?會不會就是那個要活得好的好,反而使得人們都活得不好了呢?人們以為,有一個所謂的分岔點,選錯的分岔點。「要是我當初……」因為走了這條岔路,所以遇到了下一個岔路,「如果選擇另一個岔路,就不會遇到那個後來讓我很慘的岔路……」
可是站在岔路上的你,不是你自己選的嗎?可是,真的是你自己選的嗎?有時我可以很確定,有時我無法確定。有時我認為掌握權在自己手上,有時又不那麼肯定。
──刊載於《幼獅文藝》第797期,2020年5月出版
2020年5月5日 星期二
廖瞇你最喜歡什麼動物?
剛剛看完有話好說,心情很複雜。太複雜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說,先寫一段下午跟小克的對話。
「廖瞇你最喜歡什麼動物?」
「最喜歡的動物?」突然被問,我回答不出來。想了一下,我好像沒有什麼最喜歡的動物。很多動物我都喜歡,但沒有最喜歡。而說喜歡動物也怪怪的,怎樣叫做喜歡動物?我說我想不出來。
「我跟你說我最喜歡什麼動物,我最喜歡石虎,」小克說,「換你。」
我努力想了一下,然後說狗。
小克問為什麼是狗?
我說,因為目前跟我最好的動物是migu啊,所有的動物裡面我最喜歡migu,而migu剛好是狗。所以我最喜歡狗。
小克對這個答案算是滿意。接著她馬上問第二個問題──
「那全世界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最喜歡的東西?好像沒有最喜歡的東西吧?我說,我想不出來。小克一副我怎麼連自己最喜歡的東西都不知道的表情,看著我說:「我最喜歡娃娃。」
天啊,為什麼她的答案可以這樣斬釘截鐵不加思索,是所有的小孩都這樣嗎?她又繼續問,你最喜歡什麼啊?我腦袋閃過「人」、「人類」;但接著我又想,我不是說過自己最討厭人類嗎?但我剛剛腦袋閃過的答案真的是「人」。我正要開口回答的時候,小克說,「我知道了,你最喜歡的是老斌。」
她的答案讓我很想笑。我說我的答案是人啦,「老斌是人,所以也可以啦。」接著我說我最喜歡人,可是也最討厭人,「我有時候很喜歡人類,有時候很討厭人類。」
當我說我喜歡人類的時候,小克突然說,「我不喜歡人類。」
我很訝異她這麼小就不喜歡人類?我問她為什麼不喜歡?她說因為我到底是哪裡來的?這個世界是哪裡來的?為什麼人類會把這個世界弄成這個樣子?她一下子講了三個問題,但聽起來她的腦袋裡不只有三個問題,她說為什麼我想這麼多頭腦要爆炸了。
「為什麼人類會把這個世界弄成這個樣子……你的意思是人類把這個世界弄得很糟嗎?」我問小克。小克說對。
我說,我也覺得人類把這個世界弄得很糟,可是,你不覺得人類很會問問題很棒嗎?小克搖頭,說不覺得。
小克七歲半。
「廖瞇你最喜歡什麼動物?」
「最喜歡的動物?」突然被問,我回答不出來。想了一下,我好像沒有什麼最喜歡的動物。很多動物我都喜歡,但沒有最喜歡。而說喜歡動物也怪怪的,怎樣叫做喜歡動物?我說我想不出來。
「我跟你說我最喜歡什麼動物,我最喜歡石虎,」小克說,「換你。」
我努力想了一下,然後說狗。
小克問為什麼是狗?
我說,因為目前跟我最好的動物是migu啊,所有的動物裡面我最喜歡migu,而migu剛好是狗。所以我最喜歡狗。
小克對這個答案算是滿意。接著她馬上問第二個問題──
「那全世界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最喜歡的東西?好像沒有最喜歡的東西吧?我說,我想不出來。小克一副我怎麼連自己最喜歡的東西都不知道的表情,看著我說:「我最喜歡娃娃。」
天啊,為什麼她的答案可以這樣斬釘截鐵不加思索,是所有的小孩都這樣嗎?她又繼續問,你最喜歡什麼啊?我腦袋閃過「人」、「人類」;但接著我又想,我不是說過自己最討厭人類嗎?但我剛剛腦袋閃過的答案真的是「人」。我正要開口回答的時候,小克說,「我知道了,你最喜歡的是老斌。」
她的答案讓我很想笑。我說我的答案是人啦,「老斌是人,所以也可以啦。」接著我說我最喜歡人,可是也最討厭人,「我有時候很喜歡人類,有時候很討厭人類。」
當我說我喜歡人類的時候,小克突然說,「我不喜歡人類。」
我很訝異她這麼小就不喜歡人類?我問她為什麼不喜歡?她說因為我到底是哪裡來的?這個世界是哪裡來的?為什麼人類會把這個世界弄成這個樣子?她一下子講了三個問題,但聽起來她的腦袋裡不只有三個問題,她說為什麼我想這麼多頭腦要爆炸了。
「為什麼人類會把這個世界弄成這個樣子……你的意思是人類把這個世界弄得很糟嗎?」我問小克。小克說對。
我說,我也覺得人類把這個世界弄得很糟,可是,你不覺得人類很會問問題很棒嗎?小克搖頭,說不覺得。
小克七歲半。
2020年5月3日 星期日
回家,把書拿給滌
一樣,走進房間時,滌一樣被嚇到。「ㄛ……ㄛ……」他一樣發出受驚嚇的聲音。我直接說,我來聊天。滌瞥眼看我,然後點頭,好啊,來聊。
我走進房間,靜靜的把書擺在他的床上,那看來是目前唯一可以放書的地方。滌開始說話,似乎沒有看到我手中的書。這很神奇,以往他會注意對方每個細微的動作。滌開始說話,說我昨天給他的草莓,他說盒子打開,草莓的味道就衝出來。他又比較了一下市售草莓跟我給他的草莓的味道。說著說著,他停下來的那個時間空檔,我指指床上的書,我說,書出來了。
他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眼睛一亮,然後身體倒退。是真的身體倒退。他倒退一步,但眼睛仍然盯著擺在床上的書。這時我把書拿起來,遞給他,我又說了一次,書出來了。
他接過書,眼睛亮著。他說,我看到「滌」了。他指的是封面上那個滌,在黑底上金色的滌。「這個字寫得好ㄟ……」我沒想到滌馬上稱讚起這本書。滌拿著書,端詳了一會,還沒有翻開。他拿著書開始走來走去,口中唸著怎麼辦怎麼辦。他看起來有點不知所措。我問他,你是不是在找地方放?他點頭。但他房間的桌上有灰塵,他看來不知道該放在哪裡。
還沒給滌書之前,媽媽問我,你也會給滌一本嗎?我說對呀,當然。媽媽說,你書給他,他一定一下子就弄髒了,「他根本不會愛惜書。他都把我的書亂撕,做他的便條紙。」我說書我一定會給他,「給他就是他的書了,我就不去想書會怎樣。」
結果沒想到,滌現在竟然對該把書擺在哪裡,不知所措。滌討厭去接觸他人碰過的東西,看起來好像有潔癖,但其實不是。他的房間總是隨意丟著穿過的衣服。他不打掃房間。對他來說,那些灰塵那些「髒」,都是自然的。只要他人沒有碰過,那些髒,他都可以接受。
而現在,他突然在意起桌上的灰塵,桌上的水漬。他不曉得該把《滌》擺在哪裡。我看著他的舉動,所以他很在意這本書?我看著他不曉得該把書放哪的樣子。我拿出一張月曆紙,本來用來包書的月曆紙。我把紙鋪在桌上,接過他手中的書,「我鋪了一張紙,幫你把書放在紙上好嗎?」
◆
把書給滌的隔天早上,我從廁所出來,看到一個身影。那個身影看起來像是要閃進廚房,可是又定住,在那邊猶豫不決。那個身影當然是滌,滌在那邊猶豫不決。滌低頭喃喃自語,「要不要,要不要呢?」我察覺到他有話想說,而且是跟我說。我站著等他。
我等他,這次他抬頭正臉看我,「我在想要不要……」他開口,又停住,他指著櫥櫃上的檯燈,「你看,我連那個東西都找出來了……」
這是第二次,滌主動跟我說話。
把那個東西找出來了,意思是把檯燈找出來。如果他沒說,我也不曉得我們家有這盞檯燈。他指著檯燈,說房間光線太暗,看書要燈。所以他是想要告訴我他為了讀這本書,所以把檯燈找出來?他說檯燈被放在櫃子好多年,都是霉味,要先擺在客廳通風。他用手去摸脖子,說他已經很久沒有看書了,「我都看網路,我很久沒有看書了。」可是他很想看,很想看。
接著他問我現在要做什麼?有空講話嗎?我本來是要進媽房間幫她弄電腦,但我看滌很想說話的樣子,於是我說,一個小時。滌說好,一個小時。
開始說話後,滌說起盧郁佳。他說,我還沒看你的正文,雖然我之前看過電子檔,但你修改完稿的我還沒看,「我現在卡在盧郁佳。」滌說,「這個人真是個咖。」
滌說盧郁佳真是個咖的時候,我有點想笑,他竟然用「真是個咖」來形容。但滌的表情很認真。「盧郁佳是小姐嗎?」我知道滌問的是盧是男生還是女生,於是我回答,她是女生。接著又問我她幾歲,我說比我大幾歲吧。滌說你可以跟我說她是怎樣的人嗎?我很想知道寫這篇推薦序的人是怎樣的人。我說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樣的人,我只跟她通過幾次信,其他的就是網路上能找到的資訊,「我能找到的,並不比你更多。」我還沒有真的認識她。
滌說,「盧小姐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滌說他剛開始讀的時候,想說這個人這樣寫是不是在幹我?竟然說我是家裡的大魔王!「可是再仔細想,又覺得她沒說錯」。滌不服氣,卻又同意她。滌讀她的序,讀得非常細,幾乎是一字一句的讀,「她說得沒錯,我不是不會控制,我是控制得太多。」
在這之前,滌不認識盧郁佳,他很少讀與文學相關的作品或文章。然後他也因為盧郁佳的序,去查了「繭居族」這個名詞。
滌這一說,我才知道他沒聽過「繭居族」這個名詞。現在換我驚訝。
「你沒聽過繭居族?」
「對。沒聽過。我剛剛才去查。」
仔細想想,《滌》這本書的正文,似乎真的沒有出現過「繭居族」這個詞,可能是因為我一直避免直接使用它。但我沒想過滌沒聽過這個詞。
那天聊天,滌說著說著又說到別的地方去了,當下沒有機會針對他找到的資訊再多做了解。但當我知道原來滌沒聽過繭居族,我就很想知道那麼當他查到網路上的相關資訊後,他認同那些定義嗎?他認同那些精神科醫師的分析嗎?他認為自己是他們口中的繭居族嗎?所以那些被大眾稱為繭居族的人,自己可能並不知道自己被這樣稱呼?
當天沒有機會多聊,但我想到滌竟然想要去查。其實也不能說「竟然」,滌本來就是會想要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的那種人,他會想去查是非常「正常」的事,只要那個令他感興趣的東西,「有機會」被他遇到。比如盧郁佳,比如繭居族。
◆
在把書拿給滌之前,我不太確定自己是否該在臉書上寫他的事。寫在書裡是一件事,寫在臉書上又是另一件事。但這次回家跟滌聊,我發現他似乎樂意自己的事被知道。我覺得這很神奇,他看起來不願意與這個世界接觸,但當他讀到別人寫他,他似乎透過這層關係,與那個書寫者有了一種聯繫,與這個世界有了聯繫。
這個聯繫當然不是真的有一條線,而是某個關心他的什麼,激起了他對世界的好奇。我想滌感受到盧郁佳在寫文時,對「滌」(或像滌這樣的人)的理解與關心。當這個理解與關心,傳到滌那邊去的時候,滌說著說著,哭了。
滌一邊流淚一邊說,這是喜極而泣。
我沒有哭,反而是靜靜的感覺這些。這個在兩年前我還不曉得要不要去跟他說話的人,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跟我說話,想不想跟我說話,現在在我面前,主動跟我說他讀了書寫他的文章之後的,自己的感覺。這些,在我寫《滌》之前,我不會知道。當然如果我沒去寫,很可能這些都不會發生。
──20200503
我走進房間,靜靜的把書擺在他的床上,那看來是目前唯一可以放書的地方。滌開始說話,似乎沒有看到我手中的書。這很神奇,以往他會注意對方每個細微的動作。滌開始說話,說我昨天給他的草莓,他說盒子打開,草莓的味道就衝出來。他又比較了一下市售草莓跟我給他的草莓的味道。說著說著,他停下來的那個時間空檔,我指指床上的書,我說,書出來了。
他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眼睛一亮,然後身體倒退。是真的身體倒退。他倒退一步,但眼睛仍然盯著擺在床上的書。這時我把書拿起來,遞給他,我又說了一次,書出來了。
他接過書,眼睛亮著。他說,我看到「滌」了。他指的是封面上那個滌,在黑底上金色的滌。「這個字寫得好ㄟ……」我沒想到滌馬上稱讚起這本書。滌拿著書,端詳了一會,還沒有翻開。他拿著書開始走來走去,口中唸著怎麼辦怎麼辦。他看起來有點不知所措。我問他,你是不是在找地方放?他點頭。但他房間的桌上有灰塵,他看來不知道該放在哪裡。
還沒給滌書之前,媽媽問我,你也會給滌一本嗎?我說對呀,當然。媽媽說,你書給他,他一定一下子就弄髒了,「他根本不會愛惜書。他都把我的書亂撕,做他的便條紙。」我說書我一定會給他,「給他就是他的書了,我就不去想書會怎樣。」
結果沒想到,滌現在竟然對該把書擺在哪裡,不知所措。滌討厭去接觸他人碰過的東西,看起來好像有潔癖,但其實不是。他的房間總是隨意丟著穿過的衣服。他不打掃房間。對他來說,那些灰塵那些「髒」,都是自然的。只要他人沒有碰過,那些髒,他都可以接受。
而現在,他突然在意起桌上的灰塵,桌上的水漬。他不曉得該把《滌》擺在哪裡。我看著他的舉動,所以他很在意這本書?我看著他不曉得該把書放哪的樣子。我拿出一張月曆紙,本來用來包書的月曆紙。我把紙鋪在桌上,接過他手中的書,「我鋪了一張紙,幫你把書放在紙上好嗎?」
◆
把書給滌的隔天早上,我從廁所出來,看到一個身影。那個身影看起來像是要閃進廚房,可是又定住,在那邊猶豫不決。那個身影當然是滌,滌在那邊猶豫不決。滌低頭喃喃自語,「要不要,要不要呢?」我察覺到他有話想說,而且是跟我說。我站著等他。
我等他,這次他抬頭正臉看我,「我在想要不要……」他開口,又停住,他指著櫥櫃上的檯燈,「你看,我連那個東西都找出來了……」
這是第二次,滌主動跟我說話。
把那個東西找出來了,意思是把檯燈找出來。如果他沒說,我也不曉得我們家有這盞檯燈。他指著檯燈,說房間光線太暗,看書要燈。所以他是想要告訴我他為了讀這本書,所以把檯燈找出來?他說檯燈被放在櫃子好多年,都是霉味,要先擺在客廳通風。他用手去摸脖子,說他已經很久沒有看書了,「我都看網路,我很久沒有看書了。」可是他很想看,很想看。
接著他問我現在要做什麼?有空講話嗎?我本來是要進媽房間幫她弄電腦,但我看滌很想說話的樣子,於是我說,一個小時。滌說好,一個小時。
開始說話後,滌說起盧郁佳。他說,我還沒看你的正文,雖然我之前看過電子檔,但你修改完稿的我還沒看,「我現在卡在盧郁佳。」滌說,「這個人真是個咖。」
滌說盧郁佳真是個咖的時候,我有點想笑,他竟然用「真是個咖」來形容。但滌的表情很認真。「盧郁佳是小姐嗎?」我知道滌問的是盧是男生還是女生,於是我回答,她是女生。接著又問我她幾歲,我說比我大幾歲吧。滌說你可以跟我說她是怎樣的人嗎?我很想知道寫這篇推薦序的人是怎樣的人。我說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樣的人,我只跟她通過幾次信,其他的就是網路上能找到的資訊,「我能找到的,並不比你更多。」我還沒有真的認識她。
滌說,「盧小姐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滌說他剛開始讀的時候,想說這個人這樣寫是不是在幹我?竟然說我是家裡的大魔王!「可是再仔細想,又覺得她沒說錯」。滌不服氣,卻又同意她。滌讀她的序,讀得非常細,幾乎是一字一句的讀,「她說得沒錯,我不是不會控制,我是控制得太多。」
在這之前,滌不認識盧郁佳,他很少讀與文學相關的作品或文章。然後他也因為盧郁佳的序,去查了「繭居族」這個名詞。
滌這一說,我才知道他沒聽過「繭居族」這個名詞。現在換我驚訝。
「你沒聽過繭居族?」
「對。沒聽過。我剛剛才去查。」
仔細想想,《滌》這本書的正文,似乎真的沒有出現過「繭居族」這個詞,可能是因為我一直避免直接使用它。但我沒想過滌沒聽過這個詞。
那天聊天,滌說著說著又說到別的地方去了,當下沒有機會針對他找到的資訊再多做了解。但當我知道原來滌沒聽過繭居族,我就很想知道那麼當他查到網路上的相關資訊後,他認同那些定義嗎?他認同那些精神科醫師的分析嗎?他認為自己是他們口中的繭居族嗎?所以那些被大眾稱為繭居族的人,自己可能並不知道自己被這樣稱呼?
當天沒有機會多聊,但我想到滌竟然想要去查。其實也不能說「竟然」,滌本來就是會想要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的那種人,他會想去查是非常「正常」的事,只要那個令他感興趣的東西,「有機會」被他遇到。比如盧郁佳,比如繭居族。
◆
在把書拿給滌之前,我不太確定自己是否該在臉書上寫他的事。寫在書裡是一件事,寫在臉書上又是另一件事。但這次回家跟滌聊,我發現他似乎樂意自己的事被知道。我覺得這很神奇,他看起來不願意與這個世界接觸,但當他讀到別人寫他,他似乎透過這層關係,與那個書寫者有了一種聯繫,與這個世界有了聯繫。
這個聯繫當然不是真的有一條線,而是某個關心他的什麼,激起了他對世界的好奇。我想滌感受到盧郁佳在寫文時,對「滌」(或像滌這樣的人)的理解與關心。當這個理解與關心,傳到滌那邊去的時候,滌說著說著,哭了。
滌一邊流淚一邊說,這是喜極而泣。
我沒有哭,反而是靜靜的感覺這些。這個在兩年前我還不曉得要不要去跟他說話的人,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跟我說話,想不想跟我說話,現在在我面前,主動跟我說他讀了書寫他的文章之後的,自己的感覺。這些,在我寫《滌》之前,我不會知道。當然如果我沒去寫,很可能這些都不會發生。
──20200503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