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太好,怕以後讀不到。先存。)
過去讀二戰納粹德軍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書寫,我常常好奇,到底在一個黑白分明的暴行面前,為甚麼還有人可以支持德軍?到底在滅絕人性的日常裏,人們是如何過活每天?真的就沒辦法推倒暴政嗎?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的前一天,基本上無人想像過第二天蘇聯就倒台了,許多大學教授甚至國防專家都還預料要與蘇共以年計對抗。當然在這之前,有無數零星或大或小的反抗、武裝革命、組織串連等等。但就是這麼一夜之間。我們怎知道明天中共會否倒台?而如果不是明天,是甚麼時候?歷史有軌跡,往往驚人相似,但總有未知及偶然,這也是為甚麼歷史不會終結。而如果不是明天,那麼活在反人類當下的我們,又該如何整理自己,怎樣去堅持下去?
哲學家傅柯對我們說,「來自邊緣」的「鄙民」(在今天的香港則是「暴民」)卻可能藏有真正的顛覆力量。他們面目模糊且出其不意的製造混亂騷動,這些爆發式行動卻一直為我們的日常刻下不可忽視的記號——有些東西出了問題,有些說話被消音了——「沒有人能證明這些嘈雜聲響所唱出來的歌會比其他人唱的更優美,同時能說出什麼真理。但只要這些嘈雜的聲響存在就夠了;它們對所有的消音進行反抗,以便能有個傾聽這些雜音的方向,並尋求這些雜音真正所要說的。」
更何況這群「暴民」,用了渾身解數,向本地向國際宣傳解說,只花了僅僅四個多月,就推翻了中共自1970年代中美建交起建立的國際形象,現在每個人提起中國,就只會想起霸權,殖民壓逼,自由的敵人……這已不僅僅是雜音了,雜音成曲,響遍國際——知識份子的責任,在於把雜音譜成人們能讀懂的詞曲,而這幾個月,知識份子是不是沒有承擔起該負之責?
最近梁文道先生問了一個他稱之為「太過實際」的問題——「每逢有人說到革命,或者這種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的壯語,我總是會追問『然後呢?』」。他說真正負責任的政治,是不能不問革命之後的第二天該怎麼辦。
我記得文道先生在2007年的時候寫過一篇題為《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他說——「10年後你(林鄭)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我也記得文道先生在2008年《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裏寫道——「在那裏(中國),你或許會遭到很多反駁,但你起碼不孤獨,而且真有一種我們能夠改變現實的感覺。在那裏,觀念還是被尊重的,觀念還是有力量的。」
或者我們今天也該對文道先生早(十)幾年的「壯語」,追問一句——然後呢?
運動沒有大台,其實意味着每個人都是大台,因此每個人都要思考自己的行動對運動的影響及其後續。我是認同梁文道先生的判斷,搞政治需要負責任,問點實際的問題。在這樣的香港裏,每個人都對這個土地有份責任。其實人有不同的命運際遇和抉擇,對於生命該怎麼投放都有原因,無可挑剔。只不過,在問「實際的問題」前,我們或者都該問自己——作為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如果不希望事態往壞方向發展,我們「然後可以做甚麼」?我們也可以倒過來問——假如不作為,或者當運動停了下來,「然後」會發生甚麼事?我們會不會如新疆西藏一樣蒙受集中營、極權統治?
文道先生對於香港局勢的悲觀判斷,其實我也是認同的。但這樣的判斷與預期,也是絕大部份香港人從一開始就知道的。回想6月9號大遊行前,幾乎所有對於行動者的訪問,受訪者都明言覺得沒有機會贏,法案不會被撤回。但大家就是抱着不屈,然後行於所當行,各自在範圍裏盡力貢獻。無人不知文道先生口中的軌跡,但歷史從來都是在創造不確定性,稍稍挪移其彈道。香港的反抗走到此刻,中共未贏我們未輸,是大家的努力。
文道先生說「有人居然以為特朗普會是香港示威者的救星」,又說「這些人是否仍然相信勇武運動的升溫會帶來好結果?」。他這樣說肯定沒錯,二百多萬人的反抗運動裏,你總會找着幾十幾百幾千個持這樣想法的人。但這些想法是否運動者間的主流?我很懷疑,也傾向不覺得示威者如此天真。
許多論者從運動第一天已不斷擔心運動會失控,示威者會過於暴力傷及無辜。的確,這些事或許會出現,或許今天已有零星此種情況,但這些事在極權無恥拖延,四個月持續暴打殘害人民的情況下,終會出現。我們有沒有想過這樣的情況走到今天才發生,其實是有無數的人在做了無數的事?比如說,「守護孩子」的那群銀髮老人,他們擔心示威者會死,於是就聯手結伴,擋在警暴面前。他們既是保護孩子,其實也是在拖延仇恨的螺旋上升。在你們所擔心的事還未普遍,還處於一個運動內部可以自省的時候,知識份子是不是也可問點實際的問題,思考如何親自參與及介入到一場運動之間,而非站於塘邊不下場沾水?僅點出運動限制而要求抗爭者回答「然後呢」,甚至當事情在我們袖手旁觀而終出問題後自詡先見之明,在我看來,也許都是「不負責任的政治」。
──2019年10月13日,刊登於《蘋果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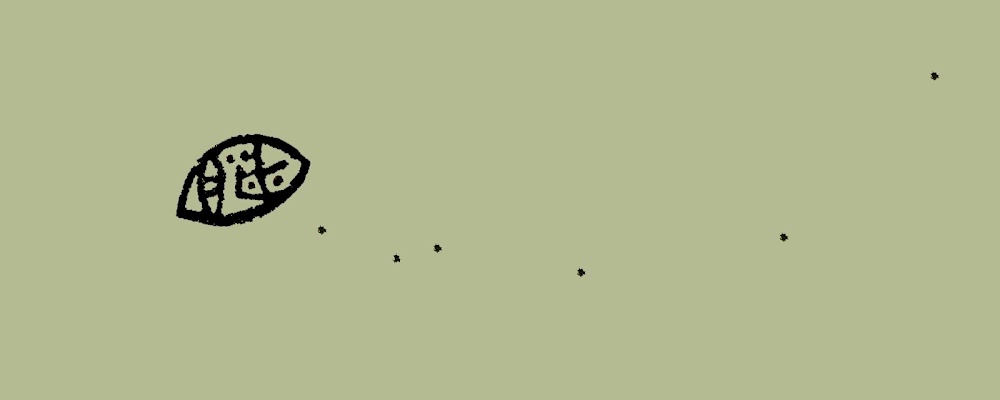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