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楊佳嫻很會帶。她建議我們三人穿插著講,這樣的方式果然是好的,確實是對談,而不是各說各話。因為這樣,我講了一些原本沒在講稿中東西;但也因為這樣,原本準備的講稿並沒有全部講完。
對講稿有興趣的朋友,以下有約四千多字的東西,不嫌長的話可以讀讀看。
◆
【我沒有想過我會來講童詩】
我小時候對「童詩」沒什麼好感,為什麼會那樣覺得,我也記不太清楚了,大概是因為我對讀到的「童詩」都沒什麼感覺吧。比起童詩,小時候的我更喜歡讀小說,我覺得小說有更多想像的天地。
現在竟然要來講童詩,真是誠惶誠恐。
老實說,按我自己來定義的話,並沒有「童詩」這一項分類。我這樣講,大概會被童詩專業人士說你真是外行,嗯,沒錯,我確實是外行。所以今天來,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外行人對「童詩」的想法。
◆
〈好遠好遠的雨只剩下樣子。太陽是蛋黃的樣子。海是線的樣子〉/ 瞇
我看過
可是我記不住
每一場在我眼前的景象
我看著海上的雲
想把她們的形狀顏色看來鬆軟的樣子
像照片一樣留在腦子裡
但是沒有辦法,連一秒都無法
只剩下感覺
所謂的感覺
有時會忘了一些事
比如,那蛋黃一樣的太陽
在我眼前掉進那條線的下面(後面或裡面)
我會以為
她正在緩慢地降落
以為
海是一條線
山是一條線
五分鐘
可能更長或更短
很奇怪
世界好像只剩下那顆蛋黃
但平常時候她其實也都在
海上的雨
遠遠的海上的雨
原來雨有那種樣子
一團會走路的灰色
我好像可以想像在那團灰色裡面
雨會怎樣地打在我的身上
可是好遠好遠的雨只剩下樣子了
就像好遠好遠的雲只剩下雲的樣子
而星星永遠只有星星的樣子
今年八月,我寫了上面那首詩貼在fb上。阿米在fb上留言說:「這首很童詩」。嗯,我的詩好像還沒被別人講過「很童詩」呢。我很好奇為什麼阿米會覺得那首詩很童詩。
「很像小朋友畫的圖,很像小朋友的腦袋。」阿米說。
聽阿米這樣說,我好像突然明白她所說的童詩是什麼。她所說的童詩,是寫詩的手像小孩的手,看世界的眼睛像小孩的眼睛,想事情的腦袋像小孩的腦袋。
雖然我早就不是小孩了,但我寫出來的那首詩給阿米童詩的感覺。阿米對童詩的想法,恰好與我對童詩的想法非常接近。
很多人會問:「童詩指的是小孩寫的詩?還是寫給小孩讀的詩呢?」
對我來說,童詩不一定是小孩寫的,也不一定特別寫給小孩讀的,只是寫出那首詩的那個人心裡有個小孩。這個寫詩的人可能是大人,也可能是個小孩,但不管是大還是小,他們的心裡都有個小孩。
重點不在於寫的人是誰,以及到底形式和內容該長什麼樣子。重點是那被寫出來的文字,或說出來的話,裡面有小孩。
但是,什麼叫做文字裡面有小孩呢?
我在編輯毛毛蟲《兒童哲學》 月刊時,會收到一些家長來信,他們記錄了自己還不會寫字的小孩所講的話。從這些小孩所講的話,或許我們可以稍稍碰觸到什麼是「小孩」。
小兒子兩歲五個月時,有一天我在洗澡,他來開門。我問:你要做什麼?他回答: 「我要看。」 他看到我的陰毛,問我:「那是什麼?」我說那是毛。後來我開始穿衣服,穿上衣的時候,他說:「ㄋㄟ ㄋㄟ不見了。」穿內褲時,他說:「毛,毛不見了。」穿外褲時,他說:「腿不見了。」
小兒子在地板上撿到剪下來的彎彎的指甲,問:「這是什麼啊?」 我說是指甲。 小兒子說:「好像月亮哦!爸爸我要月亮。」
有時候小兒子會說:
「不要倒好多滿。」
「我要畫爸爸的名字。」
──林桂如,〈不要倒好多滿〉,《兒童哲學03》
所以,什麼是小孩呢?對我來說,那代表觀察與思考不受既定印象侷限,表達不受語言文字該如何使用限制。
所以,如果那個小孩會寫字,他把說的話寫下來,就變成了一首詩──
〈穿衣的魔術〉
ㄋㄟ ㄋㄟ 不見了
毛不見了
屁股不見了
腿不見了
我想這大概是大人寫不出來的詩。不過也很難說。
◆
〈可不可以說〉/西西
可不可以說
一枚白菜
一塊雞蛋
一隻蔥
一個胡椒粉?
可不可以說
一架飛鳥
一管椰子樹
一頂太陽
一巴鬥驟雨?
可不可以說
一株檸檬茶
一雙大力水手
一頓雪糕梳打
一畝阿華田?
可不可以說
一朵雨傘
一束雪花
一瓶銀河
一葫蘆宇宙?
可不可以說
一位螞蟻
一名曱甴
一家豬玀
一窩英雄?
可不可以說
一頭訓導主任
一隻七省巡按
一匹將軍
一尾皇帝?
可不可以說
龍眼吉祥
龍鬚糖萬歲萬歲萬萬歲
從小孩的不侷限,可以看出大人的侷限。大人的侷限,讓香港作家西西寫出了〈可不可以說〉。可不可以說,一頭訓導主任?當然不行,冠詞用錯了,而且不敬,老師會這麼說。
還好並不是所有的老師都說不能這麼說。在小學任教的小石子,就曾帶他的學生們進行仿作,小孩們玩得非常開心(我想這應該是他們非常會玩的遊戲)。
〈可不可以說〉仿作/丁緒慈、顏昱庭、梁芷瑜、廖千慧
可不可以說
一隻毛皮大衣
兩位字典
三張樹
四架鳥
可不可以說
五株仙草
六個雀巢
七束豆花
八匹沙其瑪
可不可以說
一滴感動
一絲開心
一頓生氣
一盆難過
我覺得「八匹沙其瑪」真是經典。
◆
我覺得對小孩來說,應該沒有詩該寫成什麼樣子,就像沒有畫應該畫成什麼樣子。詩該寫成什麼樣子?畫應該畫成什麼樣子?這些都是大人教給小孩的。一旦學會了「怎麼寫詩」、「怎麼畫畫」,說不定就沒有童詩童畫這種東西了。
所以我不會教小孩什麼是詩,或怎麼寫詩。因為老實說,到底詩是什麼我也沒有辦法好好地說清楚。所以我不會跟小孩說「我來教你們什麼是詩」或「我來教你們寫詩」,我不會給小孩這些定義上的東西。不過,我會給小孩讀一些我覺得不錯的文字,或是我剛好想透過那些文字跟他們討論些什麼,而只是剛好,那些文字被叫做詩。
我在台東的瑞源國小帶小孩上自然生態寫作課。在小學上課我遇到一個難題。小孩太習慣被管,而一旦大人不管,小孩就會鬆掉;小孩整個鬆掉,課程就無法進行,也沒辦法好好地跟他們講話;但是,我不想用「管教」和「處罰」的方式來上課。我把我的困難告訴小孩,跟他們說:「我不想管你們,就像我不會去管大人一樣。但是你們一沒人管,就跑來跑去、衝來衝去、大聲尖叫,這樣我們就沒辦法好好上課。你們覺得我可以怎麼辦呢?」
小孩睜著眼睛看我,說:「老師,你可以處罰我們啊!」
「處罰,你們想要被處罰嗎?」我驚訝地問。
「不想啊,可是你不處罰我們,我們就會吵。」小孩說。
今年台北詩歌節跟我問簡介時,我在最後一句寫了「覺得帶小孩上寫作課是目前生活中最花力氣的事」。不是寫作這件事情難,而是在寫作之前的所有東西難。在寫作之前有什麼呢?有生活、有人與人的關係、有思考與感受,這些都是相較於寫作更重要的東西,沒有這些,寫作什麼也不是。
十月初上課時,我帶小孩玩了一個遊戲。我準備了十三首短詩(你也可以把它想成短短的句子就好),分別寫在十三張紙條上,然後折成小方塊。「我們來抽籤,抽到籤的人把裡面的字唸出來,然後說說看自己想到什麼。」我說。
很神奇,第一個小孩抽到的是〈修剪〉。
〈修剪〉/ 瞇
用長剪將樹木修剪成人們想要的樣子
用規範將小孩修剪成大人希望的樣子
用法律將人民修剪成政府喜歡的樣子
抽到修剪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想跟他們討論關於規範和處罰的事,沒想到一開始就被抽到了。抽到籤的小孩讀一遍,另一個小孩說想讀,又讀了一遍。讀完之後我問:「你們想到什麼?」
小孩A說:「要把我們剪成你們想要的樣子喔!」
小孩B抱著自己的頭說:「不要,不要剪我的頭髮!」
我聽了覺得好好笑。我說不是要剪你的頭髮啦,不過規範和處罰就跟剪頭髮這種東西很像喔,就是把對方剪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可是你們有你們的想法,不會想要被剪對不對,要是被剪成自己不想要的樣子怎麼辦?不想被剪,就要有自己的想法;沒有自己的想法,就會被剪。自己對自己要有想法,不管是自己的頭髮,還是自己的行為。所以我不是一直說我不想要處罰你們嗎?就是這樣的道理,我不希望你們變成沒有想法的人。
我一口氣說了好多,小孩到底有沒有聽懂,我也不曉得。有些小孩點頭,有些小孩看著我。
「不要剪我!」小孩B又說了一次。
那次上課我給小孩讀我寫的短詩,其中有幾首剛好都提到了規範與法律的荒謬。我並不是故意選這些給小孩讀,而是沒辦法這幾年台灣社會這麼亂,關於某些體制的荒謬我無法不寫。有個小孩抽到了〈紅綠燈〉:
〈紅綠燈〉/ 瞇
他想走的時候就按綠燈
叫別人停的時候就按紅燈
他說
紅燈停
綠燈走
這是交通安全
他是依法行政
抽到的小孩說她覺得這首詩很搞笑。我問哪裡搞笑(我心裡想著我可不是為了搞笑寫的)。小孩說:「因為紅綠燈不是我們用的。」
這下我不懂了:「『紅綠燈不是我們用的』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紅綠燈不是我們用的啊!」小孩又說一遍。
我想了一下,突然腦袋開竅:「你的意思是,紅綠燈不是我們想要它紅燈就自己給它按紅燈,想要它綠燈就按綠燈的意思嗎?」
「對啦。」小孩說。
你看,這種道理小孩都懂,但那些搞政治的大人們都不懂。
有個小孩抽到〈不能說不〉。
〈不能說不〉/ 瞇
被關在籠子裡在美術館展覽的八哥不能說不
動物園裡的熊貓不能說不
馬戲團裡的猴子不能說不
海洋世界的海豚不能說不
水族箱裡的孔雀魚不能說不
田裡的水牛不能說不
受安樂死的貓狗不能說不
餐桌上的豬肉不能說不
遭廢水汙染的河川不能說不
被砍掉做成紙張的樹不能說不
(可以一直寫下去)
抽到的小孩問「可以一直寫下去」的意思是可以繼續寫嗎?我說對呀,你想寫嗎?小孩想了想,寫了兩句:
被關在家裡的小孩不能說不
圖書室的書不能說不
真是厲害。第一句應該不用我解釋了。第二句我想是因為寫作課是在圖書室上課,他有感而發吧。
我沒有跟小孩說什麼是詩,也沒有跟小孩說為什麼要這樣寫(他們也不曉得那是我寫的)。對他們來說那就是一個一個句子。我發現他們還蠻喜歡讀的,不曉得為什麼竟然還搶著讀,沒讀到的還會不高興。有些讀完之後會一直笑,有些小孩讀完之後會想要學著寫。我發現小孩C很會觀察,因為我完全沒有跟他說為什麼那首詩那樣寫,但我從他學著寫出來的東西,就發現他在進行分析了。
〈做什麼〉/ 瞇
你們住在鄉下
都在做什麼
那隻兔子一直趴著
在做什麼
星星在那邊亮著
做什麼
雲從這裡飄到那裡
做什麼
◆
〈做什麼〉 / 小孩C
他們在飛機上
都在做什麼
那隻大象一直喝水
在做什麼
太陽在那邊亮著
做什麼
海從這裡流到那裡
做什麼
仔細對照小孩C和我寫的,會發現小孩C會先觀察我怎麼寫,然後再開始寫。所以他把「你們」換成「他們」,把「鄉下」換成「飛機上」,把「兔子」換成「大象」,把「星星」換成「太陽」,把「雲」換成「海」。
雖然小孩C不一定明白這首〈做什麼〉想要說的東西,但這樣的觀察與仿作對他來說或許是有趣的。但我想他極有可能明白我在說什麼,因為當他讀完我寫的〈做什麼〉,第一句說出的話是「好無聊」。
◆
我一直說無法定義詩,但這樣的說法好像有點不負責任。就算我說不出詩是什麼,但一定有「我覺得什麼是詩」的一種想法吧!
我覺得有些詩像任意門,比如蔡仁偉的詩。他的〈食物鏈〉非常經典:
〈食物鏈〉/ 蔡仁偉
剪刀
石頭
布
這首詩根本就是從這裡到那裡最短距離的代表。不過,有些詩像任意門,不代表所有的詩都是任意門。
有些詩像遊戲,許赫的〈牧羊人的晚點名〉根本就是遊戲。不過這首晚點名點太久了,我就不在這裡點名了,請原諒。想要跟著牧羊人一起點名的人,可以去找《診所早晨的晴日寫生》這本詩集,找到〈牧羊人的晚點名〉這首詩,看你是要扮演點名的牧羊人還是被點名的羊都行。
而有些詩是生命,真正影響著我的詩是生命。這種詩沒有一定的樣子,不一定是誰寫的,但你讀見它你就知道你碰觸到了生命。而有些生命是詩。
這是我最想讓人觸碰到的東西,不管是寫的人還是讀的人,不管是小孩還是大人,還是我自己。而生命是一輩子的,生命卻也是片片段段的;詩也是這樣的東西。
不曉得為什麼寫到最後有點嚴肅,那來讀一首可能會笑出來的詩好了。很多人讀到〈有用〉這首詩都會笑,那來讀讀看會不會笑好了。不過,當初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下寫出〈有用〉的呢?實在是想不起來。看來,寫出〈有用〉的腦袋,有點不太有用呀。
〈有用〉/瞇
你太有用了
你太好用了
你太容易用了
沒有人比你更好用了
你生出來就是要被用的
孩子,你要做個有用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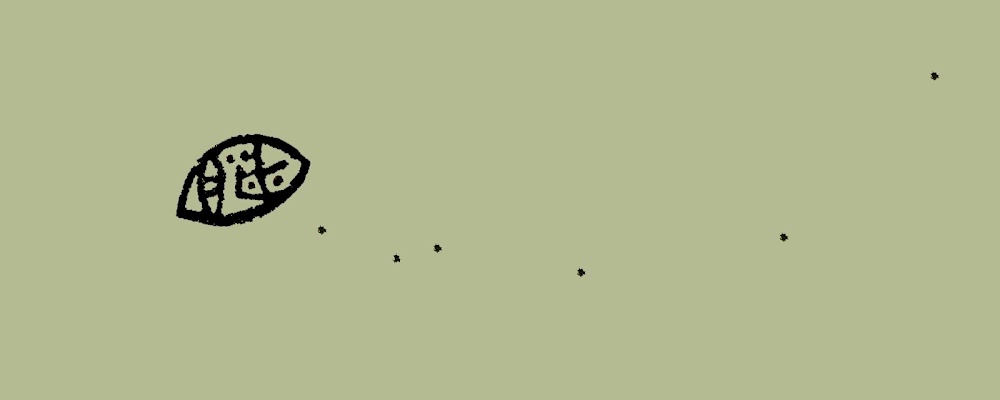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