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議題非常難。難在它明明存在於生活中,卻消失於生活中,因為大家太習以為常,理所當然。從自慰開始,幾乎沒有男人不敢談自慰,但女人就少之又少。以前女孩連月經都不敢談,現在好一些,不再用「那個」來稱呼,衛生棉也不用再躲躲藏藏,但還是有許多曖昧不清存在於性別關係中,像是,有些提倡女性主義的人說女人不能被物化,但什麼是「物化」?穿著暴露就是被物化嗎?當妓女就是被物化嗎?穿得保守以符合社會對好女人的期待難道就不是物化?讓女人沒有生存能力只能被迫嫁人的難道不是一種物化?
最近在讀《紅線》。紅線中討論的性別面向,讓我最近不管看什麼都會注意到當中的性別意識,或是女人身處的狀態。以前看不一定有所連結,但現在看便處處是性別。昨天看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裡面的〈自由夢〉,有人能為自己贖身是自由,或是自己為自己贖身,但我昨天看在眼裡,我反倒覺得能自食其力甚至有籌碼跟嬤嬤談判的藝妓更為自由。不自由是被社會綁住,渴望一個約定俗成的歸宿。當藝妓看來像是賣身,但因為懷孕而必須出嫁更像是把自己賣給男人。
所以《紅線》在談的其實是自由。怕他人說自己髒,怕他人說自己蕩,但有問題其實是那些說人髒說人蕩的人?女孩怕自己被說髒,但為什麼不是那個未經同意就進入女孩身體的人髒?為什麼是被進入的髒?
什麼又是「同意」?「你有沒有說不?」在《她和她的她》裡,少女說,老師壓在我身上的時候,我沒有說不,我為什麼沒有說不?我為什麼沒有說不?她反覆地說著為什麼我沒有說不,快要發瘋。她們能說不嗎?她們懂說不嗎?她們敢說不嗎?
《紅線》提及另一種更曖昧不清的權勢在成人男女之間。「你討厭我嗎?」男人問。女人不討厭,但也不想跟男人發生性關係。而男人以一種自以為開放自以為瞭解女性主義的姿態,對女人說,你應該要解放你自己。因為是敬仰的男性前輩,因為不確定,因為怕打壞當下原本感覺美好的交流,因為怕被討厭,女人沒有拒絕。但她有同意嗎?她模模糊糊,不清不楚。你可以說她傻,但男人也確實利用了他的位置與權勢。
而墮胎,又是這社會另一條紅線。明明是女人受傷,女人不得不墮胎,卻被說成是女人不檢點。就問女人是自己懷孕的嗎?不論是遭姦受孕,或是與男性戀人之間的不預期受孕,必須拿掉小孩所需要遭受的身心之苦,男人卻可以置身事外。更令人感到灰心的是,滿口女性主義的女人,這時也加入施壓:「你確定你要把墮胎的事寫出來?寫出來對你不好喔。」
在《燃燒女子的畫像》裡,女僕懷了孕要自己解決,沒有哭鬧,沒有悲傷,只有必須處理。18世紀的城堡裡,整部片沒有男人,而她們的生活卻被男人左右。「你不用結婚嗎?」「不用。我可以繼承我爸的工作。」女畫家因為可以自食其力,不用為了生活而結婚,而有錢人家小姐必須結婚,必須代替死掉的姐姐成婚。但片中的三個女人,她們明明穿著強調女性特徵的衣著,她們明明因為是女人,命運因此被左右,神情卻都有一種獨立感。
被性侵、從事性工作、不能說出口的紅線。代表著懷孕的紅線。代表婚姻的紅線。可以質疑婚姻嗎?結婚是為了什麼?昨天有一則新聞:「根據現行民法規定,夫妻若發生像是外遇,犯錯或責任較重的一方,不能訴請離婚。有法官認為這項規定有違憲之虞,聲請釋憲。」
濱口龍介的《歡樂時光》裡的一個女角,因長期被丈夫忽視而外遇,她希望離婚,但外遇的一方不能訴請離婚,而丈夫又口口聲聲說愛她。她想證明被當成透明人、被忽視也是一種冷暴力,但無法舉證。我忍不住想,法律中的婚姻是法律關係,法律可以定義責任義務,但可以約束忠誠嗎?法律無法約束啊,不論是刑法還是民法,都無法約束忠誠。
不論外遇的是男是女,法律對婚姻的規範,真的能保障愛情嗎?法律無法保障愛情,只能規範義務,已經不愛了卻要被義務綁在一起,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嗎?
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讀《紅線》後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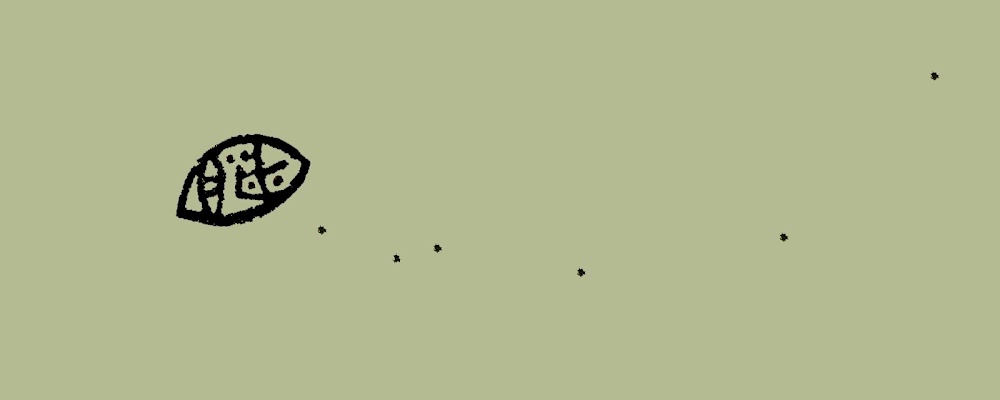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