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2
對於書寫,我有嚴格的自我要求。
每個文學人可能都有這樣的毛病:想要追求精雕細琢的字句,發揮某種精煉的美感。在亞斯這個議題上,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自己永遠也不可能準備好。
p.45
在這個網路社群發達的時代,每隔一陣子,就有「成功人士」在陳述生命經驗的時候突然「自我揭露」了自己的患者身分。光是台灣的名人就有好幾位:好比台大創傷醫學部主任醫師柯文哲、編劇謝海盟、名漫畫家朱德庸……
每當這樣的新聞見報,或者被社團轉載分享時,我總是十分的擔憂。這份擔憂的原因,並不是否認他們的診斷結果或者認為他們不應當揭露與表現與自身的和解,而是因為當社會大眾看到這樣的論述時,幾乎會不假思索的,就將這些成功人士的成功,歸因於他們的亞斯伯格特質。
p.47
以DSM-4的更新日期來看,亞斯伯格症在台灣開始有診斷及輔助機制的時間,應是1994年。由於在此一觀念引進的初期,亞斯伯格症被歸類為「小兒精神疾病」,我到2004年才獲得診斷,已經屬於比較特殊的情況。即使如此,從時間軸來看,我仍然是台灣首批被診斷的亞症患者。
如果你接觸到這個名詞的時間點在1994-2008年,你能獲得最權威的解答可能會來自東尼‧艾伍德──一位在1975年取得心理分析師、於1998年出版,2005年引進台灣,由久周出版社發行的《亞斯伯格症》。在這本書中,,亞斯伯格症是一種「疾病」,伴隨著許多症狀,如「沒有同理心」、「天真、不恰當的行為」、「欠缺社交能力」……等一連串的負面特質。
如今身處2019年的台灣,這些片面、刻板的印象似乎難以想像。但在當年,這就是第一批被診斷有亞斯伯格症孩子的家庭,能夠找到的最值得信任的一本科普書籍。
這真的嚇壞我媽了。她一直以為她的孩子只是有點怪。和他一起閱讀這本書的我也嚇壞了,因為我看到這本書籍所羅列的那些「幫助」我的方法,簡直就像把我當作一只需要經過各種訓練才能夠與他人一樣「正常」的怪獸一樣。我相當感謝我的母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沒有一板一眼的使用上面的方法來嘗試「矯正」我。
p.49
2013年是亞斯伯格症被除名的一天,也是台灣醫學界開始著手改動身障礙鑑定機制的一年。與時俱進,台灣政府決定將過去在鑑定制度上較為呆板,也比較帶有歧視意味的「國際機能損傷、身心功能障礙與殘障分類」,改制為需求評估可較為彈性,名詞也較為中性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ICF)
自ICF在台灣施行至今,正反兩面評價都有。但純粹就亞斯伯格患者以及亞斯家庭來說,很難說這樣的改動是可喜的。直到此刻,我尚能回憶起此一消息最初傳播開來的時候,許多亞症家庭的焦慮。
「你說你的孩子有亞斯伯格症,但不是說沒有這種病症嗎?」
在法律與社會福利系統之中,一個詞彙的變動,所牽涉到的往往比表面上起來更加重要。儘管在現行的台灣制度下,大部分的亞症(或稱泛自閉症類群障礙)患者能夠穩定地在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也能夠在這個階段透過特教法獲得支持與協助,但當他們要離開校園,走進社會時,所能獲得的支持可能就會面臨斷層式的衰減。當面臨困境、想要向公部門尋求社會福利與其他領域資源的協助時,也可能面臨意料之外的阻礙。
除了制度層面上的難處,還有社會氛圍上的。隨著亞斯伯格症的除名,這些患者與家庭儘管仍舊能夠獲得協助,但外在社會的不諒解有時會變得更加明目張膽。認為患者沒有病只是在找藉口的人,認為患者揮舞著障礙作為武器的人,甚至對於陪伴者來說,在長期勞心勞力的照顧之下,有時不免也會自我懷疑,並在衝突時脫口而出。
p.59
標籤既是保護,也是束縛。
「我們正常人對受汙名者的態度,以及對他們所採取的行動眾所皆知,因此人們發展出一些善心的社會行動來軟化與改善這樣的反應。」──高夫曼,《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
上面的這一段文字,來自於人類學家高夫曼的著作《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作為一位人類學家,他在這本書所討論的議題,與社會的弱勢族群有高度相關。在書中,他也精準地描寫了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處境:對需要輔助的障礙而言,即便旁人願意以最大的心態來「關懷」與「協助」,仍舊會使受到幫助的人感覺到自卑、受損、低人一等。而當這些人試圖突破自身既有的障礙,追求更好的發展時,他們的身分標籤,就會在某一個階段,成為貶低他們能力的證據。
大抵而言,除了亞斯本人以外,大眾對於亞斯的態度,可以粗略的被劃分成兩個傾向:意識到自己必須學會和亞斯共生共存的人,以及將亞斯當成闌尾、可割可棄的人。前者包含患者的親屬、選擇與患者共事、結交、甚至戀愛、共組家庭的人;而後者則認為自己能透過任何方法,來降低與患者接觸、社交的機率。
p.61
「不同的身分,會產生不同的立場,也會影響接下來的溝通效果。」引號裡這句人文學科的基礎知識,在現實生活裡卻不是人人都能夠察覺。當雙方在溝通過程中追求的根本目的不同卻無人覺察時,溝通策略很容易便會演變成情緒性的言語與行動,對另一方產生勒索的效果。
以我自身為例,作為台灣第一批被診斷的患者,國高中時期所面對的,是一個不斷變動調整的亞斯伯格判定與標準。在不斷參與亞斯伯格相關研究計畫的過程中,不只一次,年少的我必須和拿著《亞斯伯格症》來理解我的母親爭論(幾年後換成了《亞斯伯格症進階手冊》),討論書中所敘述的與我自身現實的落差。就是在這些爭執中,我覺察到她的堅持有時並非是出自於理性的討論,而是受到社會上身為「人母」角色的壓迫所致。比起以「探尋自我特質,追求獨立性」的我本人,「家長」必須承擔「讓孩子變得正常」的壓力,每當我表現出大眾認為脫序的行為時,責難的眼光往往會加諸母親身上。
p.71
我們所身處的是這樣一個社會:時刻提醒你為了它的健康必須排除不穩定的因素,你接受的原因,大抵上是因為覺得自己是健康的一方,但那並非由你決定。
誰決定誰是健康的?誰決定誰是正常的?誰決定誰需要被矯正?誰決定誰負責矯正的執行?你現在站在哪裡?你該不該站在那裡?
p.99
作為亞斯伯格症的患者,我看見為此設立的家長團體、資源機構在處理此議題上付諸的嘗試與努力。然而身在其中,作為使用(或者說被使用)這批資源的一員的我,卻始終有一個疑惑:為何所有課程設計的目標,幾乎都指向於訓練亞症患者「適度社會化」的能力?
p.153
我遇過很多亞斯,他們都是討厭讀書的,尤其討厭小說與詩。因為這些作品給予他們太多的不確定性。星星的孩子向來討厭所有不確定的事物。在他們腦中,邏輯建造世界,大黃蜂除外。我也是這樣,如今在本質上亦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因此文學是重要的,因為情緒建構社會。不幸從星星掉下來的孩子,終究必須面對邏輯以外的世界。如果你讀了《慈悲的滋味》,你就知道不是所有善心,都有美好結局的道理。如果你讀《將軍碑》,就知道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真正可靠的,包含自己的記憶。
p.163
對我來說,人文科學像是一把鑰匙,開啟了我去了解那些過去在我眼中毫無道理的社會規則,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建構出來的。而對大部分的亞斯而言,有時僅僅是這樣,就能讓他們放下自己的固執,試著去思考事物的發展,有其他的可能性。
── 《我與我的隱形魔物:成人亞斯伯格症者的深剖告白》,蕭上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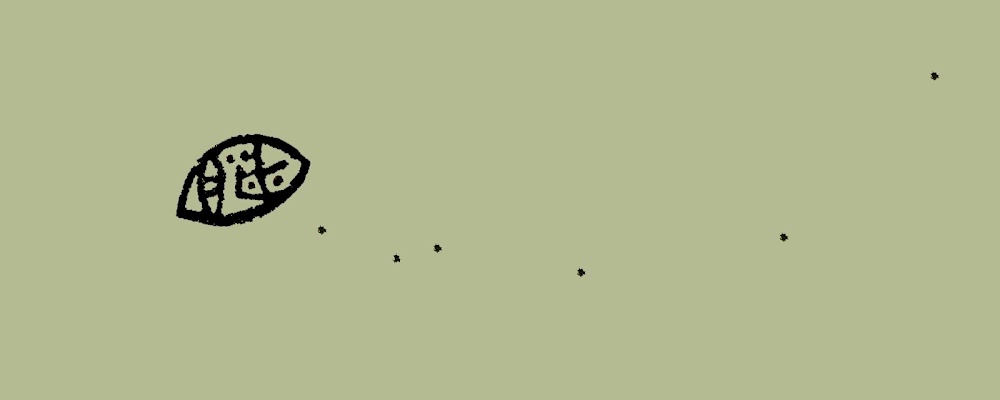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