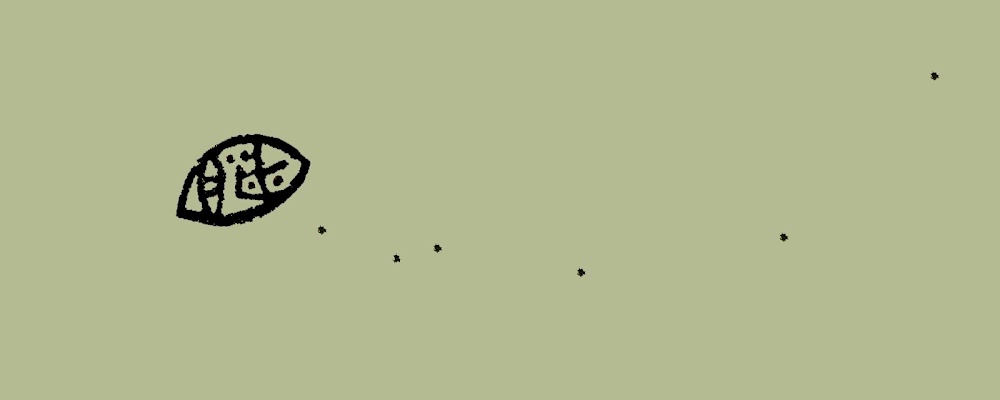你看到了,所以你相信了?還是因為你相信,所以你看到?
◆
最近在讀《所信即所見》。買了很久,一直到最近才讀。可能因為它看起來很厚?可能因為書的「樣子」看起來不易讀?但開始讀之後發現,它跟我想像得不太一樣。我原本以為會很硬,結果一點都不硬,它像說故事一樣。但這個說故事的人有點「煩」,他為了兩張照片的前後順序,千里迢迢跑到照片當初的拍攝地點,跑到克里米亞的一個名為「死蔭幽谷」的地方,之後還做了一大堆調查,為的就是想找出那兩張照片的關係。
是哪兩張照片那麼重要?
與其說是照片重要,不如說是莫里斯想知道──桑塔格說那張名為「死蔭幽谷」的戰爭照片是經過擺拍,究竟根據為何?
「事實證明,許多早期戰爭攝影的經典影像都經過擺設,或是照片中的景物曾遭到竄改更動,這點並不令人驚訝。當芬頓(Fenton)帶著他的暗房馬車抵達塞凡堡(Sabastopol)附近滿目瘡痍的山谷時,他從同一個三腳架的位置拍了兩張照片:……第一幀照片裡,有許多砲彈堆在道路左邊的地面上,但是在他拍攝第二幀──也就是經常轉印複製的那幅照片之前,他監督別人把砲彈散置在道路上。」
──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節錄
如果不是因為埃洛‧莫里斯,我在閱讀桑塔格這段話時,可能完全照單全收,甚至在心裡點頭想著「真是傷腦筋為了成就戰爭的經典攝影作品竟然做擺拍這種事。」但莫里斯對桑塔格的話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既然當時有「兩張照片」,她是如何知道這兩張照片的前後順序?她如何確定「路旁」先,而「路上」後呢?她是如何斬釘截鐵的知道「路上」是透過擺拍所得到的畫面?她是參考過研究文獻所以這麼說嗎?還是她有任何能夠佐證的證據?
莫里斯這一提我才驚覺到,對耶,桑塔格是怎麼確定的?我把那兩張照片找出來,慢慢的看那兩張照片,希望能從兩張照片的異同處看出蛛絲馬跡,好判斷出順序先後。但我發現很難,因為有可能是「路旁的砲彈被移到路上」,也有可能是「路上的砲彈被移到路旁」。那桑塔格是如何判斷的呢?她如何知道「芬頓監督別人把砲彈散置在道路上。」
莫里斯在後續的調查中發現,桑塔格並沒有證據可以確認「芬頓監督別人把砲彈散置在道路上」,是她自己「這麼覺得」。桑塔格認為芬頓是那種會刻意營造戰爭危險而進行擺拍的人,所以當她知道有「兩張照片」時,她理所當然地認為「路上」就是第二張照片,因為「路旁」不夠有震撼力。
老實說莫里斯的發現,有點震撼到我。因為《旁觀他人之痛苦》這本書很紅,桑塔格也很紅,如果不是讀到莫里斯的質疑,我可能真的沒想過「那個擺拍的判斷」很可能是桑塔格個人的見解。因為桑塔格的文字敘述那樣「肯定」,彷彿她說的是一件「被查證過的事」。
但莫里斯也沒有說桑塔格是「錯的」,他只是質疑她為何能那樣「肯定」?那麼,事實究竟是如何呢?既然光看那兩張照片看不出個所以然來,莫里斯決定找到當初的拍攝地點,為此他還找了當地的導遊,希望能透過拍攝地點的方位、光影(先確認太陽的方位,然後判斷光影在砲彈上的表現,但後來發現拍攝時的天氣條件會影響光影,就很難確定時間……);也找了研究這兩張照片的學者,還找了照片鑑識的專家……最後他發現……
最後的發現我就不破梗了。
但我想再提出莫里斯在追查過程中提出的一個思考點──「路上」和「路旁」這兩張照片曾經同時被展出,也同時被收錄在芬頓的作品集中。假設芬頓真的想透過擺拍來騙人,那他根本不需要將兩張照片都展示出來,他不需要讓世人知道有另外一張照片的存在。
PS.《所信即所見》總共有四個章節,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照片外,另外還有多張照片等待解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