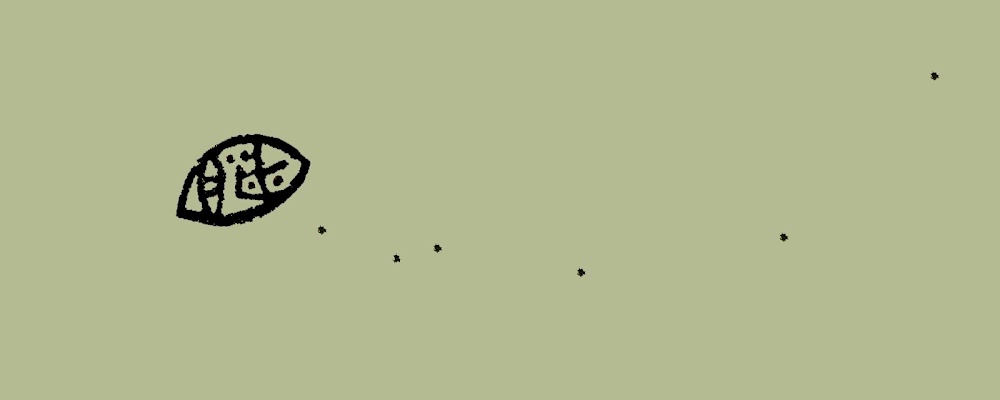這張照片太美了。所謂的wabisabi是這樣嗎?看起來有擺又好像沒有擺,那個碗的khih-kak(缺角)khih得剛剛好。感覺這時候就要唸khih-ka,khih-ka感覺只khih了一小點;「缺角」聽起來感覺缺了很大角。
然後那個光,光也太剛好。
一切都不刻意。唯一做的就是拿了一個khih-ka的碗,把那碗豆子擺在豆莢中間。
(photo by 老斌)
2021年4月26日 星期一
wabisabi
2021年4月24日 星期六
「真正的哲學思考,就是當人思考一物時,就像是全然沒有人思考過的樣子去思考。」
早上看到宋文里老師臉書,提到史作檉,想起了一件事。
我第一次知道史作檉,是在泰順街巷內的一間很奇妙的工作室。我散步經過,看到一棵很大的麵包樹,枝葉由左而右,長到對面的房子三樓陽台,像是拱門。工作室有個木板平台,看起來不像店面也不像住家(我後來才知道那是工作室)。我走近窺望,這時工作室主人剛好把拉門拉開。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個半開放的工作室,主人平常在裡面畫畫,工作室內也賣咖啡、有二手書,但沒有特別對外說明開放,有種──知道的人就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我在這間工作室遇見《哲學日記》這本書,作者史作檉。當時我不知道史作檉這個人是誰?甚至「檉」這個字我也不會唸。
《哲學日記》的第一句話就打到我:「真正的哲學思考,就是當人思考一物時,就像是全然沒有人思考過的樣子去思考。」
讀的時候我覺得這話說得真「對」。因為當時我對某些人講到哲學就是搬出許多哲學論述感到厭煩。好,你知道誰誰誰是怎麼想的,他的世界觀是如何如何,那麼你自己呢?你自己又怎麼想?
可是「當人思考一物時,就像是全然沒有人思考過的樣子去思考」──這有可能嗎?我們真的可能像是沒聽過別人說法看法那樣去思考嗎?在長大的過程中我們聽了那麼多看了那麼多。
我繼續往下讀:「但哲學思考之難處,就在於如何去剷除那些聽來的,知道的,似是而非的解釋與名詞,並有充分的能力,使你自己所用的每一個字,都成為完全屬於你自己之成功而有效的字,而不是背誦。這就是一種真正的哲學思考,即一純思考,即在宇宙中思考,而不是在文字間思考。是在真正的人性中活著,而不是在一些雜亂而浮泛之經驗現實之中。其難矣哉!」
當時我還在毛毛蟲工作,我突然想到……所以……小孩比大人更容易進行哲學思考?好像是喔,因為小孩所想的所有事幾乎都是第一次想?
但同時我又感覺到,「第一次想」與「哲學思考」似乎又有那麼一點差別。就像我發現小孩說的話和寫的字,「經常」都很詩意,但有些詩意是因為還未被文字規則所限,是偶然與巧合(雖然是偶然與巧合,但也不能說那就不是)。
我把寫作和哲學思考擺在一起想──我是碰巧說出一句詩意的話?還是有意識的表達?我是不是往裡面去想了?還是我只是順口提出一個問題就停了?雖然一個問題經常是哲學思考的開始。
哲學思考這東西……似乎……讀太多就無法思考(這裡的「讀」是指「背」)。不讀可能也無法思考(但真的嗎?)但我現在就是因為讀到史作檉的《哲學日記》所以繼續思考。可是,如果我沒讀見,那麼他寫的那些我真的就沒有機會想到嗎?
2021年4月23日 星期五
吃麵的兆頭
應該要專心寫稿子但還無法,那就先寫讀書心得。
今天早餐讀老派少女,把〈吃麵的兆頭〉又讀了一遍。重讀那段寫同行男士去鵝肉麵攤卻不點鵝肉,最後點了一盤帶霜的生魚片;第二位男士挑了間義大利麵鋪,點的培根雞蛋麵慘遭廉價奶油滅頂,卻吃得很香,「家教使我保持微笑,把麵吃了。心裡想,也就這麼一次。」
讀到這裡我忍不住想起某人也會透過吃來判斷人,只是老派少女家教好總是保持微笑,而某人心直口快嘴巴比較X。我個人倒不覺得飲食習慣有高下之分,但藉由習慣來辨識自己與此人是否相合,吃確實是個兆頭。
「憑藉吃麵,看清彼此的參差……」「見識過不少感情成災的事,是從生活裡的碎石細砂開始崩塌的。事先有兆,不必自欺欺人。」
能有一起吃飯的伴侶,很是幸福。
2021年4月22日 星期四
聲音越線?
我關掉音樂,靜下來聽周圍的聲音。
有鳥在叫,「咕嚕嚕……咕嚕嚕……」「啾啾啾……」「嘎嘎嘎……呱呱……」我不確定有幾種鳥,牠們在叫,並不會令我厭煩。Y喝水,嚥下去的最後一口漱口,漱口的聲音;Y走進房間,拖鞋啪咑啪的聲音;鳥繼續在叫,聲音不小──但這些聲音都不會令我難過。對,難過。約二十分鐘前附近鄰居傳來的音樂聲,那飄散在空氣中持續不斷的凍茲凍茲令我難過;聲音不比我現在聽到的鳥叫聲大,但就是令我難過。那凍茲凍茲會一直鑽進我的耳朵。凍茲聲沒有大到需要去跟人家說。我打開筆電,打開喇叭,試著用自己家裡的音樂蓋過。
我的音樂放出來,但我還是可以聽到隱約的凍茲凍茲。那凍茲凍茲像是不用透過空氣,而是以直線震動打進我的心。我很想忽略,想不去注意,我知道我越注意那聲音就越明顯,雖然它明明不怎麼大聲。我的音樂蓋過去,稍微好一些。但如果可以我希望沒有現在沒有音樂。我那麼怕聲音嗎?不是怕聲音。車子的聲音、割草機的聲音、吹落葉的聲音、小孩的玩鬧聲、甚至鞭炮聲,這些我可以理解的聲音我就可以接受。可以理解是什麼意思?我理解這些聲音是為什麼──因為車子經過、因為在割草工作、因為小孩在玩、因為過節放炮,這些聲音都有結束的時候;但大聲放進空氣裡的音樂以及卡拉OK,我不知道它們何時會結束。
那些音樂和卡拉OK,這些聲音沒有理由沒有道理嗎?有,他們在歡唱取樂,在high。他們把high放出來,把high放進空氣。空氣沒有界線,聲音越過家戶,透進門窗。我可以理解high,但我不理解high為什麼要越過界線?他們不能把鐵捲門拉下來在屋內high嗎?
可是其他的聲音不也越過界線?為何我對這些high聲就無法忍受?我無法忍受似乎是因為我將它解釋為自私──「因為自己想大聲聽音樂,就放得好大聲……」「因為想唱歌,就把喇叭開得好大聲……」但是小鳥不也想叫就叫?想唱就唱?小鳥就不自私嗎?大聲唱歌大聲放音樂的人類就比小鳥自私?
自私是什麼?聲音的空間真的有界限嗎?
我關掉音樂的時候,鄰居的音樂似乎也關掉了。安靜了大概一個小時。所謂的安靜,是空氣中有鳥叫但不包括人類音樂的安靜。為什麼我覺得這樣叫做安靜?吃過午餐後,又有另一戶鄰居,他們唱卡拉OK,卡拉OK聲比早上的凍茲還要更大,還加上人聲叫囂。現在是下午一點半,他們才剛開始,我不知道這聲音會持續到什麼時候,那聲音鑽進我的耳朵。我對Y說,我們出門。
但為什麼是我們出門?不是他們小聲一點?
我們出門了。Y說去田裡除草,我說我有稿子要寫,「我寫一半了,我可以帶著筆電在車上寫。」我準備了小椅凳、以及可臨時作為桌面的採收籃。我將兩個籃子倒放疊起來,成了高度適中的桌面。車子開進田裡的走道,這是我們租來的鳳梨田。Y去除草了,我說我等一下再加入,我先寫稿。我在箱型貨車上架好寫稿的位置,打開後車門,眼前是田園,田的後方是山。附近沒有住家,卡拉OK的聲音已經離我們遙遠。我打開筆電,耳邊又傳來鳥叫聲,好幾種鳥叫聲。
這裡很安靜。我聽著鳥叫聲寫稿,就在這個當下我突然意識到──剛剛我們開著車子進來,車子在田間小路行進著,引擎的聲音,輪胎滾壓路面的聲音與塵土飛揚……我說這裡好安靜,但對原本生活在這裡的小動物來說,我們其實是入侵田園的人?小鳥可能叫著:「有人來了有人來了!」「他們又來製造噪音了!」「他們把整片雜木林變成田,害我們可以棲身之所變少了……」小鳥們會不會這樣說?生活在這裡的小動物們會不會這樣說?
「所以我也是自私的人?!」我的腦袋中突然跑出這句話。我們就這樣進入了牠們的領域。但那些活在這裡的小動物會覺得這是「牠們的」的領域嗎?牠們會有界限的想法嗎?會覺得我們自私嗎?會覺得我們越線嗎?或是牠們覺得可以跟人類共享?還是牠們根本就不判斷好壞?所以到頭來界線與自私這些東西只存在人類的心裡?只有人類會說他人自私與越線?
──刊載於《幼獅文藝》第808期,2021年4月出版
2021年4月21日 星期三
為什麼拍照
出遠門時我會將sim卡置換到智慧型手機,但卻沒有因此養成移動中拍照的習慣,不管是食物照片還是沿途風景。想起從前大學時候會拿單眼底片機拍照,那時候拍的可能還比現在多,當然有可能是爸媽開沖印店洗照片不用錢。但我覺得還是有個微妙的不同在那裡。
現在更方便普及,還不用花錢,我卻沒想拿起手機拍照,為什麼呢?
昨天吃飯時朋友拿起手機拍照,他說:『年紀大了,不拍會忘記。』年紀大了是玩笑話,但怕忘記好像是真的。但我又想,怕忘記?我真的會在意自己忘了前一天的晚餐吃什麼嗎?
我又想,我應該是不會忘記咖哩先生的菜色,如果我想拍照,應該是想要分享。最終我沒拿出手機來拍,我想著如果有需要就請朋友傳照片給我就好。但後來我也沒跟朋友要照片,我上咖哩先生的粉專,那裡就有照片。
前天跟一個很少見面卻很多話可以說的朋友碰面,一見面她就說想跟我合照。我說好,但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不好意思。要分開前她說想再拍一次,因為之前拍的不太理想。我們就站在清大校門口找路人幫我們拍 (因為我們兩個人都不太會自拍)。我們眼睛搜尋著可能願意停下來幫忙拍照的路人。
這個?還是那個?最後我們問了一個戴眼鏡背包包學生樣的男生,他有點小驚訝但很快的答應,拍完照還手機給我們時還說謝謝謝謝 。
我拿過手機看照片。我說,兩個人看起來都有點好笑。人拍得有點遠,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滿好的,留下了一張好笑的照片。是說如果沒有留下照片,我真的就會忘記嗎?留下了照片又會讓以後的我記得什麼?
我臉書頭貼是我幼時的照片,我根本就忘記那時的自己 。但這個是我,我的父母留下了照片。
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簡單寫一下我對EVA結局的想法(或延伸想到的東西)寫完我就不要再想EVA了
第一次看25-26話時,我第一個反應是:靠悲,這什麼結局?我應該是哪裡不懂吧還是什麼資訊沒掌握?後來看了劇場版後發現竟然還是這樣,我就想,導演「真的就是」要做這樣的結局,所以我也就認真想了一下我對原25-26話的感覺。
「心中欠缺了某些東西」、「對此恐懼,感到焦慮」、「所以我們要合而為一」、「大家彼此彌補空缺」──如果這就是「人類補完計畫」,如果「人類補完計畫」就像是是某種心靈成長課的論述,那前24話那些龐大的設定是在幹嘛?
但劇場版把「這種結局」又換句話說重新再說一遍,讓我忍不住去想「EVA設定」與「人類補完」和「世界毀滅重新洗牌」的關聯性,好吧──
「我操控不了EVA」
「我控制不了自己」
「我無法跟EVA同步」
「我無法跟自己同步」
「我無法跟EVA合一」
「我無法跟自己合一」
「我討厭他人、討厭自己」
「沒有人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自己」
沒有人了解我。我不了解自己。人類就是因為無法彼此了解,所以毀滅彼此。人類就是因為無法彼此了解,所以創造EVA來毀滅敵人,毀滅自己。EVA毀滅使徒。EVA就是使徒。使徒就是人類。EVA就是人類。人類毀滅人類。
人類不要毀滅人類的方法就是合一。但合一之後還有「人類」存在嗎?
同步率,整個EVA都在講同步率。但我們真的可能百分之百跟自己「同步」嗎? EVA駕駛者同步率最高的是薰喔,但薰不是人類。當然,零也不是人類。
人類是什麼?
2021年4月11日 星期日
七等生:我每天都在研究我自己。
前天,跟Y討論了「七等生」這個名字。
「為什麼要叫七等生?如果要說自己比別人低等,為什麼不是三等生?為什麼不是九等生?為什麼是七等?」
「為什麼不是五等?」
「五等聽起來很中間。九等的話……又會跟『久』聯想在一起。」
「照上中下分的話,應該是三等。但三等聽起來太普通了,太直接了。」
「我第一次聽到『七等生』的時候沒想到等級,我只覺得是個怪名字,後來才知道有等級的意思。雖然他說『我就是七等』,但這個名字沒有把他往下拉的感覺,反而是往上拉。而且你不覺得『七等生』聽起來就很適合當名字嗎?『三等生』不行,但『七等生』就非常可以。」
結果昨天看《削瘦的靈魂》紀錄片時,剛好就看到了「七等生」名字的討論。七等生跟他的師專同學說:以後我不叫劉武雄,我要叫七等生。
簡:「你說自己是七等生。你不說是三等生,硬要說七等,意思是你最厲害。」
七:「沒有沒有,我最爛。」
Y問我喜歡這部紀錄片嗎?我說可以。但其實比想像中的好,因為太難拍了。「紀錄片」,到底是要「記錄」什麼呢?我們無法記錄全部,只能記錄局部。但局部等於全部嗎?局部當然不等於全部,但每一個局部,都是全部的一部分。
所以要問的是,為什麼是「這些局部」?不是「那些局部」?
我看到的《削瘦的靈魂》紀錄片,是眾人如何看七等生,包括七等生自己。眾人說七等生,包括研究他的人,批評他的人、他的同學、小孩與親人;包括他的前女友,但沒有前妻。這些人說出來的七等生,當然是他們每個人各自眼中的七等生。而七等生也說他自己,但說得不多,說得更多的是他著作中的文字。導演節錄了許多七等生的文字,讓那些文字來說七等生自己。雖然那些是「小說」中的文字,但我可以從那些文字中讀到「七等生這個人」的精神。
所以,我覺得可惜的是,導演引用七等生文字時所呈現的「畫面」──我覺得可惜的不是畫面做得「好」或「不好」,而是像〈我愛黑眼珠〉這篇小說,它的文字一旦具象化、情節化,就很難不流於表面。昨天我看〈我愛黑眼珠〉的那幕,在大水的屋頂上,李龍第低下頭與他懷抱中的女子相吻時,我腦袋浮出的是「不是這樣……」。因為,小說寫的是「李龍第懷抱中的女人突然抬高她的胸部,雙手捧著李龍第的頭吻他。他靜靜地讓她熱烈的吻著。」
所以,不是李龍第吻那女子,是那女人吻李龍第。好,誰吻誰很重要嗎?可能也不是很重要,因為畫面上「他們就是相吻了」。我猜葉石濤批評「李龍第竟然移情別戀一名妓女」、「拋下他的妻子」……說不定腦袋也是浮現了那樣的畫面。可是我覺得小說的重點不是表面上的「情節」,「情節」只是用來呈現故事主角的「精神」。李龍第想說的是──
「是的,每一個人都有往事,無論快樂或悲傷都有那一番遭遇。可是人常常把往事的境遇拿來在現在中做為索求的藉口,當他(她)一點也沒有索求到時,他(她)便感到痛苦。人往往如此無恥,不斷地拿往事來欺詐現在。為什麼人在每一個現在中不能企求新的生活意義呢?生命像一根燃燒的木柴,那一端的灰燼雖還具有木柴的外型,可是已不堪撫觸,也不能重燃,唯有另一端是堅實和明亮的。」
──〈我愛黑眼珠〉
我覺得小說想說的是──在「這個時間點」上,我對「我自己這個人」所能負責的(好吧,我這樣解釋可能還是太簡單了。有些文學作品硬要解釋,某些東西很容易跑掉,還是不要解釋得好。可以相互討論,但不要定論)。我覺得讀者可以認同或不認同李龍第,但像葉石濤去批評「怎麼可以寫出像李龍第這種移情別戀的人」?現在的我很難想像當初做如此評論的時代背景(但看了紀錄片後有稍稍了解一點)。
我覺得拍紀錄片「很難的是」的是──引述文字時的「畫面」。精神在文字裡,而不是在情節裡;而畫面有時容易將文字的精神框住。但紀錄片就是用畫面來說話,不可能沒有「畫面」。我就問自己,如果我要引述〈我愛黑眼珠〉,那我會如何構思畫面?(目前我想不出來)
但這部紀錄片確實呈現了七等生的兩極面向──
「我最爛。」
「我最厲害。」
「我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
「我這個人,就代表人類。」
「我每天都在研究我自己。」
我說「確實呈現」,但七等生「真的是這樣」嗎?會不會只是導演拍出的七等生很接近我想像中的七等生?所以我接受了它的呈現?
2021年4月9日 星期五
毋甘願的電影史──台灣曾經有個好萊塢
最近在讀《毋甘願的電影史──台灣曾經有個好萊塢》,目前大概讀了三分之一。前天發現志祺七七剛好也介紹了這本書,就點開來看。我其實很少看網紅介紹書,但很好奇「他們」(我認為網紅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製作團隊)是怎麼用短短十分鐘的時間來介紹這本擁有豐富史料的台灣電影史。看了之後覺得……嗯,整理的功夫真的很到位,參考資料來源也都標示得很清楚,好像很適合給那些要做學習歷程檔案的高中生們參考(哈哈哈離題了)(但我真的覺得可以從部分網紅身上學到怎麼整理、編輯資料的功夫)
總之志祺七七整理得很不錯,當然前提是蘇致亨這本書真的很有料(沒有料的書也整理不出重點 XD)
以下是志祺七七幫讀者抓的重點──
01:41 當時的電影都在演什麼?
04:16 當時的台語片有多紅?
06:28 起起伏伏的台語片人生
07:56 過去學界的說法是?
09:23 台語片消失的真正原因!?
對以上「重點」感興趣的朋友,歡迎在看完志祺七七的介紹後,去找《毋甘願的電影史──台灣曾經有個好萊塢》這本書來看。
然後我自己在讀的時候才赫然發現:那時台語電影海報是彩色的,但電影是黑白的!(廢話,難道我以為海報是彩色的電影就是彩色的嗎......對!我看到海報的瞬間真的忘記那時的電影是黑白的.....)
當然最有感觸的是──1969年以前,台語片盛行時一年有上百部,但1970年後就突然驟降為20部以下,1981年的《陳三五娘》則是「最後一部」純台語電影──短短五年,台語電影就消失了……。還有,1957年台語片曾辦過第一屆金馬獎,但也只辦了這一屆。而這場台語片的頒獎典禮,現場人人口說國語,女演員何玉華也為自己「國語講得太差,不知怎麼說好」感到難為情。唉,可是這明明就是台語片的頒獎典禮啊!
◆
志祺七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Bk7JPcxePY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作家是家庭裡的炸彈嗎?寫作高於親情?──讀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我的奮鬥》
翻開《我的奮鬥:父親的葬禮》,作者卡爾.奧韋.克瑙斯高在第一部分的開頭就寫了「死亡」。他寫的死亡是我沒想過的──「其實只要死者躺在那裡不礙事,就毫無理由這麼匆忙行事,他們也不可能再死一次。」
克瑙斯高寫的死亡極其理性,何必將那些死亡的軀體匆忙搬走?何必將那些軀體排除在公眾視線之外?為了合乎禮儀?但死亡對我們來說其實並不陌生,在這世界中我們身邊環繞著死亡之物──廢棄的燈盞、毀朽的門把、爆開的水管、折斷的樹枝……不論是人工之物或自然之物,無處不充斥著死,那麼人們為何要將人的屍體藏於暗處,再為屍體舉辦明亮的葬禮?讀到這裡,我以為這是克瑙斯高對死亡的看法,對死亡儀式的質疑,我想著他對死亡怎麼能夠如此理性?最後我才知道──他是透過寫來分析他父親的死,告訴自己:這不過就是生命中一個自然的環節,僅此而已。
但整個準備葬禮的過程,他一直在哭。可是他在接到電話獲知父親死訊的那刻,他卻又說,「我沒有什麼感覺。」甚至還閃過「我父親死了,我在想著我從他那裡得到的錢。」「我無法控制我想的事情,抱歉,但就是這樣,可以嗎?」
克瑙斯高對父親「真正的」感覺究竟是什麼?我忍不住一直去想。而這似乎也是克瑙斯高想問自己的──「對我來說,爸爸是什麼呢?」「一個我巴望他死的對象。」「那所有這些眼淚又是為了什麼?」
問題問了,不一定有解答,也不會有正確的答案等在那裡。那麼為何要書寫?為何要將那樣細那樣真實那樣難以說出口的事寫下?克瑙斯高寫到那棟父親生前與祖母同住的屋子,我倒抽了一口氣,那棟瀰漫著腐敗的屋子,充滿屎味尿味以及一切令人不敢直視的畫面,讀到這裡我對伴侶說,第二部分進入正題了,「很好看」。說完「好看」的當下我意識到這就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好看一樣──我怎麼能說出「好看」?怎麼能對他人的痛苦說好看?怎能對他人的不堪說好看?但我確實又感覺我讀著克瑙斯高在清理洗刷那棟被他父親糟蹋的屋子時,我想像著如果是自己會如何面對這樣的處境?我讀到他祖母喝酒喝到失去自理能力,他的祖母怎麼可以在看著自己的兒子酗酒酗到死掉後,自己也落入這樣的境地?而她其他的孩子以及孫子,怎麼可以讓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家活得如此不堪?我發現我有所疑惑,有所批判,然後在疑惑與批判後我繼續讀下去,我讀到更裡面的──無關是非對錯,而是無法歸類的情感與思考。
身為一個讀者,我謝謝克瑙斯高寫了這部書,但被他寫進「自傳小說」裡的親人,我想可能很難對他說出謝謝?
克瑙斯高是自己書中的主角,他的爸爸、媽媽、哥哥,他的祖母他的叔叔以及他的伴侶,都被他寫進了書裡。《我的奮鬥》共有六卷,《父親的葬禮》是第一卷,出版後因寫作內容過於真實而遭受親人反對。而這樣的一部自傳小說在挪威大賣50萬冊,這是否代表人們都有窺探他人隱私的欲望?還是人們因為讀到作者真實的書寫,進而連結到自己的生命?
「作家是家庭裡的炸彈嗎?」克瑙斯高認為是,他同意「當作家出生在一個家庭中時,這個家庭就完蛋了」這個說法。那麼,這代表他承認自己的寫作帶給親人的傷害嗎?那麼我呢?我在寫了《滌這個不正常的人》之後,我是否也認為自己是家裡的炸彈?
寫作者並不是為了當炸彈而寫,而是不得不寫,因為他無法對平靜海面下的暗流視而不見。但當他寫出來時,那些真實便成了炸彈──嗯,不是真實本身是炸彈,而是「掀開」讓它成為炸彈──真實一直在那裡,掀開才使得原本看似平靜的關係被點燃,得以進一步去認識真實。
但什麼是真實?書寫者的真實與被書寫者的真實一致嗎?為了真實而令人受傷值得嗎?取得對方同意之後就真的能不避免傷害嗎?在《滌》出版前,我努力取得家人的理解與同意,但一直到後來我才真正明白,某些難以言喻的心理狀態並不會因為願意彼此理解就能不造成傷害。
那麼寫作者該為了避免傷害而不去寫嗎?寫作者是不是把寫作擺在生命中很前面的位置?是不是可以超過親情與家庭?
我感覺著自己在寫作中的自以為是、矛盾、樂觀與悲觀。樂觀的時候我期待著被家人與所有的人理解我為何書寫,並且沒有任何一個人受傷。悲觀的時候我認為書寫一點用處也沒有,不僅沒用還造成他人痛苦、自己痛苦。克瑙斯高是否也曾經如此?但最終他選擇出版,而我也是。在反覆矛盾游移之後,最終我選擇了寫,選擇被讀見。
寫作有如此偉大嗎?寫作高於親情嗎?每個寫作者各自的選擇不同,我無法替他人回答。而寫作者在選擇之後,必須也只能自行承擔結果所造成的所有「好」與「壞」, 儘管很難做到真正的承擔。
──刊載於 OKAPI: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3846
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
2021年4月5日 星期一
EVA 。果然最恐怖的就是人類自己
EVA 剩兩集。越後面越「恐怖」,果然最恐怖的就是人類自己。進擊跟EVA 都好「寫實」。
剛剛看到臉友寫進擊是她目前心目中的第一。嗯,進擊「幾乎」也是我目前心目中的第一,說幾乎是因為,我覺得EVA也好強。它們如果要擺在一起比我就不知道該怎麼比。
後來想想,覺得進擊跟EVA不能擺在一起比。進擊有五季長達75話(還未完結),而EVA只有26話。拿大架構的動畫跟小架構的比,很難比(就像不能拿短篇小說跟長篇小說比?XD)
但如果要說畫面的氣氛營造,EVA用靜置的畫面來說話,令我印象深刻。畫面就那樣靜置不動,一秒、兩秒、三秒……接下來到底會怎樣?畫面就停在那裡讓「我」等,讓我跟畫面裡的角色一起等……一秒、兩秒、三秒……五秒、十秒、十五秒……等得最久的那幕是真嗣駕著EVA抓住薰,真嗣與薰對望,接下來到底會怎樣?雖然我知道可能會「怎樣」,但這樣的畫面還是令我緊張。它讓我等好久,好像有三十秒那麼久,到底有沒有三十秒那麼久?還是更久?我剛剛打開來重看,再看一次還是很緊張,我一邊看一邊數,它讓我等了四十五秒。那四十五秒,真嗣與薰對望,像是聖歌的音樂在背景裡。最後「結果」還是來了,雖然我「已經知道」結果,但再看一次還是讓我心跳了一下。
那靜置的畫面像是電影裡的長鏡頭。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動畫運用長鏡頭的方式來說話?EVA不只用了長鏡頭的概念,也用了好多拼貼的方式,人物被困在夢裡、困在回憶裡、困在自己心靈裡面的時候,那反覆的畫面造成的壓迫感……
手法可以呈現「精神」,所以手法很重要。但手法卻不是最重要,如果手法裡面沒有想要表現的精神。
薰:「死亡是我唯一的自由。」「快摧毀我。」
2021年4月3日 星期六
自由
看著朋友除草時想著什麼是「自由」。忍不住又重新想什麼是「自由」?
人類經常覺得自由跟腦袋有關。「我的腦袋希望這樣就能這樣,那就是自由」,「我所要的不如我所想的,那就不自由。」
自由存在嗎?自由只是一個概念?當我不知道「自由」的時候,我不自由嗎?
當人認識自由之後,才能得到自由?
還是當人認識自由之後,才開始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