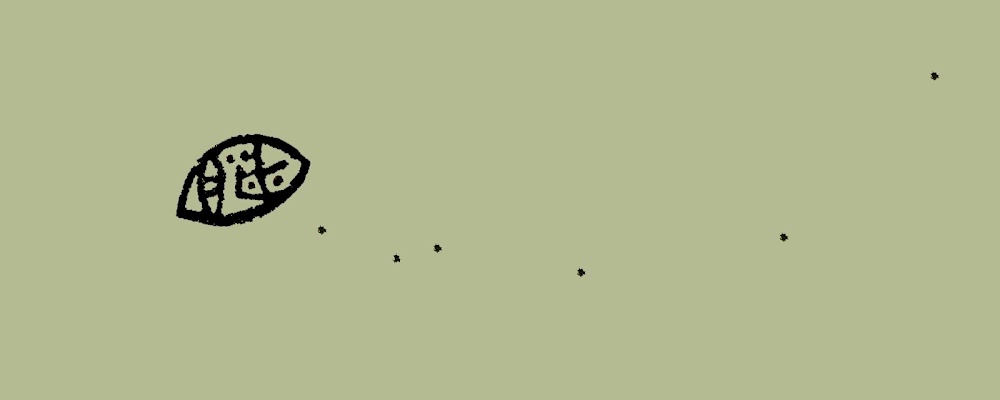又來睡前的murmur。
今天下午在國圖看了五年份的《攝影天地》的廣告(民國66年到71年),軟片啦放大紙啦沖印器材的廣告, 真是看到我頭昏眼花,但忍不住放手,尤其是翻到那篇可以回答我疑惑的廣告時,忍不住幹了一聲就是這個!幹!真的是,好多資訊都牽起來了。之前的「聽說」,現在總算有「更具體」的資訊,不再是聽說,不再是推測。
翻到時好興奮,但大概只有我會那麼興奮,其他人應該不會懂我到底在興奮什麼吧。一邊拍照一邊記錄出現刊期與年份,坐下站起來,坐下站起來(因為不站著拍書頁會反光),手寫記錄,一邊小心不要恍神寫錯,雖然動作很簡單,但這樣持續四個小時也是很累,肚子超餓。
答案就藏在那裡,好簡單,你能找到答案就好簡單。困難的是不知道答案藏在哪裡。
2022年7月31日 星期日
答案就藏在那裡
把忌妒寫得那樣迷人──艾莉絲‧孟若
怎麼能把忌妒寫得那樣迷人?她真心想道歉,寫出來的卻是相反的話,「我的確怪他,忌妒且不屑。」
「他竟然成為作家了」──裡頭參雜著感動與不屑。她深受感動,但同時不屑。那些點子的來源當初可是我的,是我叫他應該要多多觀察。寫出來的雖然是他,但察覺到的人可是我。
◆
「我心想該寫一封信給他。我想告訴他,此刻我才明白(雖然這麼說很怪),原來我們共享的回憶,存在同一個銀行;只是對我來說,這些零星片段如同派不上用場的人生行囊,在他手中卻變成極具價值的財物。同時我也想道歉(當然不必講得太白),居然不信他能當作家。不,是認可,而非歉意,我欠他的是這個。不妨寫幾句讓人舒服的話、感激的言詞。」
我找到一枝筆,拿起放在面前的紙,開始寫信,我運筆如飛,寫出與原意相違的句子,簡短而傷人:
「這樣做不夠,胡戈。你以為夠了,但還是不夠。胡戈,你錯了。」
──艾莉絲‧孟若,〈素材〉。出自《一直想對你說》
2022年7月30日 星期六
我們怎麼認識一個人?
認識一個人啊,還真不能只從臉書認識,從LINE認識,從那人會傳的圖片或影片認識。圖片和影片很無聊,不代表那個人就很無聊。但是常常啊,因為討厭那些東西,對方就出局了,那人的其他面向沒有被你認識的機會。這也沒辦法,人之常情。除非因為特別原因,或是不得不,不得不繼續與對方建立關係,結果因此看到了令你意外的一面,哇喔,眼睛一亮。
突破同溫層,有時是好的。
2022年7月28日 星期四
人格測驗
習慣坐中間
習慣坐邊邊
會拖延
不會拖延
怕別人討厭
不怕被人討厭
能感受別人的感覺
非常可以一點點可以中間不太可以非常不可以
你是守護者
你是調停者
你是提倡者
測驗
人格測驗
測驗你是誰
「我想知道我是誰?」
但難道我不知道我是誰嗎?
每天起床就是測驗
鬧鐘要按掉幾次
會不會賴床
早餐吃很快還是很慢
你說因為有小孩無法自己決定所以不算
那麼如何與小孩相處是測驗
能不能忍受髒亂是測驗
與伴侶相處是測驗
或是
與自己相處是測驗
跟主管說話是測驗
跟同事說話是測驗
與業主說話是測驗
遇到不合理的要求是測驗
遇到為難的請求是測驗
安排工作進度是測驗
講電話是測驗
回訊息是測驗
與人應對進退是測驗
快要爆炸是測驗
解決危機是測驗
毫無人性沒人能懂爆炸難用的工作系統是測驗
選擇工作
無法選擇工作
都是測驗
選擇說
選擇不說
選擇如何說
生活就是測驗
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人格測驗
2022年7月25日 星期一
2022年7月23日 星期六
怎麼有人這麼會寫短篇小說?──艾莉絲.孟若
一天我在傍晚熨衣服時,突然想到了我生活問題的解決之道,十分簡單卻大膽。我走進客廳,對著正在看電視的丈夫說:「我覺得我應該有一間辦公室。」
這聽來多荒誕,連我自己都不禁覺得。我要一間辦公室做什麼呢?我有一個家,舒適寬敞,還有海景;家裡有地方吃睡、洗澡、約朋友談天,此外我還有座花園;家裡不缺空間。
沒錯,但我要宣告一件對我來說頗難啟齒的事:因為我是個作家。這聽起來不太對勁,太突然、虛假,至少不太有說服力。重來,我平常會寫作。聽起來好些嗎?我「試著」寫點東西。聽起來更糟,謙虛到矯情。
……我要一個寫作的地方。我旋即意識到這聽起來是過分的要求,是十分罕見的自我放縱。大家都知道,寫作只需要一部打字機,或至少一枝鉛筆,還有紙張和桌椅,這些我都有,就在臥房一隅。但現在我還想要一間辦公室。
而且說到底,我甚至不確定我要在辦公室寫什麼,或許我會只是坐在那兒盯著牆壁,但就連那樣的光景在我看來也不糟。我喜歡的其實是「辦公室」這詞聽來的感覺,帶著尊嚴和平靜,還有目的性和重要性。但我沒想到對丈夫說這些,因此我生出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詞,印象中大致像這樣:
男人可以在家工作,把工作帶回家裡,就會有一塊空間騰出來,家裡會盡可能以男人為中心調整一番,每個人都明白他在工作,沒人會期待他去接聽電話、找不見的東西、察看孩子為何哭鬧,或是餵貓,他可以把門關上。但想像一下(我對丈夫的原話),一位母親把關上,兒女知道她在門後──怎麼可以,光想到這個畫面就令人髮指;同理,一個女人兩眼出神,望向一片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女的鄉間,這在眾人眼裡也同樣違反自然。因此,家對女人而言是不同的,她不能走進家裡,利用一番,然後隨時再走出去。女人就是家本身,兩者無從切割。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辦公室〉節錄
◆
儘管我沒有小孩,我的伴侶也非常尊重我在工作時需要的安靜,但當我讀到孟若寫的這篇,當下真的可以體會那種身為寫作者的「不知如何是好」。需要空間,卻又會因為這種需求「感到不好意思」。不只因為需求感到不好意思,連說出自己在做什麼都不好意思。有次有個剛認識的朋友問起,「你們是全農嗎?」你們,指的是我跟老斌。我很快的說只有老斌,我不是。說完「我不是」,我就沒有接下去說了,我沒說自己在做什麼,好像沒有辦法很自然地說出來。接著陷入一種微妙的尷尬,我沒跟著老斌一起務農,只是偶爾幫忙,那我在幹嘛?我在家都在幹嘛?
孟若生在1931年的加拿大,我則是在2022年的台灣。相隔時間那麼久,距離那樣遠,但我對孟若所描寫的情境,非常有感。
但〈辦公室〉是一篇短篇小說,不是散文。特別提這點是因為,剛開始讀的時候,我直覺孟若在寫自己。讀著讀著,我發現這確實是「小說」──讀到後段,劇情有了轉折,結局更是出乎人意料。它不只在談女性寫作者的困境,還轉折進一個更幽微的人性──這幽微的人性是孟若小說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她的短篇小說,幾乎每一篇,都存在一種我曾經歷過的感受,我已經快忘了,讀到時才又想起。
◆
我看到麥拉和吉米走在我前面的坡上。他們姊弟總是很早上學,有時甚至得站在那兒等工友開門。此時他們緩步走著,麥拉不時會稍稍轉過身。我也經常像那樣閒晃,想跟走在後面學校的風雲女孩走在一起,又不敢直接停下來。這會兒我想到麥拉正對我做一樣的事,我不曉得該怎麼辦,我可不能被撞見和麥拉走在一起,而且我也不想。但另一方面,她那樣謙卑而期盼的轉身所帶來的虛榮並非完全沒影響到我,我無法忍住不去扮演一個專為我打造的角色,我感到一股自覺的善心,愉悅地泉湧而上,腦袋還沒想清楚便開口喊道:「麥拉,喂,麥拉,等我一下,我有餅乾傑克的焦糖花生爆米花。」她停下來,我便快步迎上去。
──〈蝴蝶的日子〉節錄
在《幸福陰影之舞》這本短篇小說集裡,有許多以小女孩或青少年為主角的小說。我每讀一篇便忍不住驚訝──「她怎麼有辦法將那些細微的心理狀態寫得那樣深刻?」我的意思是,她的其他本短篇小說集,如《感情遊戲》、《出走》,多半以中年婦女為主角,而小女孩和青少女離自己那樣久遠,當她開始提筆寫作的年紀,她怎麼還想得起來,還能寫出屬於小孩的那種非善非惡的心理狀態,那種小孩才會有的行為,小孩才說得出來的話?
◆
我回家三個星期了,不太成功。雖然我和美德一直開心地說這次可以親密相聚這麼久真好,但結束時兩人大概都會鬆一口氣。我們之間出現沉默時總是不自在,我們總是笑個不停,而我害怕──很可能我們都害怕──當道別的時刻來臨,我們若不快快親一下對方,熱切而嘲弄似地捏捏對方的肩,就得直視那片隔在兩人之間的荒漠,承認我們姊妹不僅互不關心,其實內心深處根本排拒著彼此,而我們煞有其事分享的那段過往,其實也不是真的分享,我們各自眼紅地將過去據為己有,暗自覺得是對方變了,喪失了資格。
──〈烏得勒支的和平〉節錄
這麼直接,開頭我就被打到。整篇讀下來,我無法不覺得這就是孟若親身經歷的改編,若非如此,她怎麼有辦法將那些無法定義是非對錯的東西寫得那樣令人「共感」。共感,指的不是有同樣的經歷,而是有類似的感受。
◆
讀完《幸福陰影之舞》好幾天了,早就想書摘,卻遲遲沒時間。今天,覺得再不寫可能就不會寫了,但我實在太喜歡這本了,最後一篇與書名同名的〈幸福陰影之舞〉也非常厲害,讀完會嘆氣。
怎麼有人這麼會寫短篇小說?我好嫉妒,也好幸福。
2022年7月16日 星期六
非常律師禹英禑
最近也看起了《非常律師禹英禑》(基本上無雷,但很擔心被微雷的請自己略過)。禹英禑實在是太可愛了,人可愛行為可愛,連那些對當事人而言是障礙的動作都好可愛,忍不住擔心大家會不會以為自閉症都很可愛?還好我多慮了,第三集透過另一個重度自閉症者凸顯了患者與其家庭的困境,也呈現了禹英禑其實也有困境,特別是小時候,她與她的爸爸還沒有建立起連結的時候。
親情連結,在大部分情況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東西,但對某些人來說並不是。之前讀《背離‧親緣》時,讀到〈自閉症〉一章實在令我喘不過氣,雖說自閉症的光譜極廣,輕度與重度,行為的呈現也各有不同,但當中我覺得最令人感到辛苦的是──某些自閉症者感受不到「對自己來說重要的人」。
「有個病人,二十五歲,是數學天才,他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他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但他對母親說:「人為什麼需要母親?人為什麼需要家庭?我不懂。」他母親後來說:「他每一件事都用理性來思考,他不懂我聽了會有什麼感受。」英國的精神分析師米契說:「在極端的案例中,『你不存在』這件事殘酷得讓你喘不過氣。這不是指你被抹去了,而是你從來就不存在,根本不必被抹去。兩方的靈魂毫不對等:你認得對方,但對方並不認得你。」
──《背離‧親緣》上,〈自閉症〉
看《非常律師禹英禑》時,雖然覺得太可愛,但也可以明白為何要讓她如此可愛,劇情也正向光明,包括禹英禑長大後還是與父親建立了連結,雖然總是從自己的角度去解讀他人喜歡的東西;包括她交到了朋友,雖然最初的出發點是「跟這個人在一起我就不會被欺負」。可愛加光明,輕盈的翅膀可以帶著沉重的身體飛起,大眾才看得下去,也才能看到自閉症者的特質,而不只是障礙,不得不說這劇本真是很會寫。
但如果真的想了解自閉症,非常推薦閱讀《背離‧親緣》上冊〈自閉症〉一章,光譜之廣,訪談之深,安德魯‧所羅門真是令人欽佩的作者。
2022年7月6日 星期三
我們不是來提倡墮胎的,我們是來提倡女性權利
利用中午吃飯的時間配Netflix,把《羅訴韋德案:女權與政治》分幾次看完了,還不錯的紀錄片,把墮胎議題在美國的脈絡補完(但必須承認小小複雜)。
看完才知道,原來共和黨以前並不反對墮胎,雷根跟老布希都曾支持女性「選擇權」。而在羅訴韋德案做出墮胎合法判決的大法官,也不是因為他們有多支持女權,只是因為在當時墮胎還不是黨派議題,還沒成為選舉操作籌碼,他們視墮胎是醫療問題與社會問題,並尊重當事人的選擇與隱私權。
還有,原來在羅訴韋德案之前,美國沒有那樣大規模勢力想阻止女性墮胎,但當法庭一說「你有權做這個決定,你能定義你的人生,不是宗教。」保守派福音派就不能接受了。他們以一連串的行動逼迫提供墮胎服務的診所關門,並以龐大勢力介入選舉(原來他們也是社運人士!超會搞社運!)從那之後墮胎議題變成選舉議題,若想獲得保守派福音派的選票,候選人便要表明支持「生命權」。
與其說反墮胎者支持生命權,不如說他們不願意讓女性決定自己的生命。事實上他們根本不願意面對女性有可能面臨必須墮胎這一困難選擇的處境,他們假裝沒有墮胎診所就沒有墮胎,假裝只要有法律禁止墮胎就沒有墮胎;他們以保護生命與女性身體健康為包裝,將女性推入無所支持的深淵。
但墮胎一事根本就不是「生命權」與「選擇權」的對立。尊重女性有墮胎的權利,給予足夠的資源讓他們做選擇,而非被迫選擇;相信他們自己能夠做這項決定,才是真正的尊重生命。
引述一段羅訴韋德案的辯護律師──莎拉華盛頓的發言:
「我們不是來提倡墮胎的,我們不要法庭判斷墮胎是好事,或是在某種狀況下是好事。我們是來提倡女性權利,讓她自己決定是否中止妊娠。」
「我們不想認定人命何時開始,沒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答案,並沒有法律標準決定『胚胎何時會變成人』。所以問題是誰能做這個決定,是女性?還是政府?我的立場總認為不該是政府。」
2022年7月2日 星期六
若冤案無解,又為何要解?──我讀《流氓王信福》
我第一次知道「流氓王信福」,是因為張娟芬以此題入圍台北文學獎年金計畫。當時我沒聽過王信福,也不曉得這究竟是個什麼事件。讀了計畫內容後,知道張娟芬想寫一件陳年冤案──冤案主角王信福,1990年被控教唆殺警後逃亡至中國,2006年被捕,2011年在沒有確切事證僅憑證人供詞的情況下,判決死刑定讞,待死中。
不過,雖然我很欣賞張娟芬,但我對自己尚未完全明白的事情,皆抱持保留態度。我不會因為張娟芬說王信福案是冤案,就馬上相信這是冤案;我要聽到她怎麼說,她如何判斷,提出了哪些證據證明王信福被冤枉。所以我在等,等「流氓王信福」完稿成書,在瞭解來龍去脈後,我才知道該如何判斷。
但書還未出版前,張娟芬先拍了電影。
三月中,電影《審判王信福》在台北光點華山有場公益播放,我去看了。先說我在觀影時當下的直覺反應──由於《審判王信福》並不是紀錄片,它是一部改編自王信福案的劇情片,電影將重點擺在法庭上的審判,簡單來說,它以模擬法庭的形式來呈現王信福案的爭議點。這樣的表現形式,坦白說我剛開始並無法「百分之百」相信這部電影。因為它是改編,而我對原案一無所知,所以我無法判斷編劇改編的程度。我的意思並不是覺得編劇會造假,而是──「會不會這是因為要救援王信福,所以模擬法庭呈現了對王信福有利的一面?並突顯檢警在辦案時的荒謬?」證人說自己當初的證詞是因刑求被脅迫是真的嗎?兇槍上找不到王信福的指紋,但法院卻推說指紋可能是因為被人擦拭或年代久遠所以驗不出來──如此違反「無罪推定」的說法,司法真的那麼離譜嗎?關鍵證人傳喚不到,法官可以講一句「我也沒有辦法」就算了?以及,《審判王信福》的爭點若如此明顯,那為何法官會做出死刑定讞?
當天電影結束後雖有QA時間,但因為我問題太多,而且有些還在腦袋中轉著,尚未理出頭緒,所以我沒在當下發問。我想,或許我讀完《流氓王信福》後就能解惑?而當我讀完書,我發現確實解惑了,但解惑的同時也帶來更大的疑惑──我們的司法是為了找出「真相」?還是只是想「破案」?找到一個名字一個人,有人頂罪為此負責就好,不管偵辦過程中有多少瑕疵與漏洞?我發現,我想像中司法所能做到的公平正義,與現實有著一大段距離。
--原來那是個沒有「無罪推定概念」的年代--
並不是我有多相信司法,但我原本以為無罪推定是基本原則,是司法審判過程中最起碼該遵守的線。後來我才知道我認為的理所當然,在從前的司法中並不存在。「沒有找到證據不表示你沒有做」──本案的關鍵證據兇槍送驗後並無發現王信福的指紋,但法官卻在判決中說:「不能僅以扣案槍枝並未鑑出被告指紋,即否定被告有交槍予陳榮傑之事實」……
以邏輯來說,這是推論,而非「事實」;該推論僅代表「他並非沒有拿過此槍的『可能』」,但無法以此作為「他拿過此槍的『事實』」。
我不是念法律的,但以邏輯來看,法官將「可能」與「事實」混淆了。法官不能僅憑「可能」來建立「事實」。要說「可能」,除非可能性為零,否則每件事都有可能。所謂嫌疑,代表有可能,但也僅僅是可能,必須透過證據來證明「那個可能」「為真」,否則就該排除,落實無罪推定。
另外,法官也犯了因果關係上的謬誤──他先認定王信福有交槍給陳榮傑的「事實」,然後再說不能因為未驗出指紋就否定此事實──事件的因果邏輯關係,似乎顛倒了。
--原來那是個僅憑「供述性證據」就能將人判死的年代--
不過,既然沒有物證證明王信福交槍給陳榮傑,那麼法官何以做出如此判斷?法官靠的是「供述性證據」──陳榮傑在警詢筆錄中說,「是王信福叫我開槍的。」可是,陳榮傑每次在筆錄中說的都不太一樣。看到這裡,直覺反應是「那叫陳榮傑上法庭跟王信福對質啊」。但很抱歉沒辦法,因為陳榮傑在審判後很快就死刑定讞執行槍決。
看電影時感覺很荒謬,覺得法官怎麼可能單憑證人供詞就將人判死?而讀了書之後才知道,原來這在從前的司法審判中很常見。就算我不是讀法律的,但看過法庭電影也知道證人在法庭上作證要發誓(所謂的具結,如果說謊就有偽證罪);應該要讓檢辯雙方交叉詰問;除此之外法庭也該公開審理,讓證人可按照自由意志說話(免除被脅迫的疑慮),然後法官也可據此判斷證人的可信度──但這些,在王信福的審判中都沒有。
--原來檢警並不如我以為的,抽絲剝繭的辦案--
王信福案沒做無罪推定,僅憑供述性證據定罪,除此之外,警方還憑成見辦案。
王信福很衰,他只是那天唱歌唱得不爽,罵了聲「幹你娘」,就被認為是殺警的嫌犯。沒辦法啊,誰叫他罵得那麼大聲,全場的人都聽到了。當警方詢問當天槍擊之前有沒有什麼異狀,卡拉OK的服務生和酒客都提到聽到有人罵「幹你娘」。但罵幹你娘跟槍擊殺警的關係是什麼呢?從張娟芬爬梳卷宗梳理證人證詞的結果,發現那當中並無因果關係,但在警察認為兇手陳榮傑一定有「共犯」的前提下,在誘導式詢問與威脅下,證人的供詞從「王信福唱歌不爽罵幹你娘」,被扭曲成「王信福在罵警察」,再變成「王信福命令陳榮傑開槍」。
張娟芬在書中提到,許多冤案是因為辦案人員的「隧道視野」──一旦有了成見之後,就只看得到前方發光的那一小點,其他什麼都看不見。但其實只要像張娟芬一樣,將不同證詞交叉比對,或同一人的證詞前後比對,就能篩出證詞的可信度。
--「外面的人都不是這樣想」……但我開始這樣想了--
其實看完電影後我還有個疑問──「如果真相如電影所演,那王信福案有沒有重啟調查的機會?」讀了書之後才知道,儘管王信福案在2006年開庭再審,當時證人證詞對王信福有利,但因距離案發年代久遠,法院無法評估其真實性而不採信。而除了證人證詞外,目前尚無新事證,王信福案若想翻案,張娟芬說:「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此題無解。」
此題無解,又為何要拍攝電影《審判王信福》?為何要爬梳所有卷宗,理清案情爭點?為何要寫一本厚達四百頁的《流氓王信福》?
前面提到警方辦案時若陷入隧道視野,就無法一一檢視辦案過程所出現的證據。那麼我們一般人呢?我們是否也可能陷入「隧道視野」?「那人已經死刑定讞,一定有罪。」「他說他被冤枉,但為什麼不是別人而是他?他自己一定也有問題。」「又是冤案?哪來那麼多冤案?」一般人可能沒有資源與能力抽絲剝繭調查案件,但如果已經有人將案情的來龍去脈與爭點都整理好,並提出一套分析證據結構的方法,我們是否願意先排除對死刑犯的偏見,去了解王信福案的審理過程,再下最後的判斷?
王信福說,「外面的人都不是這樣想。」不是這樣想是什麼意思?不認為王信福無罪、無辜?老實說剛開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想,因為知道得太少,但當我知道了這些,當張娟芬幫我把證據梳理好擺在我的面前,我開始這樣想了。
──刊載於《幼獅文藝》第822期,202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