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有人坐在椅上
本來有人坐在桌旁
本來有人給一盆花澆水
本來有人從書本中抬起頭來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那個隨著音樂起舞的人
那個喜歡吃麵條的人
那個喜歡喝白開水的人
那個戴頂帽子擋陽光的人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變成一個分水給陌生人喝的人
變成一個為信仰而停止進食的人
變成一個含著眼淚勸告武警的人
變成一個為朋友擋去子彈的人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輾成了碎片
撞成了彈孔
吹成了風砂
撒成了灰塵
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變成了你我身畔永遠的影子
變成了我們每日的陽光和空氣
變成了生活裡的盆花和桌椅
變成了我們總在讀著的那本書
──也斯
2014年9月30日 星期二
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
選擇
這幾天看著香港的新聞,又讓我想到「選擇」這個問題。
我一直認為出自本能的選擇不是選擇,比如在想睡覺的時候「選擇」睡覺,在肚子餓的時候「選擇」吃飯,我不認為這種叫做選擇,只能說是反應而已。這樣舉例好了:某個男人看到一張裸女照片,雞雞忍不住翹起來,儘管那個翹著雞雞的男人完全沒有要跟那個女人睡覺的意思,但雞雞就是翹起來了。這種時候我們總不會說:「那個男人『選擇』讓他的雞雞翹起來。」我們不會這樣說,因為他根本沒得選。
我也認為在有限的選擇內選擇,不是選擇,特別當那有限的選項中,完全沒有自己想要選的。比如在一個不愛吃甜食的人面前,擺了巧克力、蛋糕、紅豆湯和冰淇淋,然後問他:「你想吃什麼,隨便選!」或是更誇張一點的例子:在你面前擺了大便跟廚餘,然後問你:「你想要選什麼當晚餐吃?」
用這種例子來說明「選擇」,好像有點太小看人了,「搞什麼?我當然知道那種不算選擇啊!」問題是,這樣的例子發生在「選舉」這件事上,許多人倒是覺得莫可奈何。
「政府那麼大,他要什麼選什麼我就選什麼,不然怎麼辦?難道要硬幹嗎?」
這一代莫可奈何,第二代莫可奈何,到了第三代就理所當然了。
「政府給我們選什麼我們就選什麼,不是一直都是這樣嗎?政府推舉的人不會有錯,政府總是為我們百般設想。」
前面不是說了本能嗎?如果當「服從權威」這件事變成了人的本能,那麼對那個人來說,就沒有選擇這件事了,他只是在做看起來像是選擇的行為而已。
不要覺得不可能。在打罵教育中長大的小孩,幾乎總是會服從大人的權威,對他們來說,服從幾乎是一種本能了;他們幾乎想不到,除了服從之外,還有對抗的可能。
為了不讓這些不算選擇的選擇假象繼續下去,香港正在努力。
不過坦白說,台灣並沒有比較好。年底就要選舉了,看看我們的候選人;我現在住台東,看看台東縣長候選人好了。我們真的有選擇嗎?
相關文章:香港人給台灣人的10個快問快答:中國都給香港「普選」了,為什麼學生還要罷課?
我一直認為出自本能的選擇不是選擇,比如在想睡覺的時候「選擇」睡覺,在肚子餓的時候「選擇」吃飯,我不認為這種叫做選擇,只能說是反應而已。這樣舉例好了:某個男人看到一張裸女照片,雞雞忍不住翹起來,儘管那個翹著雞雞的男人完全沒有要跟那個女人睡覺的意思,但雞雞就是翹起來了。這種時候我們總不會說:「那個男人『選擇』讓他的雞雞翹起來。」我們不會這樣說,因為他根本沒得選。
我也認為在有限的選擇內選擇,不是選擇,特別當那有限的選項中,完全沒有自己想要選的。比如在一個不愛吃甜食的人面前,擺了巧克力、蛋糕、紅豆湯和冰淇淋,然後問他:「你想吃什麼,隨便選!」或是更誇張一點的例子:在你面前擺了大便跟廚餘,然後問你:「你想要選什麼當晚餐吃?」
用這種例子來說明「選擇」,好像有點太小看人了,「搞什麼?我當然知道那種不算選擇啊!」問題是,這樣的例子發生在「選舉」這件事上,許多人倒是覺得莫可奈何。
「政府那麼大,他要什麼選什麼我就選什麼,不然怎麼辦?難道要硬幹嗎?」
這一代莫可奈何,第二代莫可奈何,到了第三代就理所當然了。
「政府給我們選什麼我們就選什麼,不是一直都是這樣嗎?政府推舉的人不會有錯,政府總是為我們百般設想。」
前面不是說了本能嗎?如果當「服從權威」這件事變成了人的本能,那麼對那個人來說,就沒有選擇這件事了,他只是在做看起來像是選擇的行為而已。
不要覺得不可能。在打罵教育中長大的小孩,幾乎總是會服從大人的權威,對他們來說,服從幾乎是一種本能了;他們幾乎想不到,除了服從之外,還有對抗的可能。
為了不讓這些不算選擇的選擇假象繼續下去,香港正在努力。
不過坦白說,台灣並沒有比較好。年底就要選舉了,看看我們的候選人;我現在住台東,看看台東縣長候選人好了。我們真的有選擇嗎?
◆
相關文章:香港人給台灣人的10個快問快答:中國都給香港「普選」了,為什麼學生還要罷課?
2014年9月27日 星期六
「為什麼夜晚要把國旗降下來,我不明白那理由。」
他這麼說著。
我說,就跟晚上要睡覺一樣啊,
為了明天早晨要醒過來。
「但是,為什麼每天都要把國旗升上去呢?」
「是為了夜晚要降下來。」
(「為什麼夜晚要把國旗降下來,我不明白那理由。」這句話出自《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
我說,就跟晚上要睡覺一樣啊,
為了明天早晨要醒過來。
「但是,為什麼每天都要把國旗升上去呢?」
「是為了夜晚要降下來。」
(「為什麼夜晚要把國旗降下來,我不明白那理由。」這句話出自《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
2014年9月26日 星期五
朱槿花 (孫維民)
我注視著越過人家的圍牆
一排花瓣似乎永遠捲合的朱槿
我注視著,並且懷疑
那些深紅的花瓣是否終於打開
在我所不知道的時刻?
我懷疑著,並且想到
下午才寫給你的一封信
那是文字搭建的天塔,以及
描述我的痛苦和哀傷
此刻的我後悔寄出的
一封信。因為一個疲憊的下午
終於讓我了解:字語
可以如何褻瀆崇高的痛苦
膚淺深沉的哀傷──
我思索著,並且傾聽
一排無聲的朱槿像一首歌
心想那些花瓣永遠不會打開了
彷彿句句未說的,真實的言辭
彷彿發自深紅的喉嚨
千言萬語層層捲合的靜默
──孫維民,〈朱槿花〉, 《拜波之塔》
一排花瓣似乎永遠捲合的朱槿
我注視著,並且懷疑
那些深紅的花瓣是否終於打開
在我所不知道的時刻?
我懷疑著,並且想到
下午才寫給你的一封信
那是文字搭建的天塔,以及
描述我的痛苦和哀傷
此刻的我後悔寄出的
一封信。因為一個疲憊的下午
終於讓我了解:字語
可以如何褻瀆崇高的痛苦
膚淺深沉的哀傷──
我思索著,並且傾聽
一排無聲的朱槿像一首歌
心想那些花瓣永遠不會打開了
彷彿句句未說的,真實的言辭
彷彿發自深紅的喉嚨
千言萬語層層捲合的靜默
──孫維民,〈朱槿花〉, 《拜波之塔》
2014年9月24日 星期三
殺人的人
被媒體寫得像變態的
殺人的人
不是什麼別的生物
一樣有著兩隻手、兩條腿
一個頭顱
一顆心臟的人
一樣曾是嬰兒
一樣有童年
一樣一年長一歲
一樣難過會哭開心會笑
當然也一樣會死
不曉得是哪裡出了差錯
或者也沒有所謂出差錯這回事
人就是這樣一件事一件事累積起來的
長成現在這個樣子
十五年前的他並不曉得自己現在殺了人
不會曉得
我們可以坐多拉A夢的時光機回到過去
說你殺了人所以我們要矯正你嗎
要矯正什麼呢
矯正哪一件事情呢
還是乾脆先把這個人殺了
那麼另一個人就不會死
那個殺人的人正站在教室的講臺前
接受老師的表揚
「你們大家都要向他看齊」
殺人的人想著自己美好的未來
那美好的未來包括成為一個殺人的人嗎
(記張彥文情殺與媒體現象)
殺人的人
不是什麼別的生物
一樣有著兩隻手、兩條腿
一個頭顱
一顆心臟的人
一樣曾是嬰兒
一樣有童年
一樣一年長一歲
一樣難過會哭開心會笑
當然也一樣會死
不曉得是哪裡出了差錯
或者也沒有所謂出差錯這回事
人就是這樣一件事一件事累積起來的
長成現在這個樣子
十五年前的他並不曉得自己現在殺了人
不會曉得
我們可以坐多拉A夢的時光機回到過去
說你殺了人所以我們要矯正你嗎
要矯正什麼呢
矯正哪一件事情呢
還是乾脆先把這個人殺了
那麼另一個人就不會死
那個殺人的人正站在教室的講臺前
接受老師的表揚
「你們大家都要向他看齊」
殺人的人想著自己美好的未來
那美好的未來包括成為一個殺人的人嗎
(記張彥文情殺與媒體現象)
2014年9月21日 星期日
第一次淹水就上手
看這個標題就知道淹水情況應該還好,把家裡的水掃完之後還有閒情雅緻上網。不過老實說水剛進來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看著水從廚房後門下的縫口流進來,瞬間漫過廚房地面,往更低的客廳地面流過來。
第一個想到的是「X!廚房跟客廳之間怎麼沒有門檻」,第二個是「還好客廳和臥室之間有門檻」,第三個是「流進客廳的水就快要漫到書架那啦……」,第四個是「水這種東西它要是想要流,你怎麼檔都沒辦法……」
大概是因為沒想過水會流進來,所以一開始只想著要拿什麼東西來擋,可是沒有啊,沒有沙包(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颱風天要準備沙包了……),我們家沒有任何可以擋的東西。老斌說趕快打電話問小四能不能來幫忙,我想說叫他來是要幫什麼呢,叫他帶沙包嗎?可是他們家應該也沒有那種東西呀!不過我還是打了電話,話講得不清不楚,水淹進來了,現在要淹到客廳了;小四問從哪裡淹進來的?我說從廚房後門。「那你們現在趕快去挖一條溝,把水排出去。」小四說。
於是我在家裡掃水,老斌去後院挖溝。挖了一陣,老斌進來,「溝挖好了,水還有再進來嗎?」我看了看後門,呼,水真的沒有再進來了。
不過,約莫短短十幾分鐘所淹進來的水,就讓我們掃了兩個小時。
淹水心得:
1.後門要有排水溝保持暢通。門縫要擋起來。
2.廚房和客廳之間有門檻就更保險了。
3.書架全部墊高。
4.床底下不要擺任何物品。
5.感謝這是我們可以處理的淹水,不是無法處理的淹水。
對了,看到這篇文的我媽不用擔心,只是淹水而已,而我也只是記錄而已。
掃了兩個小時後,水終於漸漸退了。
2014年9月19日 星期五
20140919.蘿蔔發芽了(可是,那個灑在土壤上紅紅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啊!)
嗯,還是要再說一次,已經互相了解,有默契的小孩真的很好相處。還沒有彼此了解、沒有默契的小孩,要讓他們在滿腦子都是「玩」的年紀,好好地聽你講話,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還有,我真的很不喜歡小孩來告狀啊(雖然我小時候也會告狀)!可以不要跟我告狀嗎?這是你與同學之間相處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但是,是不是沒有人教小孩如何解決衝突呢?所以他們只好告狀?還是說「告狀」只是一種情緒發洩?看來下週我第一件要跟小孩討論的事是關於「告狀」這件事。這可要好好來想一想。(補充說明:「告狀」與真的有事要請人幫忙解決不同。「告狀」是:「老師你看他......」、「老師他一直弄我」、「老師XXX都XXXXXX.......」,這類叫做「告狀」。)
糟糕,這個記錄怎麼寫得像是在抱怨呢?好啦其實除了三年級小孩會忍不住尖叫、總是衝來撞去、總是喜歡告狀之外,其他部份都還算好玩。今天進學校前,我先繞去小菜園看了一下,喔!9月12日播種的白玉蘿蔔都發芽了!這應該歸功於颱風靠近下的雨吧!
我問三年級小孩,這個禮拜瑞源有下雨嗎?小孩說有。我問下幾天呢?有的說四天,有的說三天,有的說兩天,有的說一天(是在玩四三二一的遊戲嗎?)我問你們有去澆水嗎?大家都說有。我說,那你們一定看到蘿蔔發芽了吧!蘿蔔芽長什麼樣子呢?這一問,沒有小孩答得出來。
我畫圖給他們選:1.鋸齒狀。2.愛心狀。3.圓形。4.針葉狀
結果有八個小孩選了4.針葉狀,兩個小孩選了2.愛心狀。
我說,你們都選好了喔。好,我們來去小菜園看看到底是什麼形狀吧!
來,你看,是愛心形狀的喔!
看不清楚的話,再來一張近的。
我發現蘿蔔芽有些徒長,莖長得太長都垂倒了。所以今天的重點是帶小孩培土。
有些小孩很認真地培土,但更多小孩很認真地玩水。
再來一張更近的。這紅紅的東西該不會是肥料吧?長得有點像魚飼料?不管是肥料還是魚飼料,我們不需要這種東西呀!到底是誰「幫」我們灑的啊!
好吧,希望下週可以知道那位「好心人士」是誰,請他不用再那麼好心了。
如果沒有意外,下週蘿蔔的本葉應該就長出來了。今天還不及疏苗,所以下週要疏苗、培土,還有落葉覆蓋。嗯,下週小孩有得忙了。
替代能源的夢
昨晚夢很多,我就想該不會說了一個晚上的夢話。果然老斌說,「你昨天晚上一直講夢話,好吵。」
到底講了什麼,夢話咕ㄋㄨㄥ咕ㄋㄨㄥ的,所以也聽不懂。不過我記得整個長長的夢幾乎都是在「製作東西」。
製作什麼東西呢?
昨天去荒野聽了朱士杰講替代能源。朱士杰很有趣,感覺像是一個喜歡做實驗的大小孩,風力、水力、太陽能、沼氣什麼方法都試,當然也有很多失敗的心得。
大概是昨天聽他講了一長串吧,又看了好多照片和資料,結果晚上就做起自己在製作什麼東西的夢了。不過到底做了什麼,完全想不起來了呀!
朱士杰不是理工出身,但他很會找資料,而且有一種「因為是素人所以不怕做錯」的衝勁,反正也不算花什麼大錢(他會找相對來說省錢的方法),找到材料就來試試看就對了。
簡單整理一下,以朱士杰的實作經驗,目前家庭式的風力發電完全不可行,因為平均至少要12級以上的風才能有效發電。12級的風有多大呢?大概就是颱風等級的風吧!
水力發電有成功有失敗的,但主要是看地勢條件。「但水力發電比我想像中的吵,如果旁邊有住人,就需要解決噪音的問題。」朱士杰說。
沼氣感覺是可行的,不過當然也要有條件,比如動物或人的大便,至少要有夠多的大便才行吧!如果是一個人獨居,哪來夠多的大便呢?當然也要有好的設計。
那麼太陽能發電呢?太陽能本身當然沒有問題,要考慮的是太陽能板製程所造成的汙染,維護與維修有哪些問題需要注意、以及太陽能板壽命結束後該如何回收處理。
聽起來沒有任何一種能源是又方便又有效又完全沒有問題的。嗯,是,我覺得現實就是這樣,在使用能源這件事上,我覺得要先有這樣的覺悟;了這樣的覺悟,才會不辭辛勞地繼續不斷思考與實驗,對環境影響負荷低的能源使用。
而更現實的現實是,目前就是沒有「完美的」的替代能源,但難道這樣我們就不使用能源嗎?也不是這樣說。我覺得朱士杰很棒的一點是,他四處去看別人怎麼做,然後自己實驗,不斷嘗試可能性;做不起來或效能不好或根本沒辦法用的時候,「啊,原來這樣不行呀……」然後繼續嘗試。
老實說,這樣的實驗精神我完全沒有,感覺上要很愛玩又不怕失敗才有辦法。那我們能做什麼呢?如果我們有「能源並非永不匱乏」以及「沒有一種能源使用是完美的」的想法,至少我們就不會自大,自以為某一種能源發展可以解決人類生活的所有問題。至少我們會開始想辦法節能,而所謂的節能是不浪費,而這不只是電價問題,不只是錢的問題。
到底講了什麼,夢話咕ㄋㄨㄥ咕ㄋㄨㄥ的,所以也聽不懂。不過我記得整個長長的夢幾乎都是在「製作東西」。
製作什麼東西呢?
昨天去荒野聽了朱士杰講替代能源。朱士杰很有趣,感覺像是一個喜歡做實驗的大小孩,風力、水力、太陽能、沼氣什麼方法都試,當然也有很多失敗的心得。
大概是昨天聽他講了一長串吧,又看了好多照片和資料,結果晚上就做起自己在製作什麼東西的夢了。不過到底做了什麼,完全想不起來了呀!
朱士杰不是理工出身,但他很會找資料,而且有一種「因為是素人所以不怕做錯」的衝勁,反正也不算花什麼大錢(他會找相對來說省錢的方法),找到材料就來試試看就對了。
簡單整理一下,以朱士杰的實作經驗,目前家庭式的風力發電完全不可行,因為平均至少要12級以上的風才能有效發電。12級的風有多大呢?大概就是颱風等級的風吧!
水力發電有成功有失敗的,但主要是看地勢條件。「但水力發電比我想像中的吵,如果旁邊有住人,就需要解決噪音的問題。」朱士杰說。
沼氣感覺是可行的,不過當然也要有條件,比如動物或人的大便,至少要有夠多的大便才行吧!如果是一個人獨居,哪來夠多的大便呢?當然也要有好的設計。
那麼太陽能發電呢?太陽能本身當然沒有問題,要考慮的是太陽能板製程所造成的汙染,維護與維修有哪些問題需要注意、以及太陽能板壽命結束後該如何回收處理。
聽起來沒有任何一種能源是又方便又有效又完全沒有問題的。嗯,是,我覺得現實就是這樣,在使用能源這件事上,我覺得要先有這樣的覺悟;了這樣的覺悟,才會不辭辛勞地繼續不斷思考與實驗,對環境影響負荷低的能源使用。
而更現實的現實是,目前就是沒有「完美的」的替代能源,但難道這樣我們就不使用能源嗎?也不是這樣說。我覺得朱士杰很棒的一點是,他四處去看別人怎麼做,然後自己實驗,不斷嘗試可能性;做不起來或效能不好或根本沒辦法用的時候,「啊,原來這樣不行呀……」然後繼續嘗試。
老實說,這樣的實驗精神我完全沒有,感覺上要很愛玩又不怕失敗才有辦法。那我們能做什麼呢?如果我們有「能源並非永不匱乏」以及「沒有一種能源使用是完美的」的想法,至少我們就不會自大,自以為某一種能源發展可以解決人類生活的所有問題。至少我們會開始想辦法節能,而所謂的節能是不浪費,而這不只是電價問題,不只是錢的問題。
2014年9月17日 星期三
20140912.帶小孩種菜
寫記錄有時需要衝動。比如,「今天下課回家後就來寫。」可惜,上週五我沒有那樣的衝動。今天是禮拜三了,再兩天就禮拜五了,我像是該交作業卻還沒寫的小孩,「好吧,今天來寫。」
第一件事是翻照片。
現在的四年級,也就是之前上過一學期的那批三年級生,幾乎都很愛拍照,每次上課都會有小孩來跟我借相機。這學期我藉借相機給他們之名,行記錄之實,「拍照記錄這件事,乾脆就交給小孩好了。」由於每個小孩都想拿相機,於是我們排了個表,每次兩個小孩。這樣剛好,我也可以知道究竟那些很厲害的照片到底是誰拍的。
這學期的重頭戲是帶小孩種白蘿蔔。本來是想帶小孩去銘孝的田種菜,我跟學校提了這個想法,校長就說學校後門剛好有塊地可以讓小孩種菜。真是太好了,我又問,那三年級跟四年級可以分開上課嗎?一次二十個小孩我實在顧不來。沒想到竟然也可以,太好了。
四年級是舊小孩了,說起話來有些默契,跟他們談事情也比較能好好地講道理。三年級是新小孩,雖然我們還在彼此認識的階段,但他們似乎查覺到我是一個不太會管他們的大人,下課時間馬上就撲上來,「來玩,老師我們來玩」。
結果我的回答是:「我剛剛講好多話喔,我好渴,我想休息一下。」
帶小孩種菜,我從「我們要在哪裡種菜」開始。「我跟我男朋友去年才搬到鹿野。我們沒有自己的地,也沒有錢買地。不過很幸運,有朋友借我們地讓我們種菜。」我這樣跟小孩講,三年級小孩馬上說,「老師,那你來我們家種,我們家的地給你種。」
出發點不同,所以對待種菜這件事的態度,應該也會很不一樣。對小孩來說,種菜對他們來說是件什麼樣的事呢?對三年級小孩來說,種菜對他們來說就像是出去玩,一走出校門就到處跑,拿到花灑還沒撒種就要澆水,才曬了一會太陽就說好熱好熱。
四年級小孩呢?我跟四年級小孩說這學期我們來種白蘿蔔吧!他們說我們二年級就種過xxx了(我忘記他們講什麼了....),一付興趣缺缺的樣子。但當我拿出還沒有剝殼的白蘿蔔種子時,本來坐得很遠的小孩就靠過來。
「你們有看過嗎?」
「沒有。」
「蘿蔔種子本來是在裡面的喔!」
「是喔!」
「想剝剝看嗎?」
四年級小孩去種白蘿蔔的時候,已經三點四十分了。一個小女孩說射箭隊的教練來了,我要去練習了。我說,可是我們還沒有種耶,等我們種完,你再去練習好嗎。小女孩想了一下,說好。
小孩好像只要出了校門,只要碰到水,就回不了家。幾乎每個拿到花灑的小孩都想要澆水。好好笑,種子都還沒灑澆什麼水呢?所以重點根本不是澆水而是玩水嘛!
我帶小孩先挖淺淺的溝,然後一個巴掌大的距離,丟一兩顆種子。有些小孩很小心地丟,有些小孩很豪邁地灑。
「種子都被你丟到外面去了啦,好可憐......」
「這個沒有覆到土,我們幫它一下.....」
「水已經夠多了,再多就要溺死了......」
「白玉蘿蔔大概五到六天就會發芽。播種後如果沒有下雨,需要有人來幫它們澆水。明天就是禮拜六了,有沒有人明後天可以來幫蘿蔔澆水呢?」
三年級和四年級都有小孩自告奮勇說要負責澆水:
「老師,明後天我來澆水。我禮拜一到禮拜五也可以澆水!」
「禮拜一到禮拜五讓給別的同學澆啦!」
九月的下午太陽還是有點熱,還好喊熱的小孩不算多。還算順利地灑了第一批白玉蘿蔔種子;前兩天下了一場雨,應該會發芽長大吧。
農會借給學校種菜的地。我本來打算帶小孩從整地開始(至少讓他們看到整地的過程),可惜上課前兩天校長來了電話,說地整好了。總共有七條畦,最左邊那條給四年級小孩種,左邊第二條給三年級小孩。其他條畦是學校食農課程用地。
這是三年級小孩,在洗腳。由於三年級小孩沒有負責拍照的同學,而我也沒有空著的手可以拍照,所以記錄只有這兩張照片。
以下是四年級小孩拍的照片。9月12日拍照的小孩是潘子賢和彭程益,最後潘元皓好像也有拿到相機。
小孩挖溝,準備播種。
要小孩正經地挖溝是不可能的。
要小孩正經地種菜是不可能的。
播種。
覆土。
澆水。
接下來要觀賞兩張小孩拍的,我覺得很厲害的照片。被拍的小孩是潘子賢,那麼拍攝者應該是彭程益或潘元皓了。
2014年9月16日 星期二
更年期
所謂的更年期是
從小就開始的
小孩三歲到四歲
身體明明還很小但裡面的靈魂突然迅速長大
便面臨了第一次的更年期
她不明白自己怎麼了
她的母親也不明白
從那之後更年期便
隨著年紀
隨著體內的什麼而更替
不定期、無預警地來臨
小學三年級到四年級是第二次
國中一年級是第三次
高中一年級是第四次
大學一年級是第五次
第六次是讀第二間大學的一年級
之後間隔開始拉長
第七次是第六次的七年後
老實說她也搞不清楚現在究竟是第幾次
只知道更年期總是在更年的時候出現
儘管之前經歷過那樣多次數的更年
每次更年
都還是像
第一次更年
更年很累
但總會過去(?)
從小就開始的
小孩三歲到四歲
身體明明還很小但裡面的靈魂突然迅速長大
便面臨了第一次的更年期
她不明白自己怎麼了
她的母親也不明白
從那之後更年期便
隨著年紀
隨著體內的什麼而更替
不定期、無預警地來臨
小學三年級到四年級是第二次
國中一年級是第三次
高中一年級是第四次
大學一年級是第五次
第六次是讀第二間大學的一年級
之後間隔開始拉長
第七次是第六次的七年後
老實說她也搞不清楚現在究竟是第幾次
只知道更年期總是在更年的時候出現
儘管之前經歷過那樣多次數的更年
每次更年
都還是像
第一次更年
更年很累
但總會過去(?)
2014年9月15日 星期一
桌布
我每天都看到他
看久就忘了
忘了他其實並不在我電腦的桌面上
而是在我身後那片小園子裡
我每天都看到他
看久就看不到了
我的眼睛開開關關
卻什麼也沒看到
「好可愛的兔子喔」
昨天第一次來家裡的朋友說
我才發現親愛的斑斑
已經變成一張桌布
看久就忘了
忘了他其實並不在我電腦的桌面上
而是在我身後那片小園子裡
我每天都看到他
看久就看不到了
我的眼睛開開關關
卻什麼也沒看到
「好可愛的兔子喔」
昨天第一次來家裡的朋友說
我才發現親愛的斑斑
已經變成一張桌布
攝影:楊老斌。2013年11月20日
2014年9月14日 星期日
稻穗拓繪記錄(天然油漆)
這批帆布袋拓繪用的是天然油漆,用法跟之前用壓克力顏料很不同。要調色或把顏色洗掉,是用松節油,而不是水,所以顏料要分色分得很清楚,筆也要分很多枝,一種顏色用一枝筆,調色時也要換筆(從前我用壓克力顏料都是一支筆用到底)。
拓繪其實有點像版畫(其實就是版畫),只是那個版是實物的版。一個一個帆布袋拓印下來,附著在稻子上的油漆也會跟著越來越厚,厚到一個程度,稻子的形狀就會越來越不明顯。這時可以用剪刀或刮刀輕輕地將還未完全乾掉、多餘的顏料刮掉。沒有處理好就會糊掉,像下面那張拓繪。
同一批稻子拓到後來,會變得很像稻子的模型。明明就是稻子,卻很像稻子的模型。
實物拓繪的缺點是,被拓的東西是消耗品。像稻子,稻穗隨著一次一次拓印,一次掉個幾粒,掉個幾粒,掉到最後稻穗上的稻子便零零落落了。這時候就只好再換一批稻子。
2014年9月13日 星期六
我到底是哪裡卡住了呢?
昨天,我跟學校借了鑰匙
開學校後側的大門
帶小孩去種菜
我拿鑰匙開鎖
鎖開了之後鑰匙在鎖上
我把鑰匙跟鎖一起
放在包包內
放學時間到了
小孩也播完種子澆完水了
雖然他們還不想回家
因為灑水實在太好玩了
但是沒辦法
水再繼續澆下去
種子就要淹死了
於是我吆喝著
腳洗一洗我們要回去囉
然後小孩們一個一個走回校園
我走最後一個
我走最後一個
把鎖拿出來要鎖門的時候
發現
咦?鑰匙怎麼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
我怎麼轉動鑰匙都
拔不出來
這下該怎麼鎖門呢
鎖該不會被我用壞吧
(還好小孩都走前面沒有看到)
如果我硬要轉鑰匙鑰匙會被我弄斷吧
真糟糕
才第一次開學校的門
就要把人家的鎖弄壞嗎
我把拔不出鑰匙的鎖
放回包包內
去找主任
雖然有點不好意思
但總比把學校的鎖用壞好吧
「主任,不好意思,這個,鑰匙我拔不出來耶」
「不知道是哪裡卡住了......」
主任帶著狐疑的表情接過鑰匙和鎖
然後
我聽見「咖」的一聲
「鎖要先鎖上,鑰匙才拔得出來喔!」
主任的臉微笑著
我想我的臉大概也只剩下微笑
不對,是傻笑
「ㄛ,真是太蠢了……我想應該是我卡住了……」
回家的路上
我一直想著
我到底是哪裡卡住了呢?
到底是哪裡卡住了呢?
是哪裡卡住了呢?
好吧
這種事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像
我下車時
經常會撞到頭
一次、兩次、三次
特別是坐XX的車的時候
我真的有注意
可是就是會撞到頭
我的頭本來就有角了
這下角更是明顯了
這就是人生無法解釋的缺陷嗎?
(喂,不要推託給人生好嗎?)
開學校後側的大門
帶小孩去種菜
我拿鑰匙開鎖
鎖開了之後鑰匙在鎖上
我把鑰匙跟鎖一起
放在包包內
放學時間到了
小孩也播完種子澆完水了
雖然他們還不想回家
因為灑水實在太好玩了
但是沒辦法
水再繼續澆下去
種子就要淹死了
於是我吆喝著
腳洗一洗我們要回去囉
然後小孩們一個一個走回校園
我走最後一個
我走最後一個
把鎖拿出來要鎖門的時候
發現
咦?鑰匙怎麼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
我怎麼轉動鑰匙都
拔不出來
這下該怎麼鎖門呢
鎖該不會被我用壞吧
(還好小孩都走前面沒有看到)
如果我硬要轉鑰匙鑰匙會被我弄斷吧
真糟糕
才第一次開學校的門
就要把人家的鎖弄壞嗎
我把拔不出鑰匙的鎖
放回包包內
去找主任
雖然有點不好意思
但總比把學校的鎖用壞好吧
「主任,不好意思,這個,鑰匙我拔不出來耶」
「不知道是哪裡卡住了......」
主任帶著狐疑的表情接過鑰匙和鎖
然後
我聽見「咖」的一聲
「鎖要先鎖上,鑰匙才拔得出來喔!」
主任的臉微笑著
我想我的臉大概也只剩下微笑
不對,是傻笑
「ㄛ,真是太蠢了……我想應該是我卡住了……」
回家的路上
我一直想著
我到底是哪裡卡住了呢?
到底是哪裡卡住了呢?
是哪裡卡住了呢?
好吧
這種事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像
我下車時
經常會撞到頭
一次、兩次、三次
特別是坐XX的車的時候
我真的有注意
可是就是會撞到頭
我的頭本來就有角了
這下角更是明顯了
這就是人生無法解釋的缺陷嗎?
(喂,不要推託給人生好嗎?)
2014年9月11日 星期四
事件
事件,通常會說成「事情」,或「事」。我們會說「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或「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比較少說「今天發生了一個事件」。但其實這只是說法的習慣而已,事情、事件,指的都是類似的意思。
但是,事情,或說事件,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張大春在《本事》中是這麼解釋「事情」的:
無論字典上的定義如何、也不管在一般人的經驗理解中如何;依照我固執的看法,(事情)就是一連串無法避免或更改的因果關係之中的一個鍵、一個部份、一個不能被抽離於之前以及之後一切的某種存在狀況。
為什麼要引用張大春的說法呢?因為,關於「事情」的意思,張大春的說法是我從前沒想過的。雖然這樣的說法沒有什麼了不起,也不是什麼創新的意見,但由於我自己沒有想到過,所以也不好意思把別人的說法當成自己的想法,雖然(再次強調)這樣的說法在理解之後會覺得是啊本來就是這樣有需要特別拿出來說嗎。
延伸張大春的說法,若我們想要定義「一個事件」將十分困難,或者說根本不可能;因為,有什麼事件是可以脫離其他事件,自己單獨存在呢?
我在這裡用「事件」,而不用「事情」,是因為「事件」聽起來比「事情」更有一種──發生了一個什麼XX的味道;我不太會解釋,只能舉例。比如我們會說「十三年前的今天發生了911事件」,而不會說發生了「911事情」。
所以說,「事情」和「事件」,應該還是有些不一樣的。但這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重點。嗯,我的廢話真是很多。
其實,我想寫的是影響「我這個人」的「幾件事」;其實,會想寫這個東西是因為小四說「我的生命經驗幾乎都是『事件影響』」;其實,誰不是呢?所謂的生命經驗這個東西,不就是一個事件一個事件累加起來的嗎?(當然,我們無法明確地區隔這個事件與那個事件的界限)
但在我們的記憶中,總是有那麼一個點,我們對於某件事的記憶的起點與終點。也就是說,儘管那個事件並沒有所謂的起點與終點,但記憶中的事件是有的。隨便回想某個事件,會發現自己對它的記憶一定是從某個點開始,某個點結束,而前面後面究竟發生了什麼,細節全忘記了,最多只剩輪廓。
當然據說也是有那種全部記得一清二楚的人。還好我不是那種人,那很恐怖。
關於什麼是「事件」這個東西,好像寫得太多了,寫到後來到底哪些事情是我覺得影響自己生命的事,好像寫不寫都無所謂了。我本來想要藉此再回顧一下自己,一些曾經發生的事。但是,我能從那些記憶中曾經發生的事,再得出一些新的體悟嗎?會不會只是在翻舊事而已?
人總是喜歡翻舊事,因為舊的事已經過去,而新的還沒有來。我們在自己現在的位置上,用舊事替自己定義現在的位置:「為什麼我在這裡?」
但究竟「為什麼我在這裡?」這件事,不是幾個事件就可以回答。
但是,事情,或說事件,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張大春在《本事》中是這麼解釋「事情」的:
無論字典上的定義如何、也不管在一般人的經驗理解中如何;依照我固執的看法,(事情)就是一連串無法避免或更改的因果關係之中的一個鍵、一個部份、一個不能被抽離於之前以及之後一切的某種存在狀況。
為什麼要引用張大春的說法呢?因為,關於「事情」的意思,張大春的說法是我從前沒想過的。雖然這樣的說法沒有什麼了不起,也不是什麼創新的意見,但由於我自己沒有想到過,所以也不好意思把別人的說法當成自己的想法,雖然(再次強調)這樣的說法在理解之後會覺得是啊本來就是這樣有需要特別拿出來說嗎。
延伸張大春的說法,若我們想要定義「一個事件」將十分困難,或者說根本不可能;因為,有什麼事件是可以脫離其他事件,自己單獨存在呢?
我在這裡用「事件」,而不用「事情」,是因為「事件」聽起來比「事情」更有一種──發生了一個什麼XX的味道;我不太會解釋,只能舉例。比如我們會說「十三年前的今天發生了911事件」,而不會說發生了「911事情」。
所以說,「事情」和「事件」,應該還是有些不一樣的。但這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重點。嗯,我的廢話真是很多。
其實,我想寫的是影響「我這個人」的「幾件事」;其實,會想寫這個東西是因為小四說「我的生命經驗幾乎都是『事件影響』」;其實,誰不是呢?所謂的生命經驗這個東西,不就是一個事件一個事件累加起來的嗎?(當然,我們無法明確地區隔這個事件與那個事件的界限)
但在我們的記憶中,總是有那麼一個點,我們對於某件事的記憶的起點與終點。也就是說,儘管那個事件並沒有所謂的起點與終點,但記憶中的事件是有的。隨便回想某個事件,會發現自己對它的記憶一定是從某個點開始,某個點結束,而前面後面究竟發生了什麼,細節全忘記了,最多只剩輪廓。
當然據說也是有那種全部記得一清二楚的人。還好我不是那種人,那很恐怖。
關於什麼是「事件」這個東西,好像寫得太多了,寫到後來到底哪些事情是我覺得影響自己生命的事,好像寫不寫都無所謂了。我本來想要藉此再回顧一下自己,一些曾經發生的事。但是,我能從那些記憶中曾經發生的事,再得出一些新的體悟嗎?會不會只是在翻舊事而已?
人總是喜歡翻舊事,因為舊的事已經過去,而新的還沒有來。我們在自己現在的位置上,用舊事替自己定義現在的位置:「為什麼我在這裡?」
但究竟「為什麼我在這裡?」這件事,不是幾個事件就可以回答。
隱匿最近常上新聞
衛生局查如記「隱匿」全統油開罰
「隱匿」用餿油!台中太陽堂罰200萬
如記餿飯糰全數供給國軍「隱匿」未報重罰3百萬
光頭呂抓餅「隱匿」下游再罰300萬
餿水油二業者「隱匿」台中重罰
油蔥店爆用餿水油涉「隱匿」下游廠商
不滿「隱匿」用餿水油桃衛生局重罰中壢「老克明蔥油餅」
油蔥店「隱匿」下游商衛生局令停業
「隱匿」戴奧辛鴨環保署:民眾夠痛苦了
隱匿真是無所不在
隱匿耳朵會癢嗎?
隱匿說她一點都不高興
(註:「隱匿」是淡水有河book老闆娘,為人相當隱匿)
「隱匿」用餿油!台中太陽堂罰200萬
如記餿飯糰全數供給國軍「隱匿」未報重罰3百萬
光頭呂抓餅「隱匿」下游再罰300萬
餿水油二業者「隱匿」台中重罰
油蔥店爆用餿水油涉「隱匿」下游廠商
不滿「隱匿」用餿水油桃衛生局重罰中壢「老克明蔥油餅」
油蔥店「隱匿」下游商衛生局令停業
「隱匿」戴奧辛鴨環保署:民眾夠痛苦了
隱匿真是無所不在
隱匿耳朵會癢嗎?
隱匿說她一點都不高興
(註:「隱匿」是淡水有河book老闆娘,為人相當隱匿)
2014年9月10日 星期三
十本書(不只十本)
被蔡仁偉點到要點十本書。其實前兩天老斌和我還在說「什麼十本影響最深的書……」我的意思是挑十本感覺像是排出前十名,而我實在不太喜歡排名這種東西。
後來想想其實好像也可以換個方向想,不是排名,而是人家問你說有什麼好看的推薦,你會說這個好啦一定要看的啦。不過不看其實也不會後悔,因為別人就算不看你推薦的這本,但他還是有可能會碰到其他的書呀;就像你遇到一個很棒的人,但其他的人也會遇到其他很棒的人一樣(我在說什麼……)。說是這樣說,但我確實因為遇到了一些很棒的書(或人),我生命中部份的什麼,好像因此被影響了。我是這麼覺得。
1.《二十世紀少年》浦澤直樹
雖然我前面說沒有什麼好排名的,但《二十世紀少年》是我最愛的漫畫無誤!
2.《我的天》歐陽應霽
《我的天》是我最愛的四格漫畫。所謂的哲學味四格漫畫就是這個吧!
3.《失落的一角》、《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謝爾.希爾弗斯坦
幾乎,每次看都哭。(偷渡一本應該沒關係吧......)
4.《怪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我讀過最好看的劇作集。(糟糕,當我這麼說時,我又想起了另外一本……)
5.《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村上春樹
其實村上太難選了。所以我只好選我第一本讀的村上。
6.《鴿子》徐四金
整個故事都在講一個男人如何如何怕一隻鴿子,就只有這樣而已。
7.《家變》王文興
總覺得用一句話來講《家變》會被王文興罵……
8.《怎麼可能》隱匿
怎麼可能只選出一本詩集呢?但如果真要選就是《怎麼可能》了。沒有什麼道理,就是直覺而已。
9.《衛生紙+》鴻鴻編
蔡仁偉可以列《史努比》,我應該也可以列《衛生紙+》吧!說起來《衛生紙+》是我為什麼會寫詩的原因之一,我這麼列應該不為過吧......
10.《愛的藝術》佛洛姆
這本書不曉得到哪裡去了。請問有人借走了嗎?
點完之後,今天早餐時才想到:啊!我竟然沒有點《童年與解放》呀!然後另外我還想加點《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和《中東現場──揭開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迷霧》。
另外加點:
後來想想其實好像也可以換個方向想,不是排名,而是人家問你說有什麼好看的推薦,你會說這個好啦一定要看的啦。不過不看其實也不會後悔,因為別人就算不看你推薦的這本,但他還是有可能會碰到其他的書呀;就像你遇到一個很棒的人,但其他的人也會遇到其他很棒的人一樣(我在說什麼……)。說是這樣說,但我確實因為遇到了一些很棒的書(或人),我生命中部份的什麼,好像因此被影響了。我是這麼覺得。
1.《二十世紀少年》浦澤直樹
雖然我前面說沒有什麼好排名的,但《二十世紀少年》是我最愛的漫畫無誤!
2.《我的天》歐陽應霽
《我的天》是我最愛的四格漫畫。所謂的哲學味四格漫畫就是這個吧!
3.《失落的一角》、《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謝爾.希爾弗斯坦
幾乎,每次看都哭。(偷渡一本應該沒關係吧......)
4.《怪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我讀過最好看的劇作集。(糟糕,當我這麼說時,我又想起了另外一本……)
5.《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村上春樹
其實村上太難選了。所以我只好選我第一本讀的村上。
6.《鴿子》徐四金
整個故事都在講一個男人如何如何怕一隻鴿子,就只有這樣而已。
7.《家變》王文興
總覺得用一句話來講《家變》會被王文興罵……
8.《怎麼可能》隱匿
怎麼可能只選出一本詩集呢?但如果真要選就是《怎麼可能》了。沒有什麼道理,就是直覺而已。
9.《衛生紙+》鴻鴻編
蔡仁偉可以列《史努比》,我應該也可以列《衛生紙+》吧!說起來《衛生紙+》是我為什麼會寫詩的原因之一,我這麼列應該不為過吧......
10.《愛的藝術》佛洛姆
這本書不曉得到哪裡去了。請問有人借走了嗎?
點完之後,今天早餐時才想到:啊!我竟然沒有點《童年與解放》呀!然後另外我還想加點《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和《中東現場──揭開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迷霧》。
另外加點:
◆《童年與解放》黃武雄
◆《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顧玉玲
◆《中東現場──揭開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迷霧》張翠容
◆《觀看的方式》約翰.伯格
◆《觀看的方式》約翰.伯格
2014年9月8日 星期一
海上的雨
「我在那黑暗中,想起降落在海上的雨,想起廣大的海上,沒有任何人知道正靜悄悄地下著雨。雨無聲地敲著海面,連魚兒都不知道。」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村上春樹
第一次讀到這段話時,我還沒有見過海上的雨。可是不曉得為什麼沒見過海上的雨的我,卻覺得自己好像知道他在說什麼。一直到我遇見了海上的雨,遠遠地看著海上的雨,正「靜悄悄地」下著;我才明白,原本我一開始根本不懂,那靜悄悄地降落在海上的雨,想要說的究竟是什麼。
從前我以為海上的雨就像那段文字寫的那樣,是靜悄悄地。後來我才明白那其實並不是靜悄悄地。海上的雨怎麼可能靜悄悄地呢?你看那樣厚重的雲在海面的上方,那灰黑色的雲會下著多麼大的雨呢?雲在海上走著,雨啪拉啪拉地下著。我好像可以想像大顆大顆的雨滴打在海上的聲音,打進海面的聲音。
但那只是想像的。事實上遠遠的在車子這端的我,什麼聲音也沒聽到。我只是看著那樣的雨,然後這麼想像而已。這時我才發現,如果在車子裡的我一直朝著前方看著,我沒有轉頭去看右方的海,那麼,那海上的雨「確實」靜悄悄地下著,靜悄悄地下著,沒有人發現。
明明那樣灰那樣黑那樣沉重的雲,下著那樣灰那樣黑那樣沉重的雨,可是沒有人發現。雨明明劈哩啪啦花哩嘩啦地下著,卻連魚兒都不知道。
海面上的雨很大聲很大聲地下著下著,可是他沒有轉頭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再大的雨也是靜悄悄地。
我想這是他想說的,或是我想說的東西。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村上春樹
第一次讀到這段話時,我還沒有見過海上的雨。可是不曉得為什麼沒見過海上的雨的我,卻覺得自己好像知道他在說什麼。一直到我遇見了海上的雨,遠遠地看著海上的雨,正「靜悄悄地」下著;我才明白,原本我一開始根本不懂,那靜悄悄地降落在海上的雨,想要說的究竟是什麼。
從前我以為海上的雨就像那段文字寫的那樣,是靜悄悄地。後來我才明白那其實並不是靜悄悄地。海上的雨怎麼可能靜悄悄地呢?你看那樣厚重的雲在海面的上方,那灰黑色的雲會下著多麼大的雨呢?雲在海上走著,雨啪拉啪拉地下著。我好像可以想像大顆大顆的雨滴打在海上的聲音,打進海面的聲音。
但那只是想像的。事實上遠遠的在車子這端的我,什麼聲音也沒聽到。我只是看著那樣的雨,然後這麼想像而已。這時我才發現,如果在車子裡的我一直朝著前方看著,我沒有轉頭去看右方的海,那麼,那海上的雨「確實」靜悄悄地下著,靜悄悄地下著,沒有人發現。
明明那樣灰那樣黑那樣沉重的雲,下著那樣灰那樣黑那樣沉重的雨,可是沒有人發現。雨明明劈哩啪啦花哩嘩啦地下著,卻連魚兒都不知道。
海面上的雨很大聲很大聲地下著下著,可是他沒有轉頭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再大的雨也是靜悄悄地。
我想這是他想說的,或是我想說的東西。
2014年9月7日 星期日
為理想勞動
三百個帆布袋拓繪,要在一個月內完成。如果除以三十,那麼就是一天十個。說是這樣說,但一個月三十天我不可能天天拓繪,總還有其他的事。禮拜五下午固定要去學校上課,要上課的話就花時間得備課;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當然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事。於是我抓了二十一個工作天,其實本來打算只抓二十天,一天做十五個這樣,但總覺得一定會有某天狀況不好或時間不夠而無法達成,所以多給了自己一天。
三百個袋子都是稻穗。小四說這樣你跟成衣廠有什麼兩樣?我說對呀我就是人工成衣廠,心裡想著剛好可以感受看看女工工作的心情。當然女工一天不可能只做十五個袋子,也不能自己決定上下班的時間,想休息的時候說不定也不能休息,心情不好的話也不能耍脾氣。
今年詩歌節的主題是「為理想勞動」。「為理想勞動」,聽起來好馬克思喔。不過我一點都不懂馬克思,我是亂說的。為理想勞動,那麼,我現在是在為理想勞動嗎?
女工為理想勞動嗎?還是為錢勞動呢?為理想勞動比為錢勞動高尚嗎?我為了什麼勞動呢?
9月5日那天剛好在區役場攔截到要送袋子去我家的貨運。我請司機先生幫我把裝滿帆布袋的一個好大的紙箱放上我們自己的貨車後,把車門關上又回到區役場。小四說袋子不是來了嗎?我說明天再開始好了,今天如果沒幫區役場做根榫,我想整個九月應該都沒空做了。
柏宏還在替木頭畫線,所以一時半刻也沒工作好做。我說我今天該不會做不到半根榫吧?小四說人生來不是來工作的,是來吃飯生孩子的。
我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是人並不是生來做事的。但這又不意味著不要做事。
我們為了什麼做事呢?
在區役場施工的大家都是志工,換句話說大家在這兒並不是為錢勞動,因為根本就沒錢呀。那麼大家是為理想勞動嗎?每個人的原因可能都不太一樣,通通說成是為理想勞動那話也說得太漂亮了。別人是為了什麼我不知道,我是為了想要做那件事而勞動。
比如做榫。我看小四阿春輝哥他們用槌子和鑿刀一塊塊一片片將木頭削下來,原本實心的地方開始慢慢變成一個缺角,或一個洞。我好想要感覺看看用鑿刀將木頭削下來的感覺。感覺這種東西,不自己試試看是不會知道的。
所以呢?為什麼說到這個地方來了呢?
做稻穗拓繪時,我將稻穗排成我希望她在布上呈現的樣子,然後分色調漆,上色,將布固定好位置後按壓,翻起看印色狀況,再局部上色,按壓。上色與按壓的動作大概重覆三次,所以三百個袋子拓繪我將重覆這樣的動作約九百次。
有時會想,重覆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不會去問為什麼每天都要吃飯、睡覺。(有人會說這跟工作不一樣)
我們不會去問你愛某個人為什麼你要天天愛他?為什麼不要今天愛明天不愛呢?(有人會說這跟工作有什麼關係)。當然關於愛這件事,確實有今天愛而明天不愛,這樣的事。
某些事情必須不斷重覆,因為重覆而美好。
這跟為理想勞動有什麼關係呢?沒什麼關係。只是我還蠻喜歡看著那些拓繪上稻穗的袋子,一個個掛吊著的樣子。
9月6日是11個。9月7日是15個。目前完成26/300。給自己的deadline是10月3日。
三百個袋子都是稻穗。小四說這樣你跟成衣廠有什麼兩樣?我說對呀我就是人工成衣廠,心裡想著剛好可以感受看看女工工作的心情。當然女工一天不可能只做十五個袋子,也不能自己決定上下班的時間,想休息的時候說不定也不能休息,心情不好的話也不能耍脾氣。
今年詩歌節的主題是「為理想勞動」。「為理想勞動」,聽起來好馬克思喔。不過我一點都不懂馬克思,我是亂說的。為理想勞動,那麼,我現在是在為理想勞動嗎?
女工為理想勞動嗎?還是為錢勞動呢?為理想勞動比為錢勞動高尚嗎?我為了什麼勞動呢?
9月5日那天剛好在區役場攔截到要送袋子去我家的貨運。我請司機先生幫我把裝滿帆布袋的一個好大的紙箱放上我們自己的貨車後,把車門關上又回到區役場。小四說袋子不是來了嗎?我說明天再開始好了,今天如果沒幫區役場做根榫,我想整個九月應該都沒空做了。
柏宏還在替木頭畫線,所以一時半刻也沒工作好做。我說我今天該不會做不到半根榫吧?小四說人生來不是來工作的,是來吃飯生孩子的。
我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是人並不是生來做事的。但這又不意味著不要做事。
我們為了什麼做事呢?
在區役場施工的大家都是志工,換句話說大家在這兒並不是為錢勞動,因為根本就沒錢呀。那麼大家是為理想勞動嗎?每個人的原因可能都不太一樣,通通說成是為理想勞動那話也說得太漂亮了。別人是為了什麼我不知道,我是為了想要做那件事而勞動。
比如做榫。我看小四阿春輝哥他們用槌子和鑿刀一塊塊一片片將木頭削下來,原本實心的地方開始慢慢變成一個缺角,或一個洞。我好想要感覺看看用鑿刀將木頭削下來的感覺。感覺這種東西,不自己試試看是不會知道的。
所以呢?為什麼說到這個地方來了呢?
做稻穗拓繪時,我將稻穗排成我希望她在布上呈現的樣子,然後分色調漆,上色,將布固定好位置後按壓,翻起看印色狀況,再局部上色,按壓。上色與按壓的動作大概重覆三次,所以三百個袋子拓繪我將重覆這樣的動作約九百次。
有時會想,重覆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不會去問為什麼每天都要吃飯、睡覺。(有人會說這跟工作不一樣)
我們不會去問你愛某個人為什麼你要天天愛他?為什麼不要今天愛明天不愛呢?(有人會說這跟工作有什麼關係)。當然關於愛這件事,確實有今天愛而明天不愛,這樣的事。
某些事情必須不斷重覆,因為重覆而美好。
這跟為理想勞動有什麼關係呢?沒什麼關係。只是我還蠻喜歡看著那些拓繪上稻穗的袋子,一個個掛吊著的樣子。
9月6日是11個。9月7日是15個。目前完成26/300。給自己的deadline是10月3日。
2014年9月6日 星期六
一直想著前天晚上的月光
一直想著前天晚上的月光。
應該是晚餐時間的七點多,洗完澡後就覺得不行了,簡單吃了餅乾後就去榻榻米上倒,那時讓身體平平地躺下來雙手雙腳打開比什麼都重要。以為會很快睡著,沒想到倒下來後就只是倒下來,眼睛雖然閉著,卻一點睡意也沒有,腦袋裡一直轉著各式各樣的事情。
竟然就這樣過了一個多小時。
因為躺了實在很久,眼睛也確實閉著,所以一個多小時後疲勞好像有點消褪了。我起來上廁所,喝一小口水,老斌切了鳳梨我們一起吃。我翻開張大春的《本事》讀了幾頁,想著說不定看到累了就想睡了,那時候八點多快九點。
九點多我回到榻榻米,躺平,閉上眼睛。閉著眼睛的我感覺到從窗外透進來的光比平常亮。我睜開眼睛,看著那亮在榻榻米上的光,那光和影子確實比平常鮮明,顏色也不一樣。
「是月光嗎?」我坐起身子看出窗外,循著光的方向找月亮。「如果沒看到月亮,那就是路口的燈了。」我這樣想著。
我看到月亮了。
以我坐著的位子為中心的話,抬頭約11點鐘時針的方向是月亮。當然這不是確切的月亮的位置,而是那時坐在榻榻米上的我對月亮方向位置的感覺而已。總之,月亮在高高的,接近頭頂但還不到頭頂的地方,遠遠的斜斜的光,從我無法想像的遠的地方,到達我坐著的榻榻米上。
當然我可以上網google,一查就可以知道月亮離我們有多遠。但那個數字對當時的我來說沒有任何一點意義。我坐在窗邊,歪著頭看月亮。月亮旁邊一片雲都沒有,月亮很亮,看起來是圓的。
說看起來是圓的是因為當時的我沒有戴眼鏡。昨天戴著眼鏡看月亮時,才發現原來月亮一點都不圓啊!是檸檬形狀的月亮。還好我跟小四阿春說起前天的月亮時,是說月亮好亮,不是月亮好圓,不然一定會被以為眼睛壞掉。
我跟老斌說我們榻榻米上的光是月光喔。老斌說是路燈吧。我說是月光啦。老斌說看光等一下會不會移動就知道。
後來,光還沒有動的時候,就先漸漸淡了,淡到快要看不到的樣子。前幾分鐘還非常鮮明的光,突然就暗下來了。我又坐起身,又歪頭看出窗外看月亮,月亮旁邊看起來有雲,但還是看得到月亮。
榻榻米上的光快要不見了。那是月光。
月光暗到快要看不到了,但是月亮在那裡。在我坐起身歪頭看出窗外就能看得到的地方。
過了感覺上大概幾十秒的時間,月光又亮在榻榻米上了。我看著在亮在榻榻米上的光,想著如果是路燈如果是陽光,我都不會這樣大驚小怪。「就只是月光照進來房間裡面的榻榻米而已,」應該會有人這樣說吧!
路燈的光不曉得照進來幾千幾百次了,太陽的光一直都在,月光也是。但為什麼那個時候那一小塊亮在我面前的光,讓我看那樣那樣久呢?
因為我很累嗎?我並不是真的很累。因為那光讓我想起了許多事情。
我想起我以為不在的東西但其實都在。一些很遠的人。曾經很近卻很遠的人。在我看著這個光的時候,那亮著這光的月亮在我們的上方,即使他們沒有看到。
應該是晚餐時間的七點多,洗完澡後就覺得不行了,簡單吃了餅乾後就去榻榻米上倒,那時讓身體平平地躺下來雙手雙腳打開比什麼都重要。以為會很快睡著,沒想到倒下來後就只是倒下來,眼睛雖然閉著,卻一點睡意也沒有,腦袋裡一直轉著各式各樣的事情。
竟然就這樣過了一個多小時。
因為躺了實在很久,眼睛也確實閉著,所以一個多小時後疲勞好像有點消褪了。我起來上廁所,喝一小口水,老斌切了鳳梨我們一起吃。我翻開張大春的《本事》讀了幾頁,想著說不定看到累了就想睡了,那時候八點多快九點。
九點多我回到榻榻米,躺平,閉上眼睛。閉著眼睛的我感覺到從窗外透進來的光比平常亮。我睜開眼睛,看著那亮在榻榻米上的光,那光和影子確實比平常鮮明,顏色也不一樣。
「是月光嗎?」我坐起身子看出窗外,循著光的方向找月亮。「如果沒看到月亮,那就是路口的燈了。」我這樣想著。
我看到月亮了。
以我坐著的位子為中心的話,抬頭約11點鐘時針的方向是月亮。當然這不是確切的月亮的位置,而是那時坐在榻榻米上的我對月亮方向位置的感覺而已。總之,月亮在高高的,接近頭頂但還不到頭頂的地方,遠遠的斜斜的光,從我無法想像的遠的地方,到達我坐著的榻榻米上。
當然我可以上網google,一查就可以知道月亮離我們有多遠。但那個數字對當時的我來說沒有任何一點意義。我坐在窗邊,歪著頭看月亮。月亮旁邊一片雲都沒有,月亮很亮,看起來是圓的。
說看起來是圓的是因為當時的我沒有戴眼鏡。昨天戴著眼鏡看月亮時,才發現原來月亮一點都不圓啊!是檸檬形狀的月亮。還好我跟小四阿春說起前天的月亮時,是說月亮好亮,不是月亮好圓,不然一定會被以為眼睛壞掉。
我跟老斌說我們榻榻米上的光是月光喔。老斌說是路燈吧。我說是月光啦。老斌說看光等一下會不會移動就知道。
後來,光還沒有動的時候,就先漸漸淡了,淡到快要看不到的樣子。前幾分鐘還非常鮮明的光,突然就暗下來了。我又坐起身,又歪頭看出窗外看月亮,月亮旁邊看起來有雲,但還是看得到月亮。
榻榻米上的光快要不見了。那是月光。
月光暗到快要看不到了,但是月亮在那裡。在我坐起身歪頭看出窗外就能看得到的地方。
過了感覺上大概幾十秒的時間,月光又亮在榻榻米上了。我看著在亮在榻榻米上的光,想著如果是路燈如果是陽光,我都不會這樣大驚小怪。「就只是月光照進來房間裡面的榻榻米而已,」應該會有人這樣說吧!
路燈的光不曉得照進來幾千幾百次了,太陽的光一直都在,月光也是。但為什麼那個時候那一小塊亮在我面前的光,讓我看那樣那樣久呢?
因為我很累嗎?我並不是真的很累。因為那光讓我想起了許多事情。
我想起我以為不在的東西但其實都在。一些很遠的人。曾經很近卻很遠的人。在我看著這個光的時候,那亮著這光的月亮在我們的上方,即使他們沒有看到。
2014年9月4日 星期四
擠壓
如果從腳底開始算的話,現在已經快滿到頭頂了,差不多在眼睛的位置。由於還沒有蓋過眼睛,所以還看得到,還知道不能再加事情進來。儘管如此,聽到一件有趣想要試試看的邀約時,竟然還是考慮了幾分鐘。
如果真的再把事情加進來,那就不是滿到頭頂的問題了,而是擠壓的問題。為了把那件事加進來,不得不把已經滿到眼睛的部分,再往下面擠壓,擠壓到喉嚨,甚至是胸口的位置。這樣,加進來的事才不會把自己撐到爆掉,因為爆掉就沒有了呀!
但是,被擠壓的部分呢?那些原本應該有鬆鬆寬寬空間的東西,因為被擠壓而變形了。想想就覺得很可憐,被壓到變形的樣子。
更可憐的可能是自己,外表上看不出來,可是裡面已經被擠壓到變形了。
如果真的再把事情加進來,那就不是滿到頭頂的問題了,而是擠壓的問題。為了把那件事加進來,不得不把已經滿到眼睛的部分,再往下面擠壓,擠壓到喉嚨,甚至是胸口的位置。這樣,加進來的事才不會把自己撐到爆掉,因為爆掉就沒有了呀!
但是,被擠壓的部分呢?那些原本應該有鬆鬆寬寬空間的東西,因為被擠壓而變形了。想想就覺得很可憐,被壓到變形的樣子。
更可憐的可能是自己,外表上看不出來,可是裡面已經被擠壓到變形了。
2014年9月2日 星期二
訂閱:
文章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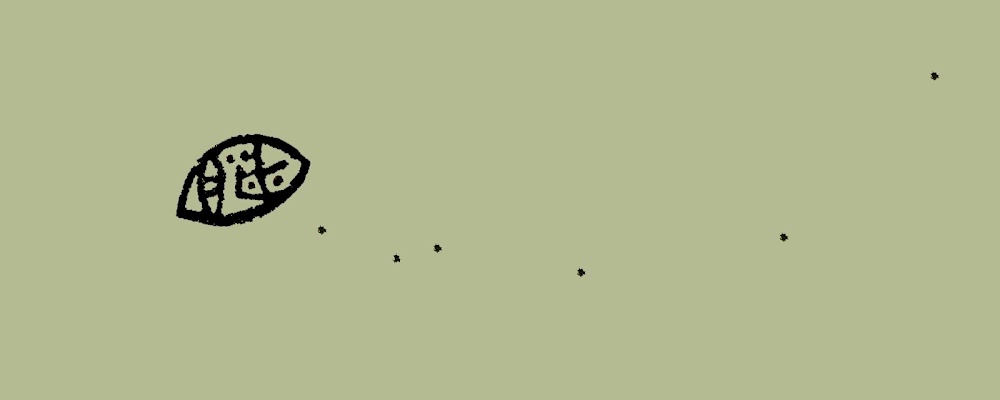
.jpg)
.jpg)

.jpg)
.%E4%BF%AE%E6%94%B9.jpg)
.jpg)
.jpg)
.jpg)
.jpg)
.%E4%BF%AE%E6%94%B9.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