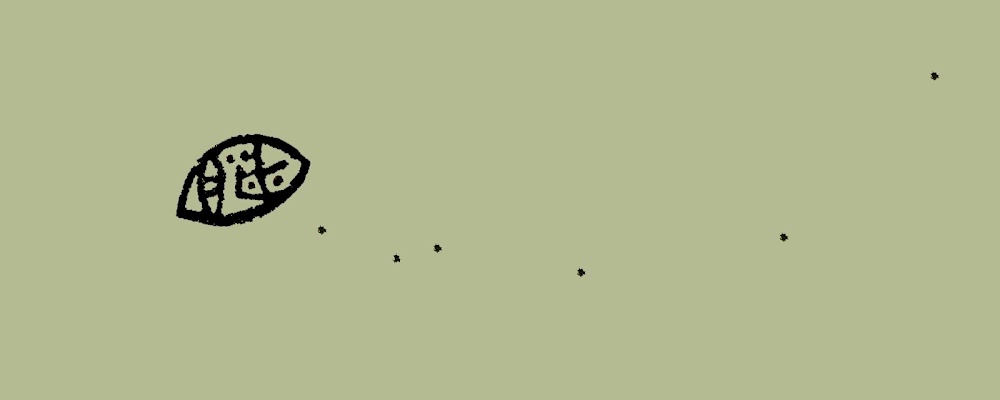讀完《女二》,去找了鄧九雲的短篇來看。《最初看似新奇的東西》,書封那張金金粗粗亮亮的紙,上頭有著淺淺的波浪,像是金色的海,像是月光反射在黑夜海上。「短的故事會慢慢念。有很多事情要交代的長故事會快念。」扉頁引了一句John Cage。
我跟著這句話念了好幾遍,接下來我果然念得很慢。念,感覺有聲音,用嘴巴發出聲音念出來。讀就沒有聲音了,是用腦袋看。這十七篇故事,在我的腦袋裡發出聲音。每一篇都是「我」,我跟著「我」的獨白。
「喜歡一個人就是這個樣子嗎?覺得他跟別人不一樣,所以被他喜歡的我,就因此跟別人不一樣了。總會突然想到這種感覺,每天醒來的第一秒想到,肚子很餓時想到,聽朋友說話沉默的空檔想到,或是洗澡,上廁所,刷牙時,很突然地想到──我喜歡這個人。短暫到甚至有點忘記自己剛才是否想過這個念頭。」
「我開始思考人類的思想與線性時間的關係。時間不如所有物體那麼具象。但時間能量化,幸福的感覺卻只能質化。」
「觀眾當然沒有演員好看,可是真實才是最嚇人的。難看的戲,往往能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了無新意。人就沒有那麼好預測了,所以生命有時比戲劇還要精彩(可以說戲劇就是濃縮版的生命故事嗎?)比如說,接下來這突如的一刻,我在自己的愛情故事裡從主角降格成一個大配角。」
「一想到不會再見面,我的身體竟產生一種奇妙的鬆弛感。我在路上漫無目的地行走,身邊經過很多男人與女人,我想專注觀察他們身上的某一個微小的部分,譬如男人的嘴唇上面有沒有剛長出來的鬍渣,女人兩邊的眉毛是否對稱。漸漸地,每個從我眼前經過的人,都不再以『人』為單位,而是一個個『部位』。每個人的氣味都不一樣,一口氣混雜在一起聞著想吐。世界的一切像用望遠鏡看出去的放大距離。我好像突然聞到他身上的味道,感到連接心臟的肌肉和血管被狠狠扯了一下。」
我在睡前看,在火車上看,斷斷續續地看。看得很慢,怕太快看完。但終於還是看完了。剛剛,我隨意抽取了幾個段落,每段每段拼貼起來,發現它們竟然能變成另一篇故事?只是沒有名字,沒有劇情。好像是這樣,我們人生中的許多片段,一段一段截下來,在那些細小片刻曾看過聽過感受過的,如此貼近與重疊,像是有人幫你說你的故事,像是每個人的故事剪碎後重新拼貼。
但十七個短篇是有劇情的,每篇裡的「我」有各自的名字,作者再用某種連接將這些短篇串成長篇,這個故事的我跟另一個故事的我,因此有了連結。像是真實人生,我是我故事中的主角,在你的故事中我是配角,而另一個曾在我的你的故事中出現的人,在他自己的故事中成了主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白,每個人在獨白中都是世界的中心。
還是小孩時就曾有過這種感覺,快要睡著的時候,腦袋還在轉著,覺得這世界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我此時此刻腦袋裡的東西,這世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腦袋裡的東西。
這世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腦袋裡的東西。而另一個人也想著同樣的事情。
「這樣說吧,蒙太奇根本不是什麼新東西,人類的記憶就是蒙太奇。記憶畫面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排列組合,故事就如我們所願地被留在大腦裡了。這樣講有點俗氣,但確實我們都在自編自導,整個世界不過是配角。」